《新闻扶贫行》之四刊载于1996年10月29日《保定日报》
过去热衷办企业,建一个砸一个;如今立足优势求发展,林果畜牧治了穷。请看:
“龙泉关现象”说明了什么
本报记者 王铮 宋钢 朝辉 宇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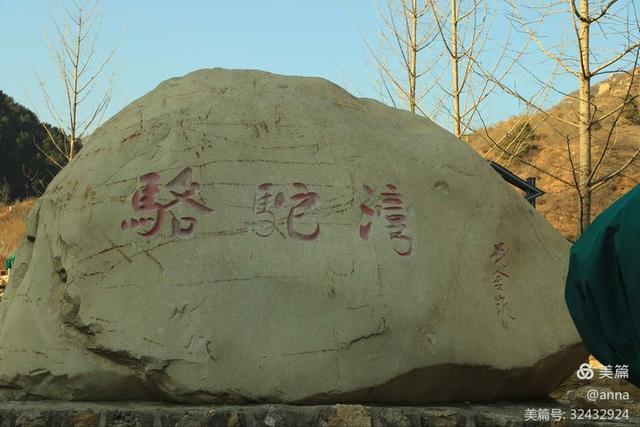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是对当今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典型概括。然而近日在国家级重点贫困县阜平采访,记者却了解到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该县龙泉关镇在80年代中期曾兴办过多家乡镇企业,没几年光景便纷纷倒闭破产;近几年,这个镇发挥资源优势,发展畜牧林果业,贫困村、户正走上稳定脱贫之路。
10月16日,在颠簸了一个多小时后,记者一行来到距县城35公里的龙泉关镇。“龙泉关现象”的话题从我们见到西刘庄村支部书记马有红谈起。马支书今年55岁,去年全家靠200多棵果树收入5000多元,成为全村脱贫带头人。
黝黑的脸膛、朴实的言谈,很难让人将老马同“厂长”联系起来,然而比起如今西服革履、手持大哥大的乡企老板来,马有红“出道”的确要早得多。还是在1984年前后,阜平县兴起了一股大办乡镇企业的热潮。当时任村委会主任的马有红,到高阳考察到景泰蓝市场看好,回来便筹集10多万元贷款办起了村工艺品厂,自己兼任厂长。马有红带人跑原料、搞推销,然而,资金有限、市场行情不清、管理不善等问题接踵而至。一年下来,挣的钱都给了聘来的技术人员,厂里只剩下一大堆景泰蓝健身球、茶杯、烟缸等积压品。
挫折使西刘庄人明白了脱贫的希望还是在山上。从1986年起,村里先筹资3万元栽下3万株苹果苗,又贷款17万元进行水利配套:修建7500米的防渗渠,铺设8000米的地下管道,还建了4个扬水站及8个蓄水池。目前,村里拥有6万棵苹果、2.5万株核桃,1万亩油松。去年全村1132口人均收入675元,在全镇是最高的。今年仅苹果,全村收入就有20多万元。
“现在比你过去当一个月挣150元的厂长强多了吧?”老马开心地笑了。
据龙泉关镇负责人介绍,类似西刘庄村工艺品厂的企业,1984年至1985年间,全镇共建了13家。尽管当时办企业的初衷是为帮老区人民脱贫,但市场竞争的法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两、三年下来,胆红素厂、玻璃纤维厂、肠衣厂等相继败下阵来。全镇为此投入的60多万元资金算都交了“学费”。
干部、群众心里不是滋味,但慢慢的,人们琢磨出点门道来了:咱这山旮旯里,交通不畅、信息不灵、原料少,没人懂技术会管理,缺乏资金投入,办企业暂时还不是时候。
90年代初,龙泉关镇、党委、政府将脱贫的立足点选在种植、养殖业上。自1993年到今年上半年,全镇共投资42万元进行了以“节打蓄引”为主的改善水利设施工程;推广优质丰产技术,栽果树11万株,果品年产量达到550吨;利用牧场广阔的有利条件,引进小尾寒羊150只,大牲畜存栏达到2300头。特困村骆驼湾今年经镇里扶持,养牛达到475头,脱贫前景光明。
山还是这座山,人还是这方人,龙泉关人经历过彷徨,也品尝过喜悦。“作为革命老区,要让扶贫工作由领导主观意识变成千家万户的自觉行动,首先要立足资源优势,启动自身‘造血’机能。”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主要负责人王秀文这样对记者说。
优势与劣势总是相对一定的时空而言的,关键还在因地制宜,这或许就是“龙泉关现象”给我们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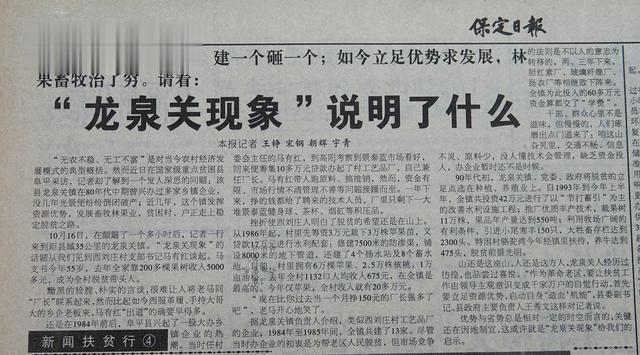
《新闻扶贫行》之五刊载于1996年11月1日《保定日报》。
8年前,从阜平深山沟里走出的9条穷汉扎根荒山,艰苦创业;看如今,异地扶贫开发使山披绿装,人结良缘。
“光棍山”上欢乐多
本报记者 王铮 宋钢 朝辉 宇青
“三岗三洼九光棍,花果满山引凤凰”。10月17日,我们刚到阜平县城厢村,就听到当地流传的这样一句民谣。民谣的背后,是一段异地扶贫,开发荒山的感人故事。过去的城厢村胡子沟,是一片荒山,夏天蒿草丛生没人腰。到处是坟头。1988年,村委会决定在荒山上开果园,便与扶贫部门联手,到县边远山区生存条件差的乡村招聘志愿者。9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小的十七八岁,大的二十八九,来到这荒凉的土地上,在村委会副主任李玉章的带领下誓与荒山较较劲。
在城厢村,我们见到了这9位拓荒者,他们是:周有章、耿卫国、耿建民、李树果、李士江、高贺英、仇喜民、王秀春、李顺。这9 人来自6个不同的山村,家乡生活太苦,土地贫瘠,连个媳妇都娶不起。
问起创业的艰辛,9个人你看我,我瞧你,每人都有一肚子苦水。
“刚来时,条件真艰苦”,耿卫国做了开 场白,“我们每天拎着7斤重的大铁锹,在山上锄草、挖坑、栽果树苗,一双新塑料底布鞋穿不到一星期就踩透了底儿。实在破得不能穿,就在鞋外面绑上块胶皮。鞋穿不起了,我们几个找到李副主任,硬让他去给订做几双铁底的鞋。”
王秀春接着说,“记得那次给树苗上肥,我们排着队去城关小学挑大粪。每人每天挑10担,来回要走三四十公里山路。那时我们都年轻,脸皮薄,挑着粪在人前走来走去可真拉不下脸。我一紧张,把粪桶弄翻了,扣了一身的屎尿。从那以后,我们这‘光棍队’又多了个‘大粪队’的美称。”
“你问我们业余时间干些啥?说实话,每天天不亮就上山,黑得啥也看不见了才回来吃饭,看见床板比见到亲人还亲,就想舒舒服服地睡一大觉,哪儿还有时间想娱乐!”李顺又说。
就这样,早出晚归,风餐露宿,9个壮小伙儿在山坡上开了4000米长的水平沟,在300多亩荒坡上种满了苹果、梨、桃、杏、柿子等14000多棵果树。打了机井,修好防渗渠,自来水通到家门口,小日子越过越舒坦。
花果满山野,引得凤凰来。1989年7月,王秀春第一个脱离了光棍队,邻村的姑娘主动找上门要嫁给他。办喜事那天可真热闹啊,原科技副县长李凤元亲自为他们主持了婚礼,县乡领导来了20多个。几个光棍汉喝醉了酒,高兴地在山林中翻滚呐喊,和同伴一起分享喜 悦。此后,光棍们陆续盖了新房,娶了新娘,唯一剩下的周有章也要在近日成亲。如今,9个光棍中有6个得了儿子,他们乐呵呵地说:“如今家里富裕了,再不用耽心儿子像我们早先一样打光棍了!”
主管扶贫工作的周怀军副县长一席话切入正题:“把边远偏僻、生存条件差的地区的村民迁出来,搞异地开发,是扶贫中一种切合实际的模式,它在富裕了村民的同时,又开发了荒山资源。”
远远望去,山坡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和嫩黄的野菊花,刚摘过果的苹果树郁郁葱葱,一片生机。李副主任告诉我们,到春天时这里更美了,粉红的桃花和雪白的梨花、苹果花全开了,漫山遍野,一团团,一簇簇,引来恋人一对对,昔日的荒山坡变成旅游风景区。到了盛果期,满山的果树至少可收入50万元,那时,我们这个集体就更富裕了。



-----------------------
阜平县扶贫办主任张永文拉着记者的手说:“我搞扶贫工作10年来,这是头一回接受专门的扶贫采访。”
《新闻扶贫行》之六刊载于1996年11月4日《保定日报》。
李新功走新路再立新功,许成勋守成规一事无成
一道之隔,家境迥异
本报记者 王铮 宋刚 朝辉 宇青
10月22日上午,我们一行人来到地处浅山丘陵地区的曲阳县北次曹村采访,这是一个正在走出贫困圈的村。采访中发现村里有这样两个家庭:一路之隔,两种境况,一个家庭6口人,年人均收入超千元,另一个4口人,年人均收入不足500元。同是中年劳力,同样在家务农,而且两个家庭的男主人均具初中文化,为何贫富反差如此之大?
为找出原因,我们分别到这两个家庭进行了详细采访。在已经脱贫致富的李新功家,我们看到院里养着4头牛、3头猪,还有一个十儿平米的烤烟房。男主人招呼我们坐下后介绍说,我是从1986年养牛开始逐步脱贫致富的。以前全家6口人全年的收入也不足千元,为帮助我们脱贫,县民政部门拿出3万元扶持村民养肉牛。我自己连凑带借一下子投入了5000多元,买了6头小牛饲养。结果当年赚了4000多元。当初不支持养牛的老伴也来了兴趣,从此,夫妻俩同心协力搞起了养牛。不懂的技术找养牛大户学习,不懂的知识就到县科协等部门请教,还买了《肉牛饲养技术》等一些养牛的书籍。他们边养边学,不断发展,1992年最多时养了12头牛。从1986年到去年底他们已经出栏肉牛40多头,获纯收益6万多元。

记者问李新功:“这两年养牛不赚钱,村里许多人都急着卖牛,你为什么还养?”他笑笑说:“价格有高有低,行情有涨有落,这是市场变化的规律,现在肉牛市场疲软,总有好转的时候,不能只看眼前一时利益。”这位刚刚摆脱了贫困的农民虽然不可能掌握市场,但他对市场有了一定认识、了解,知道发挥优势围绕市场搞经济。
在主人的邀请下,我们还参观了他为两个儿子盖的新房,10间高大的砖房,连围墙也全是砖的。他还告诉我们,他正准备安装电话,为的是便于了解外部信息,掌握市场行情。
当我们来到只一路之隔的许成勋家时却是另一种境况:全家4口住着三间旧房,连围墙也没有,唯一值钱的衣柜已破旧不堪,36岁的男主人看上去好像有四十大几了。村支书许国朝说:“别看这房子不好也不是他的,是借住一位在外工作的乡亲的。”在记者追问下,许成勋向我们介绍了他家的状况。他的主要经济收入就是种地。他家种10余亩地,地不少,但基本上都是等雨种,靠天收的贫瘠薄地,而且只种粮食作物,一年各种收入全加起来也超不过2000元。我们问村干部是如何帮助他脱贫的,许支书说:“1986年我们就让他养牛,他怕牛得病,养不好,死活不干。后来有好心的乡亲劝他养牛,并借给他钱,他仍然是怕赔了本,还不起钱,所以他一直没有养牛。”
李新功适应市场,善抓机遇,通过养牛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而许成勋墨守成规,没有摆脱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怕这、怕那,错过了养牛的好机遇,而且他也未发挥地多的优势,依靠种植业脱贫致富,他仍在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中艰难挣扎。在同一经济条件下,两种思想观念,产生出两种不同的经济效果。因此,摆脱贫困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新闻扶贫行》之七刊载于1996年11月6日《保定日报》。
唐县黑角村村民历经10年艰苦创业,绿化了荒山,摆脱了贫困,他们发自肺腑地说:
关键有个好支书
本报记者 王铮 宋钢 朝辉 宇青
10月24日上午,我们刚到地处深山区的唐县羊角乡黑角村,就被村会议室里传出的吵闹声所吸引。仔细一打听,原来是村里30多名果树能手刚从顺平取经回来,在为林果的下一步发展规划争得面红耳赤。
“致富不致富,关键在领路”。采访过程中,村民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他们的支书是位好带头人。
在村办公室,我们见到吴大德。这位连续两年被评为“县十佳支书”、去年又获省劳模称号的老汉虽只有48岁,看上去略显苍老。他解释说,“昨天晚上9点多才从顺平回来,人们的劲头十足,这不,一大早又都赶到村委开会来了。”

1984年,36岁的吴大德就任黑角村支书。当时,村里是清一色的小石头房,村边的石头山上光秃秃的,连棵树也没有,水浇地每人不足半亩,年人均收入只有100多元。乡亲们都说,“啥时玉米糊糊能填饱肚,我们也就满足了。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老辈子就留下这么座荒山,干脆就在山上做文章。几个村干部一合计,确定了“以发展林果为主,绿化荒山荒地”的思路。村里为此制定了激励机制:率先在全县拍卖“四荒”(荒山、荒坡、荒地、荒滩),谁开发谁拥有,并有转让、继承权,100年内不变;承包责任田30年内不变。”
虽然有了优惠政策,但村民们迟迟不见动静,吴大德明白:这是在看他呢。二话没有,他带上玉米饼子、咸菜,拉着小驴车上了山,每天天刚蒙蒙亮就去,太阳落山后才回来,自己栽不过来 了,就雇人栽。1985年1年,他栽杨树1700棵、柿子树100多棵、槐树500棵。
领导带了头,群众有奔头。看支书栽了那么多树,群众心里踏实了,也纷纷效仿。到冬天,不少人手里多了个蓝皮本——经县公证处公证的“林木公证书”,谁家栽了多少树上面记得清清楚楚。
一方带动一片。原来对此不信服的村民也开始行动起来。有个叫吴马存的村民开始时净说风凉话:“吴大德是干部,他这样做是在自己脸上贴金呢!”等到3年后,看到别人家的柿树上真挂满累累果实,他才着了急,也风风火火干起来。现在他已栽种了七八十棵柿树。
为发展林果,村里还规定:党员、干部每年至少栽100棵果木,并将此作为入党、提干的先决条件。乡亲们把他们称为“绿色党员”和“绿色干部”。
吴大德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说了算,定了干,遇到问题也不能变。凭着一股恒心和韧劲,他四处奔走筹措资金。1987年,村里投资5万多元盖起一座二层教学楼,在全县345村办学校中拔了尖;1990年,投资近4万元,使家家户户通上自来水;1994年,投资60万元同曲阳合办了一个铁矿厂;今年又筹资10万元修好1公里油漆路……为改善村里的设施,他跑了多少路,吃了多少苦,只有自己才清楚。
一位村民很激动地对我们说:“为了这个‘大家’,支书把‘小家’舍弃了,他自己的地春天忘了种,秋天顾不上收。”
顺着山坡向上走,我们发现山地被利用得如此之妙:凡有平地的地方就会有挂满红叶的柿树。放眼望去,满山郁郁葱葱,让人难以相信。10多年前还是光秃秃的一片。吴支书告诉我们,现在1.6万亩山场,已绿化1.15万亩,光柿树就有5万多棵,杨树、槐树不计其数。从顺平回来后,他正打算发展一个富士苹果经济沟;规划几个柿子果园;伐掉一部分用材林,为果树让路;再轰点儿平地……“我的打算还多着呢。” 他说这话时,脸上带着憧憬的微笑。


(除稿件,其余照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