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邂逅的第一缕酒香,源自散酒。
小时候,我住在村子里,那时乡亲们的生活仅够维持温饱,日子过得并不富足。每日在田间辛勤劳作后,大家也丝毫不敢让自己有片刻停歇。不是忙着照料家中饲养的牲畜,就是捣鼓那些农具,或是跑去县城打些短工,生活的疲惫如影随形。

那时,电视尚未普及,村子里仅有的几台还是黑白电视。即便把接收信号的线杆子立得再高,也只能收到一个频道,而且不到晚上,轻易不会打开。村里实在没什么可供消遣的娱乐活动,喝酒便成了乡亲们难得的休闲方式,长此以往,人人都练出了不错的酒量,可奇怪的是,却很少有人会喝醉。这是为何呢?因为喝醉的代价可不低,想要喝到醉,起码得消耗一斤酒。在当时,家里能毫不犹豫拿出钱买一斤酒给男人喝的,那绝对算得上村子里条件优越的上等人家了。再者,大家都秉持着财不露白的观念,即便真有人喝醉了,也不会对外声张。

村里人喝的酒,清一色全是散白酒。家家户户都备有一个专门用来装酒的塑料桶,这种桶带有盖子和提手,在我们当地,大家都叫它 “卡子”。这 “卡子” 本身自带计量功能,一桶能装五斤酒。要是谁要去县城办事,自行车上准会挂着自家的,或是帮亲友捎带的 “卡子”,到了县城,必定会前往酒厂,在那儿排上半个小时的队,就为了打上一桶酒。

县城不是想去就能去的,可酒却不能断顿。要是家里临时没酒了,大家就会去村里的小卖部打上一瓶。小卖部的酒比县城卖得贵,一瓶是一斤装。乡亲们平日里吃饭时,也就喝上一两口,权当是应个景、解解馋。当然,也有一些人专门在小卖部买酒,原因无他,在这里买酒可以赊账,等到秋后再一并结账,对经济不宽裕的村民来说,方便不少。

从县城把酒买回来,或是从小卖部打上酒,大家在路上碰面时,总会相互约酒。有的人是真心实意地邀请,拉着对方就走;有的人只是客气一下,嘴上说一句 “来喝一杯”。至于这其中的真假,也没人会去深究,大家图的就是个热乎劲。

酒厂售卖的散酒,都是从大罐子里直接接出来的,就跟自来水管放水似的。卖酒的工作人员那表情,傲娇得很,要是不认识,连话都不愿多说一句。你要是有啥问题,也只能自己憋在心里。不过,虽说他们态度不咋地,但往卡子里灌酒时,可一点都不含糊,每次都装得满满当当,眼看着就要溢出来,却又恰到好处,那熟练的手法,真堪比古代的卖油老翁。毕竟大家都是穷苦人出身,在钱财方面,谁都不敢有半分马虎。要是酒没给灌足,哪怕是再老实木讷的人,也会忍不住发脾气。

小卖部里的散酒,装在大酒缸里。那些酒缸也不知道有多少年历史了,个个黑得深沉。打酒的配套工具是漏斗和酒舀子,不过也有些上了年纪的老者,打酒时不用漏斗,嘴里叼着烟卷,手里稳稳地拎着酒舀子,一边和你唠着家常,一边不紧不慢地舀酒。别看他们动作看似颤颤巍巍的,可酒却一滴都不会洒出来,娴熟得很。

在城里打拼的人,若是自家独自小酌,通常喝的必定是散白酒。可一旦有客人来访,那就得拿出瓶装酒来招待。这并非是为人虚伪,而是人在经济拮据之时,往往会更在意那所谓的面子。面子这东西,说起来好像不值一文,可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它又最为珍贵。在过去空气都透着清新质朴的年月里,这值钱的面子里,满满地蕴含着尊重、善良、淳朴以及理解。

时光匆匆,许多年过去了,村子里的树木越发枝繁叶茂,可村子里的人却变得寥落冷清。如今,喝酒的人群里,喝散酒的人越来越少了,售卖散酒的店铺数量也大不如前。不过,唯一有所变化且令人欣喜的是,现存的散酒店里,酒的种类变得相当齐全。各个价位区间的,各种口味风格的,来自各个地方的酒,在店里都能找得到。价格高低任由顾客选择,店家态度也都十分和善。来店里打酒的人形形色色,有的人直奔廉价酒区,随手拿个矿泉水瓶子就当作装酒的容器,只为满足日常简单的饮酒需求;有的则是对酒颇有讲究的行家,不在乎价格高低,一心只为寻觅一口纯正的好酒;还有些人觉得散酒新鲜有趣,偶尔来买上一次,权当是给平淡生活添点不一样的调剂。

酒,自然有价格贵贱之分,人,在社会地位等方面也会存在差异。然而,不同生活水平的人在散酒店里相遇时,相互之间少了那种曾经会令人心里不舒服的异样眼神。在酒的面前,仿佛人人都站在了平等的位置,无关乎身份与贫富。这些散酒店,平日里似乎感觉不到有多少人光顾,其实只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没有留意罢了。实际上,它们大多经营状况良好,拥有一批忠实的固定客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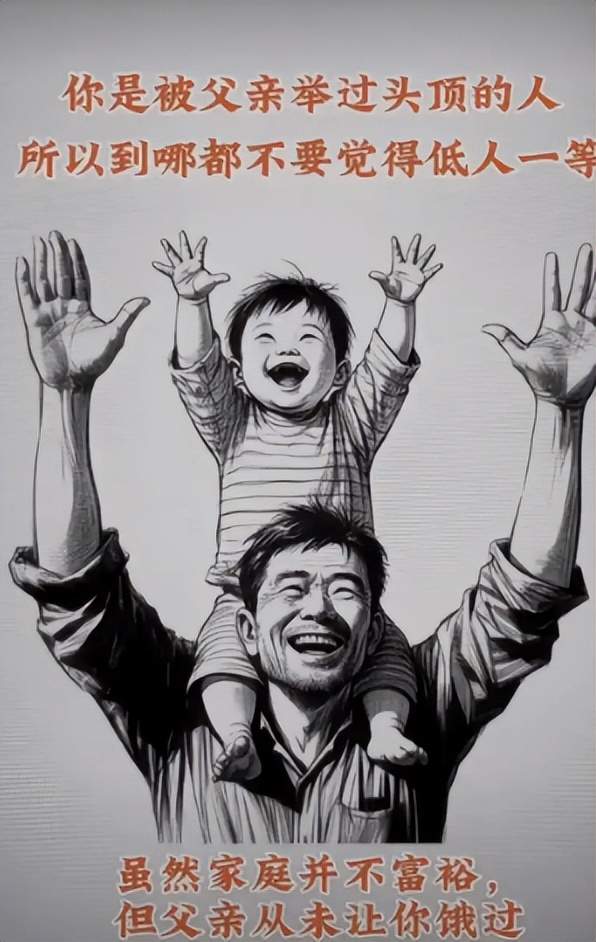
有时,我会特意陪着父亲去散酒店打酒。看着店家一勺一勺地把酒舀进瓶子里,那一刻,时光好似悄然倒流,我仿佛又回到了儿时。那时候,每次去打酒,父亲总会紧紧拉着我的手,而我则满心欢喜,蹦蹦跳跳地抢着要拎装酒的瓶子。如今,角色发生了转变,变成了我拉着父亲的手,父亲脸上洋溢着满满的笑意。这酒啊,不管最后喝还是没喝,仅仅是这打酒的过程,就已经让人沉醉其中,心生无尽感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