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案件回顾
导语:作为妻子的合法配偶丈夫被残暴地打死了,偷吃禁果的她和他被依法处决了。他们终究残途同归,谁也没占便宜……
1995年12月28日。摩托开路,警报呼啸,荷枪实弹的武装刑警,贴满惊叹号大标语的卡车上押解着五花大绑的一男一女。女的二十多岁,穿着件白底红花的尖顿长袖衬衣,头发松松地盘在头顶,脸色苍白,嘴角微微下垂。和她并排站在一起的男人约四十岁,平头方脸,浓眉大眼,满嘴络腮胡子。他们的背上各插着一块又宽又长的死犯牌子,白底黑字加红杠,十分醒目。标志上分别写着:枪决故意杀人犯吴惠芳、枪决合谋杀人犯唐皋山。
汽车缓慢地行进,街道两旁站满了密密匝匝的人群。刑车上的男女犯人时而目光对峙,时而左顾右盼。神情自若,不惊不诧。

法律是威严的。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是不容侵犯的,毁人者制造了自我毁灭的悲剧,付出的代价是相当昂贵的。如果人们想从中悟出一点生活的教训,那么有必要对这恶性案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作一番了解。
吴惠芳出生在成都大邑县悦来镇星火村,她天生丽质,聪明伶俐,自幼喜欢新事物、羡慕别人读书。1978年,她年满十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背上花布书包。
比起同学来,她年纪偏大,自然懂事最早,读起书来自觉性也特别地高,所以从进校门那天开始,成绩就名列前茅。加上她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逗人喜爱的瓜子脸,垂在胸前的又粗又长的独辫,她博得了教师们的喜爱和同学们的钦慕。
几年后吴惠芳考上了初中。当吴惠芳第一次读到那本皱皱巴巴《少女之心》时,她才见识到“世界上竟会有这样迷人的文学作品”。她爱不释手,如饥似渴地读着,抄着,随着书中故事情节的发展,她那张青春的脸上,泛起阵阵的红晕,心跳加快,两耳发烧,脑子像青潮激荡,久久难以平静。
于是,男女同学开始眉目传情,开始传递条子,用书上看来的语言大胆地表达海誓山盟。在不良读物的媒介下,诱发了对异性的追求。就在那个春暖花开,蜂飞蝶舞的季节,在放学回家的乡间小道上,一对对男女同学隐入那一片片金黄色的油菜田里,对这种如痴如醉的放荡,他们还给取了个极富诗情画意的暗语,叫做:赶菜花会。

吴惠芳从此陷入了情恋的漩涡。 成了“菜花会”会长。一年之中,她恋了好几个男生,由于她的姿色,由于她的风度,还由于她开朗大方的性格,在她周围,总是紧跟着那些年龄较大的男同学。由于年纪太轻,她并不知爱为何物?所以,她总是火一样地爱上这个,又电一样地爱上那一个。同学们背后议论她说:猴子掰包谷,掰了一个丢一个。
吴惠芳的理想是初中毕业以后上高中,创造条件,跳出“农门”。可是,由于父母百般阻挠,加之家庭经济拮据,她梦寐以求的宿愿终于破灭了。
吴惠芳终于回到了她那四周翠竹环绕的家里。回家后,慕名前来求婚的农村青年络绎不绝。可是,对众多的求婚者, 包括干部公子,她一律拒之门外。父母责怪她眼光太高,舆论说她目中无人。其实,她早已把丘比特之箭射向了那个同窗学友金仲。因为他们之间曾有过一段青梅竹马的交情,她曾慷慨地在菜花地里把自己的贞操第一个交给了他。
可是,当金仲被招收到某地粮食局工作以后,由于城乡差别的客观存在,金仲忘了旧情,向她投来白眼,在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上写下了:“天涯何处无芳草”,“祝你幸福”。她伤心地哭了一场,万念俱灰,只有屈服于命运的驱使,听任父母的安排。
不久,邻村的黎全生托人前来求婚。吴惠芳虽和此人没什么交道,但见过两面,知道此人其貌不扬, 文化很低,个头矮小,说话结结巴巴,在她的心目中,他不过是个“武大郎”而已。但吴惠芳的父母都知道他有手艺,又到建筑队打工,是一名三级技工,而且双方年纪也相当。于是,父母做主,订下婚约。
吴惠芳哭过,闹过,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她身不由己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屈从了父母的意志。
吴惠芳被迎进了黎家。拜了堂,就被簇拥进洞房,她从此结束了自由自在的姑娘生涯,和千千万万的农妇一样,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劳动,充当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

新婚,这是多么甜蜜,多么幸福的字眼,蜜月,这能引起多少神思,多少神秘,多少罗曼蒂克的幻想和憧憬?可是,对吴惠芳来说,伴随她的却是空虚、忧伤、苦恼和恐惧。“骏马可以驼痴汉。美妻难伴拙夫眠。”曾欲情似火的她,突然感到冷漠和厌倦。
新婚燕尔,红烛未烬,夫妻予盾就公开激化了。黎全生虽不爱说话,但个性却极刚强,他常指着吴惠芳的鼻子骂:“你别以为自己了不起,川西坝子的姑娘多得很。”他愤愤不平,蜜月未满就背上行装,到云南修建工地去了,抛下新婚的妻子和他在她肚中埋下的种子。
黎全生一去两年,中途偶尔回家,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和妻子的关系并未改善,对已能叫爸爸的小女儿也冷若冰霜。
吴惠芳寡居在家,孑然一身,白天下田干活,或忙于家务,倒还不觉得孤独,每当夜深人静,就不免暗自伤神。
为了寻求心理上的刺激、慰藉,吴惠芳养成了看电影的习惯。无论附近的哪个村庄放映电影,无论这电影她看过还是没有看过,她都要到场,都要看入迷,该哭就哭,该笑时笑。每当银幕上出现对对倩影,互相亲呢。拥抱接吻……她就感到心簇摇动,感到陶醉、幸福。她怨恨那个“不懂人性的丈夫”,更埋怨自己走错了路,她多么希望能结识一个能够理解自己的知音。
知音就在眼前。
电影放映员唐皋山,走南闯北,见识广泛,生活经验丰富,从部队退伍返乡后,曾任乡干部,1969年担任本乡电影放映员。他思想开放,紧跟时代潮流,为了提高票房价值,适应农村广大青年男女的爱好,他打通了电影公司的关系,经常优先租回影片,巡回放映,所到之处,备受欢迎,被农村广大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尊称为“唐电影”。

吴惠芳自然成了“唐电影”的忠实观众。她不光喜欢看“唐电”放的电影,更喜欢听“唐电影”讲的电影故事。“唐电影”仿佛看完了全世界所有的电影,他经常讲得绘声绘色,手舞足蹈。
“哎!可惜我们生错了地方。”她一声长叹,显出无比的悲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唐皋山,她说的这些话既是心声的流露,又是对唐皋山的一种探试,一种挑逗。
“其实,在大城市,在成都,她到锦江边上,到舞场去看看,那些男女,哪个不是旁若无人的搂腰,拥抱,事在人为嘛。”唐皋山一边说着一边把目光投到对方。
“喂!你到成都抱过女人没有?”吴惠芳卟哧一声笑了。
“我可不敢。”
“你经常在外边跑,你那家子(妻子)放心吗?”
“她有什么资格管我?我们是父母包办结婚的。我们毫无感情,我看到她那怪相,就想发呕,要不是因为上面管着,我早就把她踢了!”
“嗯,你骗人!”吴惠芳娇嗔地微笑着说,并同时用中指在唐皋山额头上点了一下。
唐皋山趁机捉住她指头,用双手紧握住她的手,说:“惠芳,我们交个朋友吧?”
“你……哈哈哈……”她身子一歪,很响地在他脸上吻了一下,跳起来,跑开了……

这是个漆黑的夜晚,没有风, 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一道黑影在竹林中穿梭着,悄悄出现在一座农舍门口,黑影轻轻地敲了五下门,木门立刻无声地旋开,黑影闪进屋后,木门又无声地旋上了。
黑影就是唐电影。
从此以后,吴惠芳的房门夜夜都给“唐电影”留着,她的精神感到充实,精力也变得出奇地旺盛,再也不感到孤独和寂寞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唐电影”是全乡老幼皆知的头面人物,他的一举一动,她们的任何反常行为,都会引起群众的注意。自然,关于他和她的风言风语就像瘟疫一样传开了。
为了掩人耳目,这对“野鸳鸯”绞尽脑汁,想构筑一座避风港,把无正当的接触变为名正言顺的交往。
吴惠芳煞有介事地来到公婆跟前:“她爷爷,奶奶,我们小蓉经常半夜发梦癫,挫牙齿,出虚汗,吃药打针都不解决问题,我们就这根独苗,你们看咋个办?”
缺乏科学知识的公婆,深怕孙女中了邪,忙说:“马上找个仙婆看看。”
“我已请过江菩萨了,她说要拜一个多子多福的老汉儿做干爹,才能避邪,消灾免难。”
“事不宜迟。”公公说,“对!马上准备香脸洒莱,摆在公路边上,等太阳当顶,有由北向南过来的男子汉,马上给他叩个头,请他赏脸,吃了洒菜,拜为干爹。”
吴惠芳立刻风风火火地回到家里,准备好早已准备好的香脸洒菜,牵着女儿,伴着公公婆婆来到柯边公路上等。
太阳刚当顶,一辆载着放电影器材的蓝色摩托车风驰电掣而来。
“就是他!”公公说,他虽然没看清骑摩托的人是谁。
吴惠芳立刻举起手来。摩托停下来,车上跳下唐电影。
“小蓉,快给干爹叩头。”吴惠芳说。
听话的小蓉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给唐电影叩了三个响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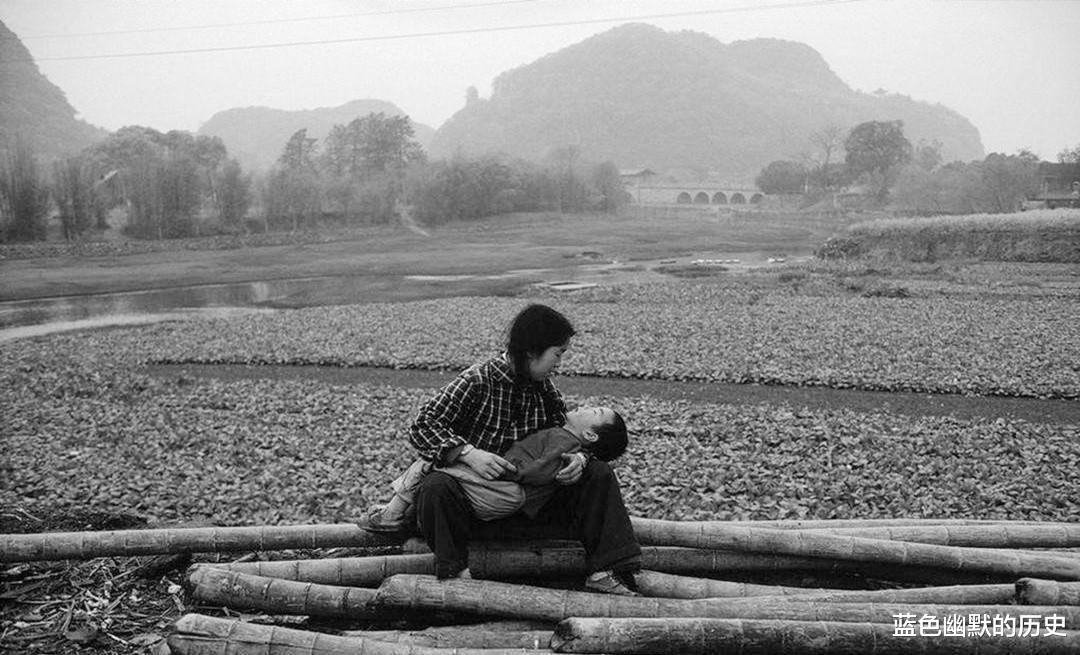
一幕吴惠芳导演,唐电影创作的喜剧。
从此以后,唐皋山开始大摇大摆地出入黎家了。看望干女儿和亲家母,这是名正言顺的事情,看谁还敢说什么。蒙在鼓中的公公,婆婆还在为孙女能过继给这位知名人士而荣耀呢。后来,黎全生回家后,也为能有这个干亲家而高兴了好久。
小蓉的生日到了,“唐电影”备了厚礼,前往庆贺。黎全生无意中谈起需要整修房屋,但经济力量不足时,干亲家立刻慷慨解囊,赞助1000元。为了帮助亲家母发展副业,唐皋山四处联系,及时购贷回优良兔种。农忙季节,唐皋山完全忘了自己家里也承包有责任田,全心全意地泡在吴惠芳的责任田里劳作……
渐渐地,在家干完农忙活的黎全生对唐皋山这种异乎寻常的关顾有些怀疑了。每当看到吴惠芳与唐皋山在一起时那副眉飞色舞的劲儿,心头就不免酸溜溜的,总感到不是滋味。可是,由于一无确凿证据,二是吃人口软,终不便启齿。农忙完后,他揣着一个疑团又离开了老家,回工地去了。
再说吴惠芳自黎全生走后,又如饥似渴地和唐皋山搅到了一起,沉浸在无境止的欲海里,真是“盐巴粮食,不吃不行”了。她连做梦也在盘算着如何才能和唐电影永远生活在一起,再不分开。
一天半夜,邻村有个小偷,半夜翻墙进吴惠芳家,东西没偷到,却发现了唐电影和吴惠芳的丑事。于是,这件丑事从外村传进本村,以最快的速度,钻进了每个村民的耳朵里。天生喜爱传播桃色新闻的人们,从窃窃私语变为公开议论。

桃色新闻不胫而走,传到外县,传到省外,黎全生怀着一腔愤怒,从云南工地匆匆赶回,见到妻子,二话不说,先“叭叭”两记耳光,接着破口大骂,拳脚交加。
吴惠芳可不是那些水做的女人,一挨打就哭、就下跪,她不躲不闪,厉声责怪黎全生:“你这不讲良心的东西,一走就是一年半载,家里无人照料,人家干爹来帮个忙,你倒听信谣言,抓屎糊脸!”
“我宁可让庄稼烂到地里,也决不要这种居心不良的人来帮忙!”黎全生怒不可遏。
……
一场殴斗和争吵之后,吴惠芳冲出家门,到成都投奔亲戚去了。她一去半月不归,留下小孩,家畜无人照管。弄得黎全生叫苦不迭。他本想通过暴力,使妻子就范,从此与唐电影两断,做个贤惠妻子,谁知反倒加速了矛盾,全部家务落到了自己头上,家里成天鸡叫鸭叫,孩子哭号,日以继夜,不得安宁。他就有些后悔了。他开始领会到这些年来,妻子一人在家遇到的种种困难。他夜不能寐,反复思索,最后终于决定原谅妻子。
“如果离了婚,这个家就散了。今后怎么办?安个家不容易啊!”黎全生想。
考虑再三,黎全生托表弟到成都,请吴惠芳回家。吴惠芳因怀念女儿,只好和表弟一起返回家乡。
回家后,她对黎全生不说不笑,冷若冰霜,视为路人,更不让他碰一下身子。黎全生耐着性子,陪着笑脸,对吴惠芳百般体贴,想感化她,但一直没有效果。

一天,黎全生突然接到工地上发来的一封加急电报,要他立即返回工地不然就要另派他人代替其工种。黎全生不敢耽误,决定启程。第二天出发前黎全生和吴惠芳吵了起来,黎全生动了手,结果闹到乡政府。乡政府一位负责人对他说过:“你安安心心去工地。我们调查一下,如果老唐和你妻子真有那事,我们会批评,处分他们的,也会把处理结果告诉你的。”于是,黎全生急忙赶去工地。
就在黎全生离开的当天晚上,唐皋山又睡上了亲家母的大花床,他带着几分忧郁地说:“我一天见不到你,心里就发慌,今后怎么办?”
吴惠芳也说:“我永远离不开你。我挨打受气,忍辱负重,就因为心中有一个你。如果要离开你,我宁可去死。为了我们永远生活在一起,我决定申请离婚。”
唐皋山思索了许久,苦离地说:“你有第三者是不准离婚的。”
吴惠芳咬了咬牙齿,坚定地说:“想个办法弄死他!”
“不行,杀人是要抵命的。”
“不要前怕狼后怕虎。”
黎全生回到工地上,烦躁不安地等待着乡政府的答复。二个多月后,乡上依然渺无音讯。黎全生这时才估计道:肯定因为没有证据,所以乡政府才没做任何处理。他想起了“捉贼要拿脏,捉奸要拿双”的道理,决定回家捉奸。

1995年9月底,秋风送爽,稻谷飘香,成熟的庄稼急需收割,建筑队的成员大多数来自农村,建筑队决定放假,让队员们回家支务。黎全生立即打点行装,登上归途。火车到达成都已是10月6日傍晚6时。尽管长途跋涉,饥肠辘辘,他也无昼在城里逗留,迅即找到归程的长途客车,回到家乡。
回到村口时,刚好晚上9点过5分。这时,村外的公路上,人迹稀疏。他选了个隐蔽的地方,窥视着那条通往自己家门的乡间小道,聚神会神,目不转睛地等待捉奸。十时许,夜幕已严严实实地覆盖了大地,天边闪着几颗星星。忽然由远而近地传来一阵熟悉的脚步声,接着“咯吱”一声,房门处闪出一片灯光,接着又是“咯吱”一声,灯光被关进了门后。
黎全生心里咚咚乱跳,他很清楚进门的是谁,他咬紧牙关,攥紧拳头,猫着腰向房后的墙壁靠近,将耳朵贴在墙上细听室内的动静……
一会儿,狂怒中的黎全生箭一样射到门口,开始用力擂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别怕,我去开门,如果他敢动手,我们就弄死他!”
敲门声稍停,门外传来呼叫声:“惠芳,开门呀,是我!”
吴惠芳穿好衣服,让唐皋山躲到床后,慢腾腾地出去,不耐烦地说:“半夜三更,进院子也不喊,我还以为是榛客来了呢!”
门刚打开,黎全生已跳进屋来,大吼一声:“为什么不开灯?!”黎全生扯亮电灯,室内立刻明晃晃的,但不见他人。
他先弯腰看看床底,没有人。又到米坛边看看,也没有人,再回过头来,发现蚊帐背后站着唐皋山。

唐皋山这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站了出来。
黎全生火红的双眼燃起了熊熊的烈焰。他站在屋子中央,两手往腰间一叉,咆哮道:“今晚,我看你们昨个说!”
唐皋山此时此刻也顾不得许多了,没好气地答道:“你要咋个说就咋个说!”
吴惠芳接着嚷道:“他就是看到你回来了才专门来找你的。”
唐皋山和吴惠芳的态度,无疑是火上浇油,黎全生怒不可遏,一把抓住她的头发,狠狠两记耳光后,将她往堂屋拖去。吴惠芳高呼:“打死人了,快救命呀!”
就像接到了行动的命令,唐皋山立刻追了上去,凭借自己的身高体壮,双手一个紧箍,将黎全生紧紧抱住,用力一摔,黎全生立刻摔倒在地。他刚奋力爬起,又被唐皋山按倒在地,一手封住了喉管。已经挣脱身子的吴惠芳,使出其女人惯用的绝招,伸手去揪黎全生的下身。抓住后用尽全力,一阵猛扯,黎全生疼痛难忍,停止了搏斗,几乎昏厥过去。吴惠芳见他已失去反抗能力,才松开手,从门后拿起顶门的锄头,叫唐皋山把头偏开,她抡起锄头,对准黎全生的脑袋狠狠地砸下去,只听“咣”一声,黎全生的头骨进裂,身子抽搐几下,不再动弹。唐泉山恐其未死,又接过锄头,对尸体猛击数下,直至确认他已经死亡。

蓉蓉被惊醒了,跑出房间,站在门边,被血淋淋的场面吓得浑身颤抖,大声痛哭,边哭边喊:“不要打我的爸爸。不要打我的爸爸……”
吴惠芳低喝一声:“不准哭!”然后抱起她,把她送回寝室,放在床上,反扣了门。
两名凶手杀死黎全生后,为了藏尸匿迹,取来一条三尺长的尼龙绳,将死者的颈子连拴数道,然后用黎全生本人的兰涤卡衣服包住他喷血的头,趁着夜深人静,唐皋山将尸体背上,出了院门,吴惠芳紧跟在后,他们沿着杨柳河行程三里,来到一座水力发电站下游八十米处,将尸体抛入激流中。
他们并肩携手返回后,将室内的血迹连夜刮洗干净,睡至天明,方才离开。
1995年10月12日上午,黎全生所在地的乡长和村党支部书记到县公安局报告:本乡九村十一组的建筑工黎全生, 自外地归来后,不见踪影,至今下落不明。
次日,在临县牧马河中发现一具尸体,虽已高度腐烂。但仍能进行辨认。经黎全生的孪生兄弟及姐妹到现场识别,确认死者就是失踪的黎全生。
经法医检验尸体,发现死者头部颅骨呈粉碎性骨折,为钝器击伤。鉴定为:死者系被人杀死后投入河中的。
经侦查人员两天两夜的紧张侦查,终于在死者家中发现杀人现场。立即拘留了吴惠芳、唐皋山。10月14日,两名罪犯在证据面前,不得不供认了其谋杀害黎全生的全部事实。
他们下了刑车,被推过了白色的警戒线。这时,他们的腿在发抖。枪响了,清脆的枪声结束了他们还算年轻的生命和我的叙述。他们的污血转眼就没有了。

杀人偿命,古已有之,在封建社会,犯“谋夫案”的女人是要被凌迟处死或遭活剐的。哪有今天挨一颗子弹痛快。
须知,听惯,看惯了川戏的吴惠芳是不会不知道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故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