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众多封疆大吏中,李卫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声名最为显赫者之一。多数受众对李卫的认知,往往源自影视作品。然而,真实历史维度下,李卫究竟是怎样的人物形象,值得深入探究。

【开挂入仕的李卫】
李卫,表字又玠,其祖籍为江苏徐州丰县,寄籍于铜山。康熙二十七年,李卫降世。在雍正一朝,李卫与鄂尔泰、田文镜并驾齐驱,同属彼时声名远扬的“模范”督抚之列,三人齐名于世,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部分影视作品的呈现中,李卫常被刻画为目不识丁之人,此观点实有夸大之嫌。事实上,李卫出身优渥之家,自幼便开启启蒙受教历程。然而,其于传统经史典籍的研习方面,禀赋欠佳,面对如《四书》《五经》这般的经典著述,往往心生畏难,甚至抵触之情。
诚然,李卫虽未饱读诗书,但绝非目不识丁之辈,其具备基础的读写能力。
在康熙五十六年,时年虚岁三十的李卫,通过捐纳方式获得监生资格,旋即被任命为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此官职品秩为从五品。这一情况颇为反常,盖因依据清代捐纳制度,就外官而言,捐纳所能达到的最高品级为四品道员;而对于京官,捐纳的上限则是正五品郎中。
尽管如此,捐纳入仕存在诸多限制条件。其遵循严格的逐级递升原则,即捐纳者需自八九品这类低级官职起步,而后依序向上晋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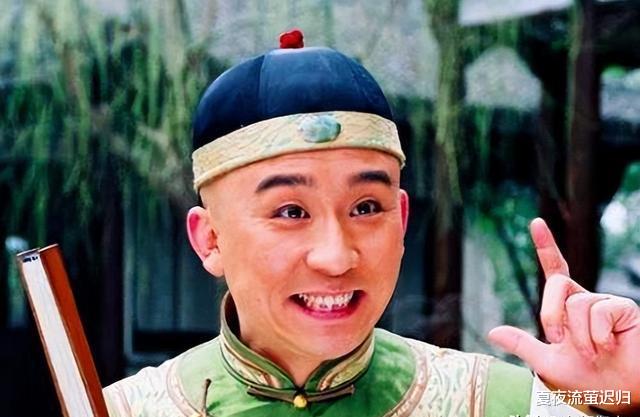
此外,通过捐纳途径入仕者,仅能获取“候补”资格。而欲得实授官职,实依赖诸多不确定因素。以从五品郎中一职为例,若无相当长时期的等待与机缘,绝难获此职位,通常而言,少则需历经数年,多则可能长达十年乃至更久。
基于相关历史背景及逻辑推断,李卫以捐纳方式入仕的时间确凿早于康熙五十六年。鉴于其汉人身份且毫无政治背景依托,在捐纳这一途径上,想必历经诸多波折与漫长过程。
据史料记载,关于李卫早期通过捐纳入仕的详情未被留存。其仕途伊始,便任职五品郎中。时隔两载,旋即擢升至户部广西司郎中一职。
需着重指出,于康熙统治时期,李卫与皇四子胤禛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私人层面的往来互动,绝然不同于部分影视作品所描述的那般,李卫身为胤禛“潜邸奴才”的关系。
康熙六十一年,雍正甫一登基,便将皇十三子胤祥封为和硕怡亲王。彼时,经由胤祥举荐,雍正帝敕授李卫为云南驿盐道之职。

从相关史料推断,在康熙执政时期,李卫与怡亲王胤祥之间极有可能维系着良好的关系。众所周知,雍正帝与胤祥情谊深厚,雍正对胤祥秉持着近乎绝对的信任。基于此,经由胤祥所举荐之人,势必会被雍正帝纳入“亲信”范畴,李卫大概率便属此类。
仅依靠十三爷的推举,尚不足以判定李卫是否具备成就非凡之潜力,其能否崭露头角,实需凭借实际功绩予以验证。雍正元年五月,李卫正式履职。次月,他便连续呈上三道奏疏,详尽地将一路之上所察风土人情、文武官员之操守以及盐政弊端等情形,一一奏明圣上。
旋即,对旧制盐课中的不合理成规予以变革,自雍正元年起推行“余盐归公总算”之策。经初步清查整顿,仅云南前两任盐政官员所追缴的积欠款项便达十一万余两。李卫通过清查盐政亏空这一举措,向雍正帝表达忠心,此举成为其获取雍正帝赏识的关键因素。
雍正二年二月,李卫获越级擢升,出任云南布政使一职,同时兼理盐务相关事宜。不仅如此,雍正帝还赋予李卫密折专奏之权力。需知悉,在雍正朝初期,密折专奏权仅为各省督抚所享有,布政使与按察使这两个层级官员,尚未被赋予此项权力。
雍正帝以打破常规之举,对李卫委以重任。彼时,李卫年仅三十六岁,且并非科举正途出身。如此殊遇,令李卫深感圣恩浩荡。自那之后,李卫矢志不渝地竭诚效力于帝王,秉持“唯君命是从,其他皆不足虑”之念,哪怕积劳成疾,数度咯血,亦毫不退缩,始终恪尽职守。

【一身坏毛病的李卫】
李卫之优劣特征鲜明,可谓泾渭分明,此特质与雍正帝颇具共通之处。因获雍正皇帝与怡亲王之青睐赏识,李卫行事勤勉奋发,展现出极高的工作热忱与积极性。
雍正对李卫的忠诚及办事能力极为信赖。然而,李卫未获进士出身,其性格中颇具躁烈之态,争强好胜,行事亦有失审慎。这些特质致使他常与上司、同僚产生龃龉,彼此关系趋于紧张。
雍正帝洞悉李卫之性情,常予以训导。李卫虽行事风格呈现出显著的“粗率狂纵”之态,然而,于雍正帝视角观之,其具备的“操守廉洁、勇于任事”之特质,显得尤为弥足珍贵。
雍正三年十月,李卫获擢升为浙江巡抚。时隔半载,其又膺命兼理两浙盐政。从客观角度审视,李卫展现出卓越的行政能力,在浙江巡抚之位上,政绩斐然。此政绩不仅令雍正帝嘉许,亦深得浙江民众赞誉。鉴于其政绩卓著,雍正五年十一月,雍正帝特为其专设浙江总督一职,且依旧兼管巡抚事务与两浙盐政。

李卫虽于任上建树颇丰,然而,其因自身修养欠缺,甚至偶有恃宠而骄之态,亦为雍正帝增添诸多烦扰。
雍正三年十一月,李卫领旨前往任职之地,行至清江浦时,按朝廷指令与河道总督齐苏勒就河工事宜展开研讨。然而,由于李卫在相关礼仪规范的践行上有所疏失,致使齐苏勒心生不满,由此二人之间产生嫌隙。
雍正五年,时任官员李卫自四川采购粮食。其间,他因不满湖广地区所征收的过境税额度过高,遂以公文形式进行问询。然而,此行为逾越了其职责范围,在官场规范中,这属于大忌之举。四川总督迈柱,正因李卫这一不当行径而心生恼怒。
雍正六年四月,李卫在负责马厂清查等事务期间,与杭州将军鄂弥达之间渐生嫌隙。而在此前后的时段内,李卫于履行自身职权过程中,同浙江观风整俗使王国栋、许容等人亦出现关系不睦之状况。
雍正六年九月,李卫堂弟李怀谨与李信枝于乡里行事肆意。彼时,李卫忧虑江南总督范时绎借该事端,于其家乡兴风作浪,对己不利。故而,李卫果断采取举措,将李怀谨与李信枝拘押并押解至浙江,拘禁于官署之内。直至雍正八年,范时绎卸任江南总督之职后,此二人方被释放,得以返回故乡。
范时铎绝非等闲之辈。从家世渊源而言,其出身相较于李卫,可谓天壤之别。范时铎作为范文程后裔,且备受雍正帝青睐。然而即便如此,李卫竟毅然决然地派遣人手前往江苏缉拿相关人员,足见其行事果敢,胆魄非凡。

事实上,此类例证不胜枚举。就李卫而言,其性格存在显著弊端。这种性格特质的形成,虽有先天因素的影响,但更大程度上是源于对雍正帝宠信的仰仗。
此外,针对李卫,亦有官员上奏弹劾,称其在管理下属方面存在疏失,未能严格约束。同时,其日常行为亦遭诟病,频繁涉足西湖游览,热衷观看戏曲演出。不仅如此,在节礼及生辰之时,他还接受他人馈赠。更为严重的是,在税收事务中,李卫竟采用白契收税之法,致使大量税款“征收入己,归公者寥寥无几”。
诸多因素致使雍正帝对李卫难以全然信任。然而,在雍正眼中,这些尚属细枝末节。真正触怒雍正帝的是,身为未通过科举正途出身的李卫,竟沾染了旧时地方官员上任伊始便拜访当地豪绅名儒的陈规陋习。其到任之际,为当地已故的名儒吕留良 “赠送祠堂匾额”,旨在博取 “重儒之美誉”。
在历史进程中,吕留良被雍正帝判定为具有“反清”倾向的人物。然而,李卫在行事之时,未充分权衡利弊,竟做出向吕留良赐匾这一不当之举。雍正帝于对李卫进行综合考量与评价时,颇为惋惜地指出:“李卫的弊端并非在于性情急躁,而在于自我约束不够严谨。”
雍正十年闰五月,李卫奉旨调离浙江,获署理刑部尚书之职。至八月,其正式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直隶地区与京师接壤,地理位置特殊。在直隶近京的州县,官员们履行公务之际,频繁遭遇来自京城权贵的干涉。面对此类情形,多数州县官员往往选择隐忍退让,听凭权贵随意指使。

大学士鄂尔泰之胞弟鄂尔奇,彼时官居户部尚书且署理步军统领之职。其行事乖张,平日里尽显骄纵之态,肆意妄为,屡屡逾越职权范围,对基层民众巧取豪夺,行径恶劣。尤为甚者,面对总督李卫呈递的关乎赈灾事宜的紧急题本,鄂尔奇竟无视事态紧迫,蓄意拖延,直至四五月之久方才予以回应。
雍正十一年九月,鄂尔奇凭借职权,不仅对家人违法行径予以袒护,还逾越自身权限,动用户部印牌插手房山县公务。此举激怒李卫,遂即上疏朝廷,严参鄂尔奇诸多不当之举。雍正帝览奏后,当即将鄂尔奇革除官职。然而,念及鄂尔奇兄长鄂尔泰在朝中所具影响力与功绩,最终特赦其罪,未予惩处。
因李卫参奏事宜卓有成效,依例可获议叙加一级之奖赏。然而,李卫并未接受此等褒奖,而是郑重恳请雍正帝收回成命,停止对其议叙。从这一行为来看,或可推测李卫此举意在表达对雍正帝就鄂尔奇一事予以宽大处理的不满情绪。
李卫行事能无所顾忌,即便是面对当朝首辅鄂尔泰亦毫无情面可讲,此皆归因于雍正帝对其给予的高度信任。

【一朝天子一朝臣】
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帝猝然崩逝。彼时,与李卫嫌隙颇深的大学士鄂尔泰获任为总理事务王大臣,肩负辅政之责。
李卫深感自身处境艰难,自觉已“结怨众多,招致怨尤,处于孤立无援之境”。值雍正帝驾崩之际,李卫于灵前恸哭,哀伤之情溢于言表。旋即,新帝弘历继位,适时召见李卫并加以抚慰。然而,李卫对于鄂尔泰所抱持的戒备态度,却从未有过丝毫松懈。
与雍正帝施政风格迥异,乾隆帝对李卫、田文镜二人观感欠佳。李卫身为前朝旧臣,于政务处理上尚算勤勉,亦有少许功绩,因而获乾隆帝别样看待。
步入乾隆时期,李卫所处境遇较之前已然式微。不过,因其长期任职地方要职,对官场之道渐有深刻体悟,深谙“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一政治逻辑。
基于此,李卫在性格上逐渐有所收敛,其言行风格较之前日,少了几分锐利,转而增添了谨慎与圆融的特质。在李卫的后半生,其政绩主要聚焦于营田与水利这两个领域。
乾隆三年孟夏,李卫身负河工与赈务之重任,因公务繁剧,积劳致疾。至仲秋,李卫于随谒泰陵之际,肝病猝发。迨至季秋,乾隆皇帝念其功绩,特敕太医前往为李卫悉心诊治,并恩准其解除职务,专心调养。

李卫于任上溘然长逝,尚未得返归故里。乾隆帝闻此噩耗,深表痛悼,敕令以总督规格予以祭葬之礼,并追谥“敏达”。至乾隆五年,李卫得以入祀直隶名宦祠与京师贤良祠。由此观之,李卫身后之遇颇为周全,其功绩大致获乾隆帝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