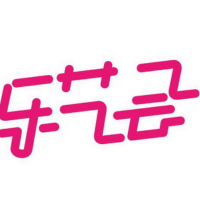二、捉人为戏与透索为戏
之前我们曾经阐述过,学者们早就关注到七圣刀这类砍头剖腹的幻术表演与祆教的关联。当然,这并不等于二郎神的来源就是祆神。唐代张鷟《朝野佥载》中记载了河南府胡祆神庙中每岁商胡祈福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的西域幻法。唐光启元年《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伊州祆庙祆主“因以利刃刺腹,左右通过,出腹外,截弃其余,以发系其本,手执刃两头,高下绞转"。宋代董逌在《广川画跋·画常彦辅祆神像》中就有对祆祠中群胡聚火祝诅,奇幻变怪,至有出腹决肠,吞火蹈刃的描绘。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南宋洪迈在《夷坚志》中记南宋民间的七圣祆队,在“阁山排军”中描述身为“七圣祆队”上首的饶州朱三。“臂股胸背皆刺文绣 , 每岁郡人迎诸神 , 必攘袂于七圣祆队中为上首”。吴任臣所编《十国春秋》中,曾有一条相关的记录:“(前蜀)帝被金甲,冠珠帽,执戈矢而行。旌旗戈甲,连亘百余里不绝。百姓望之,谓为“灌口祆神””。自然,有学者考订认为此祆字为衍字。但是,洪迈《夷坚志》中所记南宋民间七圣祆队的这个祆字,却是明确无疑的。

二郎神花钱 王帆藏品
可见与二郎神相关的七圣刀幻术与祆教祆主的幻术十分类似。巧了,在祆教氛围的“泼胡乞寒戏”中,恰好与七圣刀花钱中这个被捆翻在地的角色可以有巧妙的呼应。泼寒胡、苏幕遮作为西域习俗多被认为是由祆教徒带入中土。两者多有交融,而各有偏重。
唐代僧人慧琳在《一切经音义》“苏莫遮冒”条中描述云:
“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慈国,至今由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橃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象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或以泥水沾洒行人,或持绢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攘厌趂罗利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可见,唐代泼胡乞寒戏特征有四: 裸体、头戴面具、洒水以及用绳索捉人。而且是禳灾驱邪之俗,而陆昕所藏第二品七圣刀花钱中的穿下被捆之人,似乎也存在类似泼胡乞寒戏中“持绢索搭钩捉人为戏”的要素关联可能性,我们可以更加领会祆教中的七圣刀与祆教泼胡乞寒戏之间,也许也存在有着某种影响交融关系。假设这样的推理成立,我们也就可以更加深切地去理解本钱上的人,为什么既是被绑着,又赤裸,同时又不是捉妖治水主题,因为这也许是持绢索的捉人游戏,而这类泼胡乞寒的要素也被借用到了七圣刀的画面之中了,所以在这里绢索用以绑,游戏则非严肃的驱邪活动,而呈现了泼胡乞寒式的裸体。
这种生动而奇妙的关系还在当代社火活动中得到体现,据介绍,前述夏坊“七圣庙会”血社火活动中还有一项令人困惑的旧俗,为周边有游傩传统的地方罕见,如果吴姓村民拒绝或无力在庙会期间邀请戏班演出,夏坊村的夏氏大姓有权力用绳索绑缚吴姓负责人问罪。

泼寒胡戏在史料中又被称为乞寒胡戏,大致于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常在冬季岁末举行,早期无论胡汉皆裸露形体,泼水跳足,意为乞求寒冬顺时而至。从北周大象元年首次出现(《周书·宣帝纪》卷载七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十二月“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宫人内外命妇,大列妓乐,又纵胡人乞寒,用水浇沃为戏乐”)到开元元年被禁,从此其正式名称消失在正史之中。
由帝王带领欣赏泼寒胡戏的情况,在唐中宗时期也有两次。神龙元年十一月己丑,“御洛城南门楼观泼寒胡戏”;景龙三年十二月乙酉,“令诸司长官向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唐代睿宗时,皇帝亲自下诏作此戏,太子亦微服观赏,从而惹得时任左拾遗的韩朝宗上疏劝谏,劝阻传播乞寒胡戏这种粗鄙的夷狄之俗。
成书于九世纪的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记“婆罗遮”云:“(龟兹国)元日斗牛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蘩息也。婆罗遮,并服狗头猴面,男女无昼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为戏。焉耆国元日、二月八日婆摩遮,三日野祀,四月十五日游林,五月五日弥勒下生,七月七日祀先祖,九月九日床(一作麻)撒,十月十日王为猒法。王出酋家,酋领骑王马,一日一夜处分王事,十月十四日作乐至岁穷”。
可见,无论唐代慧琳记录的持绢索搭钩捉人为戏,还是段成式记录的行像及透索为戏,都存在用绳索钩捉人的游戏方式,这一点与陆昕所藏七圣刀第二品花钱画面上的被绳索捆绑之人的要素十分贴近。而且,持绢索搭钩捉人为戏,与行像及透索为戏,既然都是“为戏”,所以都惊人地一致地呈现为“表演”性的特色。似乎也可以为二郎神七圣刀的表演性作着某种有趣的注解。

二郎花钱 吾道鼠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