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对犹太的计算思维
与西方形而上学思维
的数学因素的关系的界划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三十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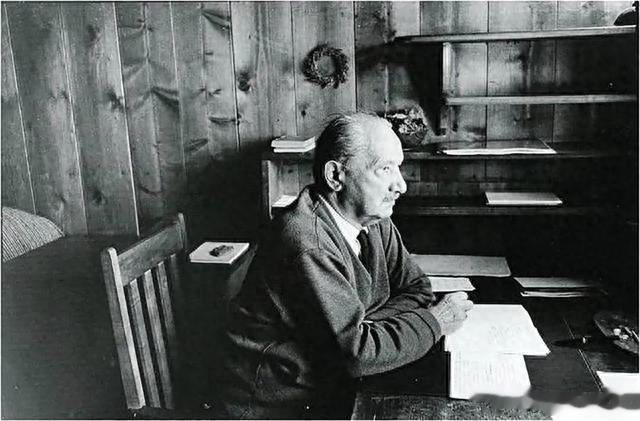
1
机巧在存在历史中的起源。
兼论古代的数学向近代的数学性思维的转变
海德格尔将机巧(Machenschaft)作为现代思想的存在状态的本现。[1]机巧虽然在科技时代登峰造极,其实并非产生自现代,而是在古代就有其根源。从词源上来说,Machenschaft跟 Machen(制作)相关。但 Machenschaften这个词在日常意义上表示“阴谋诡计”, 含有贬义,所以海德格尔说它表达一种“恶劣的人类活动和对此的谋划方式”。[2]海德格尔提出,它实际上还不是一种人类活动,而更应该看作是存在本现的一种样式,虽然它不是存在的完全本现,而且更倾向于非本现,但是它对存在的本现而言仍然是本质性的。机巧跟制作性思维密切关联。“机巧乃是制作和被制作者的统治地位。”[3]不过这种制作活动是在这样的存在解释基础上成熟起来的:存在状态是恒常状态和在场状态,存在者的可制作性在其中显现。不止是通常而言的被制作的物品,而且自然物也被看作由自身被制作的存在者。[4]这里隐含着西方思想在从古希腊开始的对存在的理解从自然(Physis)到技艺(techne)样式的转变,存在自身不再是自然涌现,自然成了被制作的-自我制作的。进而,当现代科技统治了人同存在者整体的关系之时,机巧“作为制作和被制作物的统治”[5]也成为隐而不显但起决定作用的存在理解方式。可见机巧的根源在于对存在的理解。由于存在者的存在被看作是一种恒常在场的存在状态,进而被把握为可制作性,在存在的日渐离弃状态中,机巧逐渐占了优势。
如果在当代机巧的统治显现为科学技术的统治,那么机巧在西方的存在历史中显现为什么呢?海德格尔称,它通过隐藏在别的东西后面而展开自身。“这似乎成了机巧的一个法则——它的基础尚未奠基——它越是决定性地展开自身——在中世纪和现代——它就越是顽固地和机巧地隐藏自身,在中世纪隐藏在ordo(秩序)和analogia entis(存在的类比)后面,在现代隐藏在作为现实性从而作为存在者状态的基本形式的对象性和客体性后面。”[6]在现代,机巧的藏身之所就是作为对象性和客体性的存在状态。机巧是技术的本质。技术性思维是当代思维的特征。海德格尔描述这种技术性思维为“为了控制和充分利用自然,转而从事理论自然科学的实际应用,”因此“物理学以及与之相随的整个现代自然研究,无非就是应用技术。”[7]理论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似乎并不使用机器,不用做实验,但贯穿了一种技术思维。而技术思维是以数学性思维、计算为基础的。
海德格尔提出,存在离弃状态的显现是:快速,计算,大量,在此意义上的世界和大地的摧毁。世界和大地都被荒废、破坏。天地神人都不在其位。[8]“计算”是存在离弃的最明显的表现,也是其特征。海德格尔提出技术的机巧通过计算取得其权力,“计算——首先通过以知识的方式奠基在数学中的技术的机巧,它获得力量;这里有主导法则和规则的模糊的前瞻,由此操作和计划、实验的可靠性;对如何完成的无问题性;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人对‘存在者’的确定无疑;不再能对真理的本质追问;一切都使得自己根据某种计算的状况被定位。”[9]在存在离弃的时代,计算成了主导法则和规则,它保证操作、计划和实验的可靠性。对于什么是存在者,什么是存在者的存在状态,都是根据计算来确定的。无需再问真理问题,计算及其正确性就是真理。存在离弃状态是存在的真理的历史中的一个独特的时代,时间很长,在其中真理不愿意透露自己的本质。这个时代避开任何本质的决断,放弃了标准之战。无决断表现为对机巧的不约束,甚至努力推进机巧和机巧的统治。所谓的伟大在这里表现为庞大之物(Riesigen)的畸形的大量,而所谓清晰性则是空洞之物的一览无余。[10]
数学思维和数学因素在这个机巧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数学因素并不是作为科技不可替代的工具而被强调,相反,数学因素是现代科学、现代形而上学的根源。[11]海德格尔指出,在近代,“这个方法的基本规则——数学的方法——现在同时变成了建立一门科学,或者更好地说是成为了建立基本科学的指导方法,这门科学考虑到一切可能的可知的东西,为了直接的洞识而准备好那些基本法则和最简单的基本概念。笛卡尔称最一般的基本科学为mathesis universalis(普遍数学)。”[12]这种方法进而成了近代以来形而上学的决定性的因素,数学方法不仅成了哲学乃至一切科学认识的外在框架,而且是其本质规定。数学决定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识,什么可以作为知识的对象。“哲学的内容受到数学性的东西如此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数学性的东西及其优先性已经预先决定了,什么是哲学上可知的东西,它应如何被获知。数学性的知识形式对于直到黑格尔的近代哲学而言不仅仅是为了装潢体系的外在的框架,而是其内在的法则,哲学的内容的开端以及同时真理的观念由此被规定。”[13]数学性思维统治了哲学,哲学也曾欣然接受数学性思维的改造,以求自身变得更“科学”:“虽然如此,哲学却不能看到这个法则的效果和厄运;相反,它却有真正的热情,一再试图‘将哲学提升到科学的层次’。”[14]
近代以来的这种数学因素在古代数学中虽然可以找到其来源,但是在本质上它们是完全不同的。Ta mathemata 是希腊人学习的一个分支,包括他们学习的数学,几何学,天文学,音乐等,这些领域都以数学为基础。毕达哥拉斯学派成员阿契塔斯(Archytas)称其前辈为“那些研究ta mathemata的人(τοὶ περὶ τὰ μαθήματα)”,并将科学的方法,尤其是关于数字,几何,音乐和星体的运动的学问的创新归于他们。[15]按照毕达哥拉斯学派,世界的本原是数和数的比例。数学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被认为是处理“ta mathemata(τὰ μαθήματα τῶν πραγμάτων)”的。[16]但自古代起,ta mathemata这个词所表示的毋宁是“科学”,某种真理性的认识。[17]海德格尔强调,古代的mathemata泛指可以教和可以学的东西。由于数学性的东西是在突出的意义上可以教和可以学的东西,所以这个词同时指数学性的方法。在古代这种知识是一种自足的知识,无关乎经验。人的思维和认识创造了数学对象和认识材料。所以获取这种知识的途径是“回忆”。[18]它包含两个重要元素:直观和推理。第一是直观到最基本的原则和命题,第二是从基本命题推理出其他命题。[19]这种知识形式“具有最高的普遍性”。[20]因为它具有直观的自明性和在此基础上的演绎法则的使用。
海德格尔指出,古代科学和现代科学的区别,不是后者有实验,用数学计算,而前者没有。在海德格尔看来,古代也有数学,也做实验。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古代和现代科学的不同理念。海德格尔批评了实证主义,他认为19、20世纪的实证主义虽然非常流行,被看作消除形而上学的利器,但完全没有理论深度。实证主义者盲目堆积材料,认为科学处理事实就足够了。而他们没有认识到,16、17世纪的科学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把握了真正的科学认识都是概念优先,事实只是用来论证概念和理论的。真正有创见、能发现的科学研究无不跟笛卡尔、牛顿他们所做的一样。[21]但这种赞誉之辞并非对笛卡尔的哲学在存在史上的作用的肯定。相反,海德格尔从笛卡尔那里找到了科学概念在近代转变的源头。在笛卡尔那里发生了一个理论决断,这就是普遍数学作为科学认识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对存在和真理的预先确定。真理是数学性的确定性,存在是数学能计算、可把握的东西。数学作为方法论和存在论的标准,决定了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海德格尔提出,笛卡尔的理论缺乏基础,因为笛卡尔没有进一步追问他的理论的前提,即没有追问存在和真理。笛卡尔不言自明地预先设定了存在和真理的意义,即数学性的东西所带来的确定性,而不加考察。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性的转折点有两个要素在起作用:1.数学性的东西为思想奠基,2.基督教的神学化。[22]海德格尔认为西方思想自笛卡尔以来是逐渐的没落,而非如同人们通常认为的,是对形而上学的重建。
古代以降以技艺(techne)思维代替自然样式来理解存在,随后这种思维通过基督教创世思想而得以成为主导性的存在理解方式,存在自身被遗忘,西方虚无主义在延续和深化。这还只是“机巧”伏线千里的根源。近代以来的计算思维、数学因素是机巧实现统治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数学因素并非来自犹太人或者犹太教,而是西方形而上学历史发展的结果。机巧真正的统治是在现代的技术时代。现代技术(Die moderne Technik),“这种技术乃是把自然应用到计算性表象的对象性中,其中的计算就是一种量的测量。”[23]在技术时代,计算性思维得以大行其道。这里就有了海德格尔针对犹太计算思维的批判。也引来人们对他反犹主义的质疑。

2
海德格尔对犹太计算思维批判的边界
海德格尔在《全集》第96卷《黑皮本》(“思索”XII-XV)中的几段话引起极大争议,被当成他是“反犹主义”者的证据。《黑皮本》编者彼得·特拉夫尼(Peter Trawny)也引用这几段话来证明海德格尔有一种“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其中最有争议性的是下面这两段话:
GA96:46犹太人暂时的力量攀升的原因就在于,西方的形而上学,尤其是在其近代的发展,为一种往往空疏的理性和计算能力的扩展提供了初始条件。理性和计算能力借此为自己获得了在“精神”中的一席之地,而没有能够从自身出发去把握隐匿的决断领域。未来的决断和问题越是源初和开端性的,这个“种族”就越难通达它。(…我对胡塞尔的“攻击”不是针对他个人的也不是非本质性的—这种攻击针对存在问题的耽误,也就是说针对形而上学自身的本质,在形而上学基础上,存在者的机巧才能规定历史。这种攻击奠基了那种最高决断的历史时刻:到底是存在者优先还是存在的真理的奠基。)[24]
GA96:56 由于其突出的计算天赋,犹太人很久已经按照种族原则“生活”了,……种族培育的设立,不是起源于“生活”本身,而是来自生活被机巧的高度控制。……[25]
这两段话里面出现了“犹太人”,“种族”这些高度疑似种族主义的词语。但如果仔细考察这两段话,就会发现,海德格尔所说的“种族”并非生物学的种族,犹太人在机巧的控制形成中,也非“始作俑者”。在第一段话中,海德格尔很明确地提出,西方形而上学的本质是机巧成为规定历史的力量的基础,若非西方形而上学的存在理解发生了存在遗忘,从存在自身转移到存在者的优先,机巧之控制也不会出现。西方形而上学在近代的发展为犹太人的那种计算能力或者计算的理性的扩张准备了条件。这种条件是西方形而上学向近代数学性思维的转变。也就是说,这两种不同来源但是相似的计算理性在现代合流,而犹太人的计算理性为机巧的统治推波助澜。有了这个前提,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两段话,就会发现那些反犹指控是值得怀疑的,可以说,这些话并不像通常人们认为的那样是海德格尔表达反犹——对犹太人的血缘种族的敌视和攻击——的直接证据。
反犹主义到底是什么?通常有两个词语表达反犹主义,antisemitisch和Anti-judaism。第一次使用德语的antisemitisch的是奥地利犹太学者莫里茨·施泰因施奈德(Moritz Steinschneider),他在1860年用这个词来反对法国哲学家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观点,后者认为闪族(Semitic races)比雅利安种族(Aryan races)低劣。[26]因此,Antisemitisch所表达的是一种针对生物族群意义上的反闪族、反犹主义。事实上反犹主义也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针对犹太人种族的敌意、偏见和歧视。而另外一个词 Anti-judaism 指的是一种宗教上的反犹主义,“那些接受了不同的信仰系统和实践的人全部或部分地反对作为一个宗教的犹太主义(Judaism)——部分或全部反对犹太人作为其附加,认为某些真正犹太的信仰和实践是低劣的。”[27] 这种反犹主义出于宗教的原因敌视犹太人,因此 Anti-judaism 这种字面上的反犹主义是有宗教根源的。由此来看,表达反犹主义的两个词分别有比较具体的指涉,一个是针对种族的,另一个是源于宗教信仰的。
冯·赫尔曼(Von Herrmann)认为海德格尔既非种族的反犹也非宗教信仰上的反犹,因此海德格尔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反犹主义。[28]但是,《黑皮本》编者彼得·特拉夫尼——正是他重新将海德格尔送上反犹质疑的风口浪尖,并给海德格尔贴上了“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标签——则认为,海德格尔“并不质疑‘种族’概念的生物学意义。”[29]因为海德格尔强调了血缘、土地这些概念。他尤其引用《黑皮本》(II)(GA94)中的这一段话作为证明:“站立在大地上的,可能是那种人,他来自大地(aus Boden herkommend),在其中被滋养,站在大地上,这是那源始的东西,那是经常通过身体和情调震荡我的东西——就像我扶犁走过耕地,在孤独的田间路上穿过成熟的庄稼,走过风,雾气,太阳和雪,这是母亲的血液(die der Mutter Blut)以及她的祖先循环和脉搏保持振动的东西。”[30](GA94:38,第107条)海德格尔对“鲜血”和“大地”的赞美使得特拉夫尼认为,在海德格尔那里,“民族”的属性是“种族”,“种族”和“血统”才是根源。[31]所以,他提出,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跟种族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进而提出,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不仅是种族主义的,而且是在形而上学上的,即存在历史上的反犹主义(being-historical anti-Semitism)。[32]那么特拉夫尼所谓的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是什么?特拉夫尼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要素包括:1.血缘上的种族,即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是必要条件。[33]2.在机巧统治的时代,犹太人这个种族是排名第一的力量,是“最新时代的全球性的主犯。”[34]
毋庸置疑,海德格尔个人在自然情感上对犹太人有当时普遍的偏见,甚至可以说他在这个时期有当时德国反犹主义的普遍情感倾向,这种意义上的“反犹主义”被马尔帕斯(Malpas)称为基于一种二战前在德国和欧洲蔓延在战后也没有消失的“文化上的反犹主义(cultural anti-Semitism)”。[35]这在他的书信等材料中都可以看到端倪。但这并不能证明他有一种系统的“反犹主义”的哲学思想。海德格尔对基督教在哲学上有深刻的批判,这并不是基于一种宗教情感而做出的。同样,海德格尔的自然和文化情感并不必然导致哲学上的反犹。可以说,海德格尔不是从宗教信仰角度来评论犹太教和犹太人,所以不是一种宗教的反犹主义。那么海德格尔对民族的强调是否是一种种族主义,从而导致他的种族主义的反犹?海德格尔明确反对以生物学为基础来规定民族。在1933年的讲课中他称,“即使肉体生命以某种方式是人的存在及其种族世代传承的基础,也不能证明,这个基础是决定性的基础。”[36]特拉夫尼也看到并引用了这句话,他却强调海德格尔说肉体生命才是种族的基础。认为海德格尔将血统这个“必要条件”升级为民族的“绝对条件”。[37]但是这显然是特拉夫尼有倾向地解释的结果。海德格尔事实上很早就反对达尔文生命学说在人的精神、社会、历史中的使用。[38]那种以生物学的血缘、演化为基础的哲学是海德格尔所不齿为伍的。海德格尔反对以生物学作为他哲学上的种族、民族的标准,这也是海德格尔对纳粹的反犹主义并不赞成的原因。当海德格尔说,“血统和土地(Blut und Boden)固然是强大而必要的,对一个民族的此在(Dasein des Volks)而言,却是不充分的”[39]的时候,在上下文中,海德格尔所针对的恰恰是那些当时对血统、血缘和土地的夸夸其谈,那些真正的种族主义者,将血统看作一个民族的充分条件。而海德格尔反对他们的看法,说血统和土地是不充分的,决定性的是知识和精神:“只有知识才将鲜血的奔流带到一个方向,进入一个轨道,将土地带入它能够收获的东西的孕育。”[40]这是对那种在存在历史上能够进行决断的可能出现的民族而言的。知识和追问才造成一个民族,甚至海德格尔所说的“种族”,而非血统和地域。

3
海德格尔的哲学受到反犹主义的玷染了吗?
那么,海德格尔对犹太人的这种说法是不是特拉夫尼所说的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一种哲学的反犹,易言之,是否可以将海德格尔哲学看作反犹主义的哲学?特拉夫尼坚称,海德格尔的哲学是受到种族主义的混杂玷染的。那么,海德格尔对机巧的时代的批判包含反犹内涵吗?
特拉夫尼将犹太人等同于机巧的力量,进而将海德格尔对机巧的力量的批判等同于反犹。而事实上,这样的等价关系是不存在的。进一步说,特拉夫尼所谓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在上面的第二段引文中,海德格尔说犹太人早就按种族原则生活了。但是这里的种族决不是指血缘上的种族,反而是一种“新的种族”——按照计算和算计来生活的族类。虽然犹太人早就有这个天赋,从而按照计算的天赋生活,成为这个族类,但将来的机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很多人都会进入这个族类。布尔什维克苏联、美国、英国,都是这样的族类。所以在第三段引文中,海德格尔又说,“关于世界犹太人角色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种族问题,而是一个关于人类性质(Menschen-tümlichkeit)之种类的形而上学问题。此人类性质能够把毫无约束地将一切存在者从存在中连根拔起,当作世界历史使命来担当。”[41]归根结底,海德格尔对犹太人的说辞,所批判的最终并不是生物血缘的种族,而是形而上学上的人的本质问题。他所关注的是人的本质在存在历史上的演变。海德格尔自1920年代就对人的本质及其演变的历史反复强调,并指出,所谓真理问题,实际上就是人的本质问题。“关于真理的问题不是漂浮在空中的,而是历史性的。这里所关涉的不是在不同的人类时代理解的区别,而是关于人最内在的存在的区别。”[42]人跟存在的真理的来源相关联才有历史,才有历史的进展或倒退。历史是人的本质开展的历史。海德格尔反复诠释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所展示的就是这一历史,这是人的本质开展的历史,也是人把握真理的历史。洞穴比喻中发生的转变,就是人的本质的转变。这个过程并非容易。将人的本质从黑夜之昼,达到真正的白昼。这个过程就是做哲学。追问真理就是做哲学,目的是使得人的本质发生转变。[43]对存在的真理的把握是判定人的本质的标准。这种存在历史的本质是海德格尔所谓“种族”和“民族”区分的标准。
在这里针对计算和空洞的理性在现代的突飞猛进海德格尔提出了两个来源,1. 西方形而上学尤其是其在近代的发展,使得这种计算能力成为“精神”的决定性力量。2.犹太人的计算天赋在这种基础条件下得到发挥。易言之,犹太人的计算天赋并不是西方形而上学带来的,而是一直就有的,只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发展恰好在近代以来给这种天赋提供了发挥的舞台。而现代西方的数学性思维也并不是犹太人的计算天赋造成的,而是形而上学自身发展的内在结局。但是现代的科技时代的本质——机巧(Machenschaft),按照海德格尔的想法,却是有犹太人的推波助澜才得以形成。海德格尔在上面的引文中对犹太人的指涉所针对的是机巧的统治。计算是这种存在离弃状态下的衡量标准,真理的尺度。而犹太人以其计算的天赋在机巧的时代如鱼得水,从而推进了机巧,甚至是排名第一的推动力。但是并不像特拉夫尼所指控的,海德格尔并未由此指控犹太人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犯”。在他提到“最新时代的全球性的主犯”[44]的时候,所指的并不是犹太人,而是这样一种力量:die Macht als Wesen des Seins(作为存在的本质的力量)。[45]海德格尔说,存在历史思考所试图思考的就是这个力量的本质。[46]这种力量在存在离弃过程中有不同的表现,各个阶段的发展顺序是:
存在作为现实性
现实性作为主体性
主体性作为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
权力意志作为存在(Sein)
存在作为力量(Macht)
力量作为机巧(Machenschaft)
机巧作为存在者在自身的脱离
存在者的脱离以及荒芜[47]
海德格尔明确指出,这种全球性的力量,在当代统治性的力量,是机巧。它造成了存在离弃和存在者的荒芜。
诚然,在海德格尔看来,犹太人的计算天赋加剧了机巧的统治,但他们并不是主犯。在美国主义中,虚无主义到达了顶峰。英美世界的道德掩饰起来的商业性计算性(Rechenhaftigkeit)[48]也许在海德格尔看来掺杂了犹太式的善于算计,但也并非海德格尔间接地反犹,或者如特拉夫尼所说,“是存在史上反犹主义的表达。”[49] 通过对第一段话的理解,唐娜泰拉·迪·切萨雷(Donatella Di Cesare)将之描述为:“海德格尔相信,必须断言在犹太民族和形而上学之间有一种共谋帮凶关系。”[50]“帮凶”这种说法比起说犹太民族是机巧思维的“始作俑者”更为准确,但是需要进一步进行限定。机巧是科技时代的本质,所以,犹太人的推波助澜作用是在这个存在离弃最为极端的时代发挥出来的,而并不是伴随整个形而上学史。固然机巧在整个存在历史中都以隐藏的方式存在,“它贯通并且支配着从柏拉图到尼采的传统西方哲学的存在历史。”[51]但是更准确地讲,机巧是在现代才真正成为统治存在的力量,“机巧意味着什么?是那被释放进本己桎梏中的东西。何种桎梏呢?普遍的可计算的可说明性图式,通过后者,每个事物都同等地同样地跟每个事物靠近,而跟自身陌生,事实上变得跟陌生也完全不同。那种无关联的关联。”[52]海德格尔真正意指的机巧是这种跟计算大行其道、和技术制造密切关联的机巧,即“以知识的方式奠基在数学中的技术的机巧”[53]。由于这种机巧获得力量,“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人对‘存在者’的确定无疑;不再能对真理的本质追问;一切都使得自己根据某种计算的状况被定位。”[54]在第一段引文中,海德格尔指责犹太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海德格尔是否对纳粹怀有深厚的感情,寄托了曾经的梦想,所以才对纳粹问题三缄其口,也从未退出国家社会主义党?在我看来,海德格尔一开始就没有对纳粹以及纳粹党有完全的信仰,更谈不上忠诚。他一开始就想利用这个运动,实施自己的哲学政治理念,将它引上他自己的思路。特拉夫尼也这样认为,“他从没有,或者极少赞同现实中存在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55]当国社党将他当成自己人,当他自己很快认识到不可能通过这个途径实现他的政治理念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把国社党作为同路人了。至于后来海德格尔也没有宣布退出,也出于同样的原因。那样做已经没有哲学上的意义,仅仅具有社会效应。
按照特拉夫尼的“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判词,海德格尔对机巧时代的批判包含深刻的反犹主义。因为机巧的历史形成和现代大行其道,都跟犹太教、犹太人有绝大关系。那么,海德格尔的哲学是否有可取之处,还是像一些人所言,仅仅只能将海德格尔的著作当做一种政治言论看待,或者一种用形而上学架构勾画的反犹主义内涵,从而一举抛弃?
通过我们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学说和机巧批判并没有宗教和生物学意义上的反犹主义,他的哲学也不是以反犹为目的,涉及犹太民族的言论也不构成其思想的支柱,甚至不是必要成分。从海德格尔思想的主旨出发来说,他对技术时代的批判,对座架(Gestell)的促逼的警告,都不是以反犹为目的。离开关于犹太人的论述,按照存在历史的发展趋势,仍然会形成这样的技术时代和座架对人的促逼。
▲向上滑动查看参考文献▲
[1] Heidegger, Martin.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Frankfurt am Main: V. Klostermann, 1989. S.127.
[2] Martin Heidegger, op. cit., S.126.
[3] Martin Heidegger, op. cit., S.131.
[4] Martin Heidegger, op. cit., S.126.
[5] Martin Heidegger, op. cit., S.130.
[6] Martin Heidegger, op. cit., S.127.
[7] 海德格尔:《乡间路上的谈话》,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6页。
[8] Martin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S.119.
[9] Martin Heidegger, op. cit., S.120.
[10] ibid.
[11] 海德格尔:《现代科学、形而上学和数学(1935-36)》,孙周兴译,载《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75页。
[12]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Wahrheit.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2001. S.34.
[13] Martin Heidegger, op. cit., S.36.
[14] ibid.
1 Horky, Philip Sidney. Plato and Pythagorea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5.
[16] Philip Sidney Horky, op. cit., p.32.
[17] Philip Sidney Horky, op. cit., p.15.
[18]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Wahrheit, S.32.
[19] Martin Heidegger, op. cit., S.33.
[20] Martin Heidegger, op. cit., S.36.
[21] Heidegger, Martin. What is a Thing, trans.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South Bend: Gateway Editions. 1967. p.67.
[22]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Wahrheit, S.29.
[23] 海德格尔:《乡间路上的谈话》,第13页。
[24] Heidegger, Martin, Überlegungen XII–XV (Schwarze Hefte 1939/41(GA96)). Frankfurt am Main: V. Klostermann, 2014. S.46 .译文根据:彼得·特拉夫尼:《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靳希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5-26页。有改动。
[25] Martin Heidegger, op. cit., S.56. 译文根据彼得·特拉夫尼:《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第25-26页。有改动。
[26] 参En.wikipedia.org/wiki/Antisemitism
[27] Langnuir (1971,383),参En.wikipedia.org/wiki/Anti-Judaism
[28] von Herrmann, Friedrich-Wilhelm. “The Role of Martin Heidegger’s Notebooks within the Context of His Oeuvre”, In Reading Heidegger’s Black Notebooks 1931-1941, ed. Jeff Malpas, Ingo Fari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6. p.89-94.
[29] 彼得.特拉夫尼:《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第53页。
[30] Martin Heidegger, Überlegungen II–VI (Schwarze Hefte 1931/38), S.38.
[31] 彼得.特拉夫尼,《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第55页。
[32] Trawny, Peter. Heidegger and the Myth of a Jewish World Conspiracy, trans. Andrew J. Mitchell,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p.41. 彼得.特拉夫尼,《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第50,56页。
[33] 彼得.特拉夫尼,《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第54页。
[34] 彼得.特拉夫尼,《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第45-46页。
[35] Malpas, Jeff. “On the Philosophical Reading of Heidegger: Situating the Black Notebooks”. In Reading Heidegger’s Black Notebooks 1931-1941, ed. Jeff Malpas, Ingo Fari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6. p. 6.
[36]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Wahrheit, S.210.
[37] 彼得.特拉夫尼,《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第54页。
[38]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Wahrheit, S.210.
[39] Martin Heidegger, op. cit., S.263.
[40]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Wahrheit, S.263.
[41] 译文根据彼得.特拉夫尼,《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第26页,有改动。
[42]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Wahrheit, S.201.
[43] Martin Heidegger, op. cit., S.206.
[44] Martin Heidegger, Die Geschichte des Seyns, S.78.
[45] ibid.
[46] Martin Heidegger, op. cit., S.72.
[47] Martin Heidegger, op. cit., S.72-73.
[48] Martin Heidegger, Überlegungen XII–XV (Schwarze Hefte 1939/41), S.50.
[49] 彼得.特拉夫尼,《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第50页。
[50] 唐娜泰拉·迪·切萨雷(Donatella Di Cesare),《我“对胡塞尔的攻击”——海德格尔、胡塞尔与犹太人问题》,曹忠来译,载《伦理学术》, 2018年, 第2期,第167-176页,第174页。
[51] Martin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S. 127。并且由于犹太-基督教的创世观,存在者成了受造物。S.126。
[52] Martin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S.132.
[53] Martin Heidegger, op. cit., S.120.
[54] ibid.
[55] 彼得.特拉夫尼,《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第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