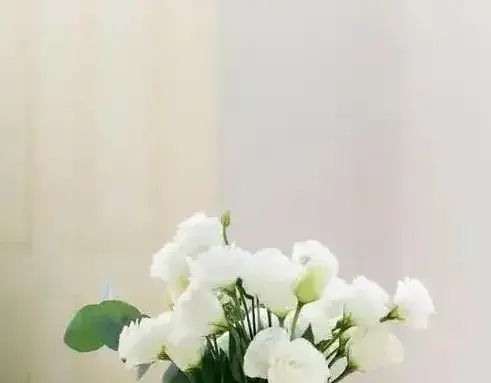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吴丽蓉
“要爱具体的人,这是我对自己的提醒。”近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乔叶推出全新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受到读者欢迎。这是一本“治愈系”的书,记录了很多生活细微处的闪光点,视角独到、情感细腻,读来让人感觉心情愉悦、万物可爱。《工人日报》记者专访乔叶,她讲述了自己如何去爱具体的人,如何在小说和散文之间自由漫步,以及如何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养分。

乔叶近照 受访者供图
努力去理解别人的时候,也拓宽了自我
记者:最近几年,“附近”这个概念变得流行,大概是说要去发现身边的美好,感觉与您所说的“要爱具体的人”是类似的意思。问题是,人是那么复杂,如何去真正地爱具体的人?
乔叶:要爱具体的人,这是我对自己的提醒,也表达了这本书的一个整体情绪。这里面“爱”当然是很重心的词,但“具体”也是很重心的词。爱具体的人,并不是说要跟每一个人去交往,这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行动——当我走向这些具体的人的时候,我有一种自我要求,要更多地去理解他们,要怀着善意去理解他们,哪怕是陌生的人。
我坐地铁的时候,身边坐着另外一个人,我对他好陌生,他是什么性格、什么职业我都不知道,但是我也怀着一种善意,还有温暖的情绪,去理解他,甚至去想象他。那对于身边熟悉的人,我觉得则是要更深层次地去理解他们。当你努力去理解别人的时候,某种意义上也拓宽了自我。
要爱具体的人,还有一个反向的指向,就是说不要老活在抽象中。大家太容易抽象了,抽象也很容易让人爱。因为抽象的人特别璀璨,比如舞台上的明星,或者是历史中的人物。相比之下,具体的人就显得灰暗。但这就是我们特别具体的生活本身,怎么接纳它、面对它,是我的自我成长很重要的一部分。
记者:您在一篇创作谈中提到,提醒自己去爱具体的人,其实就是提醒自己去爱自己。爱自己,也是当下许多年轻人试图去做的事,例如很多人在“把自己重新养一遍”。怎么做才可以被称作是爱自己?
乔叶:爱自己,包括很多方面。纵容自己是爱自己吗?肯定不是吧。想让自己吃好喝好,物质上希望自己很宽裕,这肯定是爱自己。但是,比如说胖了是不是需要健身,健身很痛苦,那是不是爱自己呢?再说精神意义上的,比如多读书,甚至读自己不爱读的书,进行自律性的要求,可能感觉上不太舒服,那是不是也是爱自己呢?
我觉得爱自己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放在人群中去互相辉映。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群体中的个体,个体的意义需要放在群体中才能更好地确认。你怎么看待他人?你对周边的人是什么态度?你对他们怀着什么样的感情?爱自己,其实也爱自己周边的这个世界,甚至通过爱周边的世界来更好地爱自己。这是一个互相构建的过程。
散文和小说之间有很多门窗,在其中可以自然漫步
记者:您日常的写作是否可以说是在小说和散文之间“横跳”?小说和散文这两种不同的文体,您如何适应切换?
乔叶:我不觉得我是在小说和散文之间“横跳”,“横跳”这样的动作是很激烈的,我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漫步。小说和散文这两种文体,我不觉得有多么不同。虽然一个是虚构,一个是非虚构,但实际上它们还是有很多本质的相同的东西,比如都要求情感的真挚、对生活的积累、对人性的认识,等等。
写散文和写小说,对我来说,甚至不用切换它就可以同时进行。我可以上午写散文,下午写小说,或者说上一个小时正在写小说,休息的时候突然觉得有个散文的素材不错,那么也可以写散文。对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一个选择。
我甚至还做过实验,比如说同一块素材,我写成小说是什么样,写成散文是什么样。我觉得它们只是形式不同,但不是天差地隔,或者说壁垒森严。我倒觉得,它们之间有很多的门和窗是可以互相透气的。
记者:我感觉有些作家随着年龄增长,似乎就不愿意再写轻巧的小文章,也许会觉得不符合自己的年龄或身份?对于写作的题材,您是如何选择的?
乔叶:这个我跟你的感觉不一样,因为我发现好多大作家其实都写小文章,比如汪曾祺,小文章里面也可以有大乾坤嘛。小文章也不小的,我觉得文章有时候有点像玉器,不是说体积越大就好,也要看它的精致度、玉化的程度。所以文章有时候看着小,其实里面也可以意味无穷,跟字数关系倒是不大。
我自己主要是看情况,为了写《宝水》,我做了好多年的生活积累。我感觉像是获得了一块巨大的布料,这个布料的主体,比如说适合做一个套装,我就把它做套装了。然后呢,还有一些边边角角的,我可能就会觉得还适合写个短篇小说。我是根据生活给予我的具体材料,来决定写什么样的东西。但不论写多长的,或者多短的,都是自己的文章,我都会尽力地、认真地写。
先把日子过好,才能用生活养育写作
记者:从您的散文中能看得出,想必您是个热爱生活的人。生活和写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乔叶:生活肯定是要大于写作的,生活是写作的基础嘛。我很爱写作,也很爱生活。有人说为了写作可以不顾一切,我说千万不要这样,先好好地生活,先把日子过好,才有可能用你过好了的生活来养育你的写作。这不仅是说用赚的工资养育,更多的还是精神意义上的养育。生活本身一定比写作更宽广,更丰富。
可能有人会觉得写作是一个很孤独的、和生活剥离的行为,但其实写作和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就像一个孩子从母体中养育出来,虽然他在独立奔跑,但还是生活这个母亲养育了他。
不管你是爱写作,还是爱干别的事情,前提是你都要爱生活。爱生活,意味着你可以去爱很多东西。
记者:写作这么多年,您如何一直保持创作的灵感且持续进步?
乔叶:那还是要感谢生活对我的养育。我热爱生活,生活也热爱我,我觉得它给予了我很多东西。灵感就像河水或者山中的泉水一样,跟周围的植被、生态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精神的水土保持得好,灵感可能就会源源不断地来。注重观察生活,在生活中汲取营养,灵感也会像山泉叮咚。另外一个方面呢,创作其实不能太依赖于灵感,灵感可以写一个小的东西,如果是长期的写作,仅靠灵感是远远不够的。至于进步吧,我也不敢说,反正就还是要继续努力地写得好一点,更丰富一点。
记者:近来,以DeepSeek为代表的AI工具,让很多文字和创意工作者产生危机感,对此您怎么看?
乔叶:我可能秉持着一些比较固执的东西,所以相应地对外界的风潮比较迟钝。比如对AI写作,坦率讲目前为止我没有什么感觉。AI的确是科技进步的产物,也的确能替代一些写作,比如一些实用性、应用型的写作。但文学是创作,有人的生命的创造性,这应该是它不具备的。
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感觉到AI对文学创作或对我个人的写作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人会有立场、情感等等各种困境,比如人会软弱、会无助、会陷入道德疑难,你很难想象一个智能设备能够陷入类似的困境,而这些都是文学领域独有的,是再高级的智能也无法替代的。来个特别简单的类比:饺子有速冻饺子和手工饺子的区别,我们理所应当地会觉得手工饺子更美味、更具有价值感,也更让我们珍爱。这就是人的宝贵、人的不可复制性所具有的魅力。在文学艺术上尤其如此,所以我更坚持和信任人类带有温度和情感的产出。
来源:中工网-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