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恰巧经过布拉格的卡夫卡博物馆。卡夫卡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在记忆中,可能因为疲惫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我只是匆匆瞥了几眼博物馆内饰,就离开了。
后来,我跟我的好朋友小蓝聊起布拉格,他在2015年前后参观了卡夫卡博物馆。小蓝是一个异常敏锐的人,他告诉我,参观时他感到一种明显的压抑感,如同阅读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判》。狭小的单人书桌,逼仄的办公环境,无尽的纸张工作。我想,他定是感受到了博物馆所营造出来的卡夫卡的真实感受和情感流动,而我可能急匆匆地选择了回避。

笔者的朋友小蓝在卡夫卡博物馆拍摄的照片。
卡夫卡对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官僚统治”的揭示,是其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官僚制(法语bureaucratie)一词由法语“写字台”(bureau)和古希腊语“权力”(κράτος)构成,这是由写字台构成的统治,写字台象征着当代行政官僚统治。卡夫卡《城堡》异常敏锐地描写了这种写字台两边记录与被记录、看与被看、认识与控制的关系。
复旦大学教授洪涛的新著《文学三篇》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分析卡夫卡、奥威尔和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年)等作家的文学作品,反思现代国家机器不断强大的同时,技术主义如何一步步吞噬人性。作者指出,一方面,在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个体总是难以摆脱孤独;另一方面, “以隐秘方式介入私人生活领域,是现代权力的一个基本特征”。那么,孤独的个体和官僚制有什么关系呢?

撰文|戴碧云

《文学三篇》,洪涛 著,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6月。
机械世界的孤独个体
与官僚技术统治
个体无法摆脱的孤独是文学作品的母题,米兰·昆德拉和奥尔罕·帕慕克的作品都有涉及。同卡夫卡一样,昆德拉也在布拉格居住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以1968年的捷克为背景,并以尼采的永恒轮回理论为开篇。昆德拉认为生命只有一次,永恒轮回之说从反面肯定了个体生命的短暂。如果生命能够无限重复,那将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相比之下,只有一次机会的个体生命则显得轻盈无比。
然而,昆德拉反问我们,沉重真的残酷,轻盈真的美好吗?哲学史上,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是流变的。巴门尼德反对赫拉克利特。他列出过一些二元对立,光明与黑夜,轻与重,存在与不存在。巴门尼德认为流变是假象。巴门尼德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找到了存在,一切且一。通过巴门尼德,昆德拉关联到了存在的轻与重,他想到了托马斯。托马斯对婚姻有着复杂的态度,他第一段婚姻失败了,他认为他不适合婚姻。他享受身体的愉悦,逃避情感的责任。他在寻找确定性的过程中深刻表现了一个现代人的孤独。特蕾莎希望托马斯负起责任,但她失望了。在小说的最后,她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结束了两人无法承受的痛苦。
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则更突出表现了古典世界与刚刚开始的现代世界的冲突。故事中的黑向往着爱,他一直深爱着谢库瑞,他一度相信谢库瑞是他孤独的解药。黑自述说:“发现在那被自己误认为是窥孔的地方,并没有谢库瑞的眼睛时,我经常会失望透顶,接着心里便会涌起一股奇异的孤独感,会像一个茫然不知所措的人那样焦躁不安”。

《我的名字叫红》,作者: [土耳其] 奥尔罕·帕慕克,译者: 沈志兴,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1月。
最后,他跟心爱的谢库瑞结了婚,然而故事的结尾却让读者陷入困惑。黑并没有因此摆脱孤独和犹豫,他被忧郁击垮了。谢库瑞这样自述:“无论真正原因为何,黑始终沉浸于忧愁当中。由于知道他的悲伤丝毫无关乎他的肩膀,因此我相信,必定是某个忧伤的邪灵占据了他灵魂的阴暗一角,使他情绪消沉,就算在我们共赴云雨的极乐刹那,也挥之不去。”
为什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生活在欧洲的托马斯,《我的名字叫红》中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黑,都无法摆脱孤独?为什么卡夫卡笔下的K和托马斯都必须面对一个无孔不入的技术统治世界?李猛教授曾经在《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的上篇用《鲁滨逊漂流记》中的现代个体鲁滨逊引出这个讨论。鲁滨逊展现了一个孤独而焦虑的自然状态的危险。
洪涛教授借用霍布斯的《利维坦》给出了一条孤独个体与国家机器关系的线索。利维坦是一种神话中的巨兽,利维坦象征着国家机器。《约伯记》中,因为受到严重不公的约伯哀怨向神质疑他的正义。神给约伯展示了巨兽利维坦。约伯在看到利维坦之后,明白了神创的秩序,接受了命运。
霍布斯认为有形的并非纯粹精神的神创造了世界,这是一个机械的世界,如同机械钟一样运转。《世界图景的机械化》一书解释了近代早期欧洲的这一趋势。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采用了纯粹唯物论形而上学。霍布斯通过物质及其运动,不仅解释了无生命自然的运行过程,还推导出所有的心灵现象,进而否认了非物质存在的可能性。物质的神设计并赋予世界以初始推动力。
霍布斯认为人同样可以跟神一样制造了人造秩序。人在自然状态下害怕被另一个理性人消灭,惶恐中的人订立契约,契约可以帮助人摆脱每一个人害怕另一个人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下,人类处于不平等的竞争与冲突之中,这会造成无休止的斗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以确保社会秩序的维持。

霍布斯的《利维坦》插图。
霍布斯在论证自然状态为战争状态时,包含了自然平等的观点。然而,他并不认为这种平等的个体能够作为现代社会稳定的基础。相反,这种平等导致了不稳定,即自然状态下的冲突与战争。霍布斯不赞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天生是社会的动物”,他认为社会的稳定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恐惧。霍布斯在《论公民》中探讨了恐惧作为社会起源,霍布斯批判传统的友谊,他的个体的确是孤独的。我们是孤独的旅人。
现代社会推动传统秩序解体,个体从传统秩序中被解放出来,卡夫卡笔下的官僚组织又重新吸纳个体,营造了新的秩序。洪涛教授指出霍布斯的利维坦方案发展出体面版本和不体面版本。这个利维坦可以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技术统治,不体面版本是一个全面监控的社会。体面版本则通过某种强制的方式制约权力,让大部分人拥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
几种逃离的出口
面对密不透风的技术统治,个体有没有逃避的方式?
《文学三篇》提供了不少实验性的非暴力方法,比如爱、传统、隐藏、讲故事和对抗等。爱可以联合他人,让家庭有凝聚力,也许这是一种出口,可以逃离现代的冷漠统治。只是爱太脆弱,过度的工具理性会让爱崩解,以爱之名绑架对方。
第一种方式为爱。爱可以联合他人,让家庭有凝聚力,也许这是一种出口,可以逃离现代的冷漠统治。只是爱太脆弱,过度的工具理性会让爱崩解或者以爱之名绑架、控制对方。
《玩偶之家》中的娜拉看清了自己在家里的工具作用、玩偶地位,她逃离了家庭。鲁迅在1923年有一个“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他认为娜拉出走后,只有两个出路:一个堕落,一个回家。鲁迅还给了另外一条路:饿死。鲁迅在为某种现代性呐喊,他希望给娜拉独立养活自己的另外一条出路。娜拉出走后,她离开家之后,可以独立养活自己,而不用回家或者堕入风尘或者饿死。当然,娜拉也许去工厂,也许去做行政。她要面对的不再是丈夫的压迫,而是日间说不上有意义的工作,夜里无边的孤独。洪涛教授在这里问,那么,爱是否是一种逃避,还是超越?如果娜拉不离开家庭,她一直爱,一直默默为家庭贡献,这是不是一种出口?爱需要幸运。

《“娜拉”在中国》,作者: 许慧琦,版本: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7月
第二种方式在鲁迅的小说中有过讨论,那就是传统。面对传统,鲁迅感到绝望。但已经被现代化的我们又该何去何从?其实这个线索已经隐隐约约隐藏在《文学三篇》的各处,但全书并没有专门论述。传统是很多人不惜以生命代价去捍卫的价值,包括《我的名字叫红》中的波斯人橄榄。
然而怎么理解传统,怎么面对传统,这成了很多学者努力终身的话题。清代俞正燮以严谨考证而闻名。他著有《癸巳类稿》,张之洞称赞他“笃守汉人家法,实事求是,义据通深”。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中也认同俞正燮对贞操、缠足和娼妓等现象的批评。然而俞正燮却在《癸巳类稿》卷一四《书〈人身图说〉后》讨论中国人与西洋人身体构造的不同,西洋人脏腑经络不全,比如中国人心有七窍,西洋人只有四窍。
“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谶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张之洞在《劝学篇·循序第七》中所提倡的中体西用是否可能?当然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东方学者,同时也困扰着西方学者。比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米歇尔·福柯、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施特劳斯、沃格林等。

《癸巳类稿》书影。
第三种方式是隐藏,换一种方式可以说是成为扫地僧。不少武侠小说中都有类似扫地僧的形象,不过金庸的刻画尤为传神。少林扫地僧是金庸笔下的神秘高手,武功绝顶。他平日只是在少林扫地,却击倒了武林高手萧远山和慕容博。如果想要逃离武林,大隐隐于世大概是一个选择。这个世界是一个用看和认知统治的世界,那么尽量少被看到似乎是一个出路。我估计每一个学过法语的学生都在某一个阶段学过这么一句法语名言。隐姓埋名,幸福安定(Pour vivre heureux,vivons cachés)。我在这里把隐藏理解为扫地僧的原因是在全景式监控的当代技术统治下,要隐藏也是一件非常困难,需要很多技巧的事情。当然,完全的隐身过于消极,毕竟扫地僧最后也出了招。
第四种出口则是想象,我们可以讲故事,写小说。洪涛教授认为小说作为一个想象的产物可以补充理性。小说是现代的产物,充分体现了个体性。
技术的本质与另一种出口
在上述几种较温和的抵抗方式以外,我们再讨论一下技术的本质以及笔者认为的另一种可能的出路。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的《素食者》的故事围绕英慧的决定开始。英慧做了一个关于暴力和血腥的梦,她决定吃素,放弃肉食。她的家人对她的行为感到愤怒,她父亲在家族聚会中用非常暴力的方式强迫她吃肉。她的生活被家人和社会所控制。作为消极反抗的方式,英慧从吃素到绝食,她走向植物化的过程。韩江还有另外一篇小说《植物妻子》也表达了相关主题。《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卢梭感慨他的心灵曾被几朵小花装点,如今花儿在忧愁中凋零,在烦恼中枯萎。植物纵然是卢梭乃至韩国作家韩江的反抗方式和情感寄托,但人是动物,可以更积极地去掌握知识,改变环境。
根据古典学家塞德利《古代创世论及其批评者》以及《古希腊哲人论神》两书中对古希腊思想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知道技术与创世理论密切相关。神可能是宇宙的创造者或创造性力量,神用技术创世,宇宙是个技术制造物。柏拉图的《蒂迈欧》代表了这一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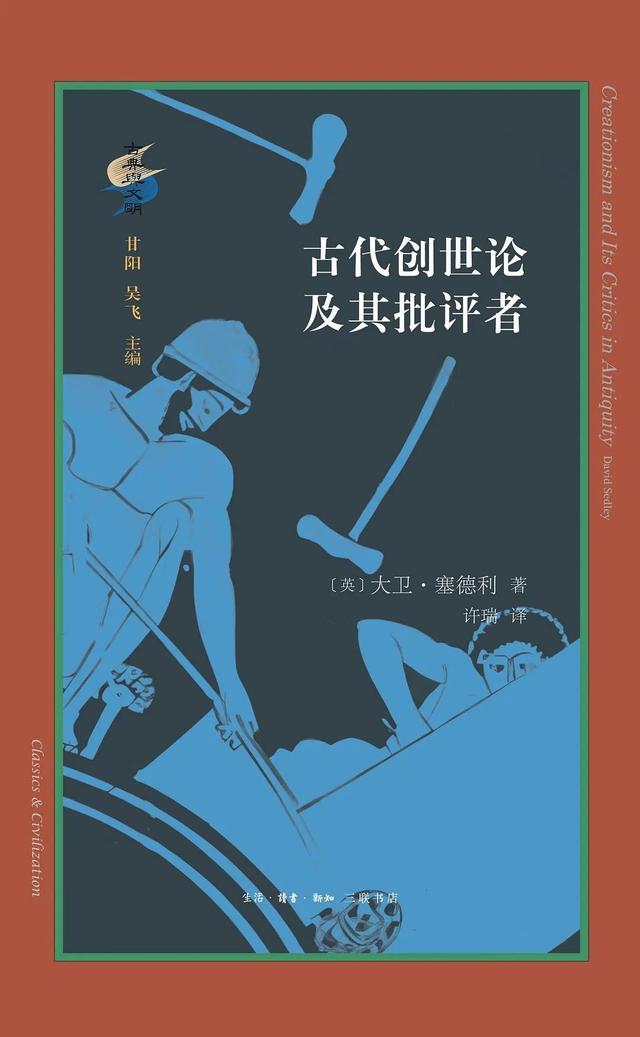
《古代创世论及其批评者》,作者: [英] 大卫·塞德利,译者: 许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年11月。
在《蒂迈欧》中,神的智慧主要通过他的技艺展现。古希腊哲学中,创世的过程意味着对已有的材料进行加工,并赋予其秩序。神通过这种技艺使宇宙井然有序。技术通常指一种专门的知识,例如医术、修辞术。然而,所有的人工制品终究会消亡吗?抛开字面解释和字面解释反对者的质疑,我们看到苏格拉底的一个经典悖论:每一种技术都有蕴含着制造对立结果的潜能。比如建筑师最擅长建造房屋,但也最擅长拆毁房屋。这同样适用于宇宙的创造者。宇宙既有生成的时刻,就有毁灭的时刻。如果只有开端,没有毁灭,那么时间就不对称。
由此可以看出,就算是神,神的技术也不持存。德里达在《柏拉图的药》中,对柏拉图的《斐德罗》进行了解析,药(pharmakon)既可作为解药,也可作为毒药。对于德里达来说,书写也是一种药。斯蒂格勒跟随德里达提出了“技术药理学”的概念,主张“技术即药”。技术的不稳定意味着技术既有可能成为治愈的手段,也可能成为伤害的来源。技术是药,是药就有毒性。
奥维德在《变形记》(Metamorphoses)卷8中记录了这么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代达罗斯是一个技术高超的建筑师,他建造了迷宫。代达罗斯痛恨克里特岛,痛恨流放生活。他搜集了羽毛,制作了翅膀。代达罗斯警告他的儿子伊卡洛斯:“你不要飞得太低,也不要飞得太高。太低了,翅膀沾水就会变重;太高了,太阳的热就会把它烧坏。你飞行的时候,要介乎高低之间。还有,你不要向北极大熊星座飞,也不要向猎户腰间的出鞘宝刀飞,你要跟着我飞。”父子在天空翱翔,地上人们以为他们看到了神。然而,伊卡洛斯忘记了父亲的忠告,越飞越高。最终摔死。代达罗斯诅咒着自己的技艺。

电影《格列佛游记》(2010)剧照。
斯威夫特虽然生活在18世纪的英国,但他非常清楚什么构成了技术统治。他在《格列佛游记》中提供了生动的例子。斯威夫特直言勒皮他岛(飞岛)的精英在数学、天文学上的伟大进展使得他们维持统治。现代哲学和天文学能帮助国王镇压叛乱。这个国家的贵族只关心理论,他们收藏着各式各样的天文仪器,但最稀罕的东西是磁石。这个地方的统治靠先进的人类技术,而这个岛依靠磁石统治。磁石能让勒皮他岛悬在半空,并且自由降落。这样勒皮他岛的统治者们在天上,而纳贡的普通人在地上。
如果下面的城市暴动或者拒绝纳贡,天上的统治者们可以用三种方法对付暴动。第一种手段比较温和,就是让勒皮他岛浮翔在暴动的城市上空,这样就剥夺了人们享受阳光和雨水的权利,当地居民就会遭受饥荒和疾病。第二种方法比第一种激进,漂浮在半空的岛上的统治者们可以把大石头往下扔,砸烂地上的一切。第三种方法最为极端,就是飞岛直接下降,压平下方。但磁石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岛的底部是由非常厚的一整块金刚石板构成的,如果震动太大,飞岛有可能碎裂。如果飞岛底部碰到火也可能爆裂。国王统治下的林达洛因人起来反抗,差点儿用铁石吸住了岛屿,靠火去攻击。因为这个方法,勒皮他王国与林达洛因人互相达成了平衡。

这幅图像是“宇宙之幕”(Flammarion Engraving),1888年法国天文学家、科普作家弗拉马里翁(Camille Flammarion)的著作《大气现象》(L'Atmosphère: Météorologie Populaire) 中使用了木雕版本。画面中描绘的是一个旅人探身穿过宇宙的幕布,看到天体运转的秘密。虽然这幅画常被误认为是中世纪的作品,因为它呈现了一个封闭的宇宙。不过这是日心说,而不是地心说。
在最近的一个访谈中,“人工智能教母”李飞飞讨论到她早年的学习经历,她说自己之前学习理论物理,后来她对生命和人的意识问题感兴趣,比如人为什么能思考。她认为认识事物最好的办法是制作。她决定自己制作意识,这样才能对理智的产生有更好的理解。
近期新闻中OpenAI公司被曝出要求投资者如英伟达等不要支持竞争对手,比如OpenAI的前首席科学家伊尔亚·苏茨克维(Ilya Sutskever)的新公司SSI(safe super intelligence,安全超级智能)。网传苏茨克维因为担心OpenAI已经接近通用人工智能(AGI)技术,这将影响人类安全,因而他离开了OpenAI。
当我们再次面对这幅天文学家试图突破当时宇宙幕布的画面时,不禁联想到想要逃离家庭的娜拉,或是因为不满而渴望逃离宇宙的灵知主义者,以及那些不断修炼与神相似技能的人。我们此时又是怎样的心情?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戴碧云;编辑:李永博 朱天元;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