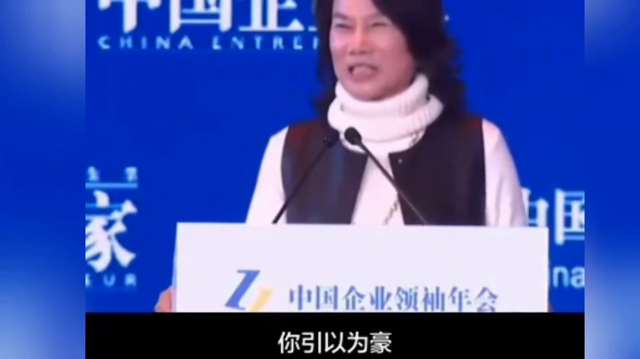作者:钱星文 编辑:冯晓晖
“浔城故事”专栏致力于分享与九江生活见闻相关的散文及纪实类文章。诚挚欢迎原创作者投稿,投稿方式及联系方式详见公众号自动回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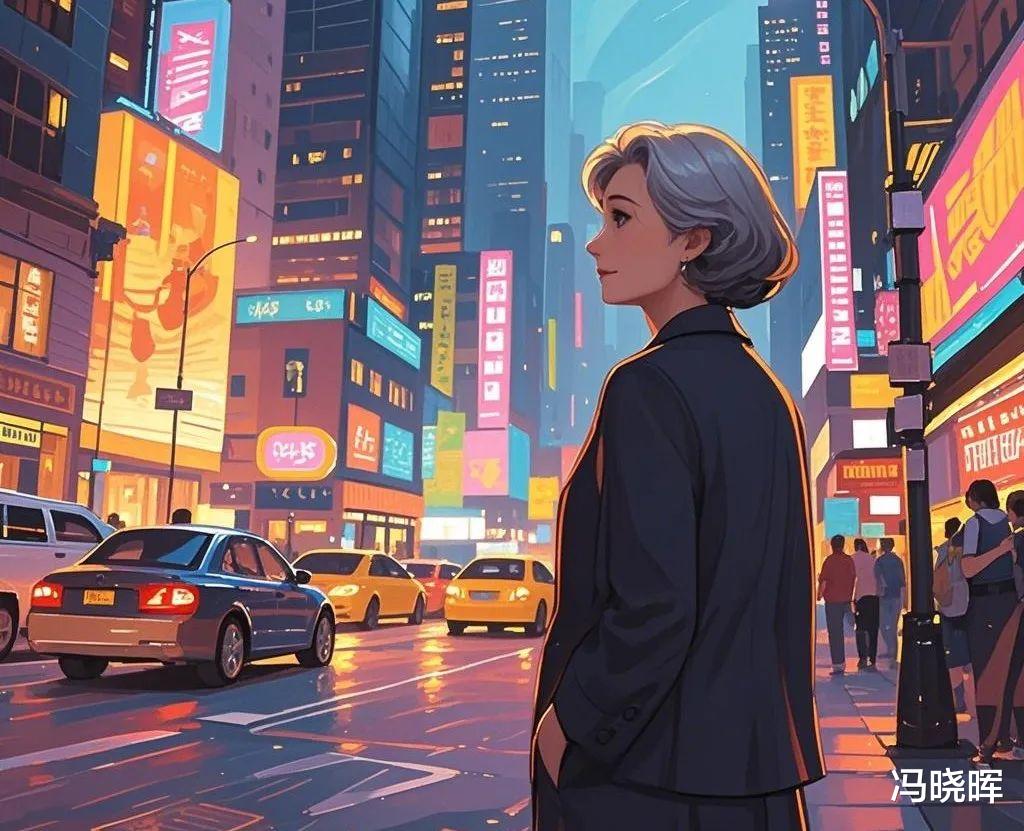
在名字这件事上,我也有过漫长的自我探索。我的名字以 X 和 Q 开头,这在西文中很少见,外国人常常念得不伦不类。当招聘的 HR 都念不出来我的名字时,这会大大降低我面试成功的几率。在邮局排队时,听到柜台叫着“轻王矿”,我一脸茫然,是在叫我吗?
为了生活和工作方便,我用了很久 Lois 这个名字,就像一张简单的工牌,对于我而言只是一个标签。每次被同事和朋友问到“你真正的名字是什么?”我心里其实都有点不舒服,仿佛背弃了自己的“真名”。我会耐心解释,写下汉字,告诉他们我的名字寓意“智慧的星星”。后来,我又想到了另一个发音接近的名字——阿文(Arwen),不仅对中国人来说更像昵称,也让我在英国的家人和亲密朋友之间有了一种更深的连接感。Arwen,是我最喜欢的《魔戒》中的一位角色的名字。后来为女儿取名时,我也思考了很久,最终选了庐谧(Lumi)这个名字,拉丁语意为“光”,也是“星之女”的意思。
这样的经历,也让我开始更多地思考,为什么中国人在名字上,会有这么复杂又微妙的感受。
关于中国人取英文名的问题,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甚至相反的声音。有些人坚持认为:无论发音多难,都应该重复教会外国人正确念出中文的“真名”,因为这是我们真实身份的骄傲。那么,“诗婷”“游蝶”们该怎么办?
中文本就有形音分离的特点,同音字极多而字义各异。表声西化的拼音名其实并不能代表中国人的“真名”。毕竟丢掉了字形之美、丢掉了字意内涵的字母拼音名,本身也是一种在国际交流中作出的妥协,并不是对本文化的否定。比如中国人在初次见面时,常常会解释自己名字中的汉字,如“立早章”或“言字旁的诗”,因为仅靠发音,往往无法准确传达名字中蕴含的意义。
从更大的文化传统来看,中国文化里,取字、号、笔名、雅称自古就很常见。这并不意味着对本名的背弃,而是一种更丰富、更有创造力的自我表达。不同情境下取不同的名字,正是我们文化中一种流动又细腻的身份意识。
今天在外企里流行的“Mary”“Eric”之类的英文名,倒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现代版的“字”。虽然“Lucy”们被不少人拿来调侃,但也隐隐延续着一种深层的文化逻辑。
起外文名这种现象反过来也存在。很多在华生活、工作的外国人,也会给自己起一个有寓意的中文名字。比如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本名 Christopher Doyle,是个澳大利亚人。还有瑞典汉学家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他们的中文名字不仅音近、好记,更融入了对文化的理解与热爱。这种取名行为,不但不会像中国人取英文名那样受到质疑,反而常被看作是尊重、喜爱中国文化的体现。而从实际角度看,这样的名字也确实拉近了交流的距离——毕竟,“Christopher”“Göran”这些发音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实在拗口。
选择一个自己喜欢、富有象征意义、又便于沟通的名字,并不会削弱身份认同,反而成为了一种自然的文化适应与融合。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在国际交流中为自己取一个英文名,本来也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在我们的日常交往中,直呼全名常常带着一种正式甚至疏离的气氛,人们更习惯在称呼中加上后缀或昵称,比如“小明”“老王”“张老师”,而不是单独叫名。这种对称呼的敏感,也让我们在跨文化交流时,更自然地接受了为自己取一个“外人使用的名字”。
可惜的是,欧美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往往容易误读这一点,总以为这是单方面的迎合。有些外国人习惯性地认为,我们用英文名是为了取悦或方便他们,却忽略了,也许我们只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或者纯粹喜欢这个名字。这种想当然,本身就是一种无意识的傲慢。如果真正尊重一个文化,应该是去理解它的文字、历史与情感,而不仅仅执着于正确发音。
名字代表了我们的身份与自我认同。重要的是,在跨文化交流中,在不同名字的标签之下,我仍然清楚自己是谁,能够自信地解释我的文化背景和中文名字的意义。
【编后记】
星文算是我的学生。这是她之前写的随笔,因为看了我发表的《浔城故事 | 做回自己》,又重写的。严格来说,本篇并不完全属于“浔城故事”的范畴,但星文是九江人,也可以算作九江故事的一部分。
转发这篇,是因为她所表达的困惑,恰恰是许多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共同的经历。我们如何在异乡介绍自己、标记自己?如何在文化的交错中,找到既自信又不失本心的位置?又如何获得来自同胞的理解?
其实,将“海外”换成任何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一问题都同样存在。本篇随笔,值得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