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海关的“旧账”:一场关于射频电路的争议
事件的导火索是一种名为“远端射频头”(Remote Radio Head,RRH)的通信设备组件。这种被封装在小型模块中的射频电路,是4G通信基站的核心部件,负责将网络信号转换为高频无线电波。2018年至2021年,三星从韩国和越南进口了价值7.84亿美元的RRH,却未缴纳任何关税。印度海关认为,这类设备应归类为“专用通信设备”,需征收10%或20%的关税;而三星坚称其只是“普通电子元件”,属于零关税范畴。
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技术定义。三星提交了四份专家鉴定报告,强调RRH不具备独立的信号收发功能,只是基站中的辅助模块。然而,印度海关翻出一封三星2020年写给政府的信件,信中明确将RRH描述为“收发器”——而收发器在印度关税分类中属于应税产品。海关专员索尼尔·巴贾杰更是指控三星“明知故犯提交虚假文件”,甚至“违背商业道德,只为最大化利润”。最终,印度政府不仅要求三星补缴5.2亿美元税款,还追加了100%的罚款,七名高管更被单独处罚8100万美元。
“养肥再杀”的印度逻辑:外资企业的“合规陷阱”
三星并非印度“税务大棒”下的唯一受害者。此前,大众汽车因“错误分类汽车零部件”被追缴14亿美元关税,起亚印度分公司也因类似问题被罚1.75亿美元。这些案例暴露出印度监管的“双重面孔”:一方面以“印度制造”政策吸引外资建厂,另一方面又以追溯性审查和模糊的法规对外企“收割利润”。
例如,三星早在2017年就因手机零部件关税争议被罚1.2亿美元,2021年又因工厂排放超标被罚3400万美元。此次罚款前,印度税务部门对三星办公室发起突击检查,没收文件并传唤高管,最终以“违反法律”为由开出天价罚单。这种“先招商后罚款”的模式,被韩国媒体讽刺为“欢迎你来挨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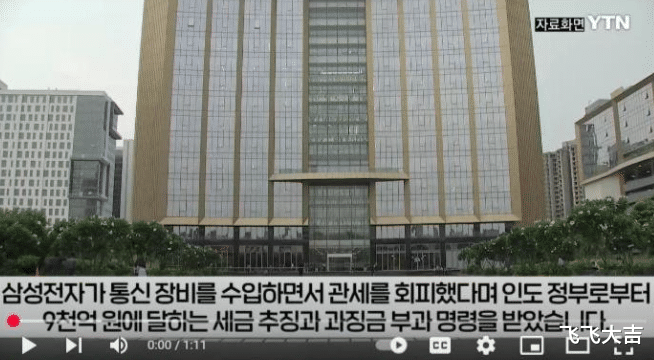
韩国人的困惑:为何怪中国?
令人费解的是,部分韩国舆论将三星在印度的困境归咎于中国。这种逻辑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全球产业链博弈。其一,中国通信设备商的“缺席”让三星有机可乘。 自2020年起,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遭遇政治打压,印度也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通信设备商参与5G建设。三星趁机抢占市场,向印度信实工业(Reliance Jio)和沃达丰等运营商供应设备。然而,印度对中国企业的排斥并未转化为对三星的优待,反而因缺乏竞争让印度政府敢于对三星“下重手”。韩国《每日经济》分析称:“三星在通信设备市场的高利润,可能让印度认为这笔罚款无关痛痒。”
其二,三星的“印度依赖症”与中国市场的对比。 三星近年将部分产能从中国转移至印度,试图构建“中国+1”供应链。然而,印度工人的罢工潮、低效的行政流程让三星吃尽苦头。2024年,印度三星工厂因劳资纠纷爆发大规模罢工,工人要求涨薪一倍、实行35小时工作制,甚至“岗位世袭”。韩方管理层强硬拒绝,最终导致生产瘫痪,工厂一度威胁“撤资回中国”。相比之下,三星在中国市场虽面临激烈竞争,但稳定的政策环境和成熟的产业链让其难以割舍。社长李在镕在北京论坛上的“谈笑风生”,与在印度的“冷面扑克脸”形成鲜明对比。
其三,中韩产业链的潜在竞争。 印度对中国手机品牌的打压(如冻结小米48亿元资产)本应利好三星,但中国厂商凭借性价比仍在印度中低端市场占据优势。2024年,vivo、小米分列印度智能手机市场份额前两名,三星仅排第三。部分韩国人认为,中国企业的“顽强生存”迫使三星过度投入高端通信设备市场,从而陷入印度政府的“合规陷阱”。
印度的算盘:财政危机下的“杀鸡取卵”
印度政府对外企的频繁罚款,背后是深层的经济困境。截至2025年,印度外债达6200亿美元,超过58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且每年外商汇出利润超400亿美元,外汇流动性岌岌可危。通过罚款和冻结资金,印度既能缓解财政压力,又能迫使外资将利润再投资本土。例如,亚马逊被罚后承诺向印度中小供应商投资10亿美元,沃尔玛则以扩大采购换取减免。

谁该为三星的困境负责?
三星的遭遇,本质上是全球化与本土保护主义碰撞的典型案例。印度政府的“合规陷阱”固然霸道,但三星也低估了新兴市场的监管风险。将责任归咎于中国,则是韩国舆论在焦虑中寻找替罪羊的体现。真正的教训在于:跨国企业需在市场扩张与风险管控间找到平衡,而依赖单一市场的战略,终将付出代价。正如网友所言:“印度挣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 三星的“印度梦”,或许正是这句话的最新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