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其他平台的搬运者们,别再搬运我的文章了,头条平台现在开启了自动维权,一旦你搬运我的文章,不是我找你维权,是头条平台自动找你维权,我想放过你都不行,别干费力不讨好的事,去搬运些流量水文,那赚钱更多。
一切取舍,皆有代价,这句话需要被正确理解,它要说明的不是简单的“舍”、“得”智慧,不是只有“得”有代价,“舍”同样有代价,但小到个人生活大到王朝历史,其实都是这样,不过是在代价和代价间做选择罢了。
本篇开始,我们将进入大武大帝篇,汉武帝刘彻,一个在民间争议极大的历史人物,喜欢他的人格外喜欢他,认为他开疆拓土、扫灭匈奴,扬大汉国威;讨厌他的人又格外讨厌他,认为他横征暴敛、好大喜功,极尽压榨之能事,让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中,把国家搞到了崩溃的边缘。
历史是复杂的,人性同样如此,汉武帝的所有侧面都真实存在,他一人千面,在50多年的超长执政生涯里给他治下的大汉帝国刻下了太多烙印,与其讨论汉武帝诸多侧面中的哪个是正面的哪个是负面的,倒不如尝试去找出汉武帝所有侧面背后的总逻辑。

要找出汉武帝施政的总逻辑,离不开一个早就登上历史舞台,在武帝时期已经成一定规模并且有明显失控表现的群体:豪强。
豪强这一特殊群体的产生原因,一方面是马太效应下资源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客观规律;而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汉帝国赖以治国,以至于连皇帝的谥号都要加上它的一个理念:孝。
你以为汉代推崇的孝只是为了让百姓懂得关爱老人?事实远没那么简单,严格意义上讲,以“孝”治国是汉帝国看到秦二世而亡教训后的无奈妥协。
“孝”字究竟意味着什么?
大汉的“孝”不知朋友们初看汉光武帝刘秀的谥号时,是否会感觉奇怪,怎么别人都是一个字,就他两个字。
事实上这并非刘秀要搞特殊,所有汉代的皇帝谥号都是两个字,只不过其他皇帝的两个字中都有一个字是一样的,所以后世也就把它省略了。

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其实完整的谥号应该是孝文皇帝、孝景皇帝、孝武皇帝。
汉代重视“孝”并非只是尊崇儒家思想的原因,因为独尊儒术是汉武帝时期才提出的,而强调孝道,在文帝,甚至惠帝和刘邦时期就开始,要知道,那时候的总体治国思想可是黄老之术。
汉文帝刘恒就提出以“孝”立国,在乡里中设“三老”、“孝悌”和“力田”,作为民间自治的重要力量,三者中,力田是为鼓励耕种而设置,而“三老”和“孝悌”都与“孝道”有关。
汉帝国对于“孝”的执着追求可不是因为汉代的皇帝道德水平突出,甚至不能完全说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对于“孝”的强调,其核心是汉帝国在权力边界问题上做出的妥协。
我们时常说汉承秦制,但是至少在汉初,汉帝国尚未将秦制贯彻到底。
相比于秦帝国,汉帝国在“国”和“家”两个层面上分别做出了妥协,国的层面大家都清楚,汉初对于那些远离帝国核心的地区分封给诸侯王,由秦的直接统治改为间接统治。
而在家的层面,汉帝国则选择适当放弃秦帝国所追求的“权力的最后一公里”。
汉帝国的统治者们这么做有其无奈的原因,因为秦帝国试图构建的那个理想国,它必须得斩断一个根本不可能完全斩断的东西:血亲。
大秦小家让秦国走向强大的商鞅变法,有一部分是专门针对“家”的。
比如:令父子同室而居者为禁。
再比如: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背其赋。
商鞅对此类变法给出的解释是移风易俗,但事实上,商鞅在“家”的范畴上进行的改革,其核心目标都是一致的:把大家族,拆散成小家庭。
秦制的核心,是把帝国内部一切稍微大一些的组织全部打散,让全体秦民以自耕农小家庭的形式存在,然后国家直接从这些自耕农手中征税,摊派徭役和兵役。
由于没有中间阶层的截留,秦帝国可以把税定的很高,没有中间商,差价我就可以使劲赚了。

收更多的税,让更多人给自己服徭役和兵役,并不是秦帝国去打散大家族的唯一原因,小家庭形式下存在的秦人,和大家族形式下存在的秦人相比,对抗秦国权力机器的可能性便成几何倍缩小。
这些再配合上让邻里间互相监督和举报的连坐制度,能够最大程度地达到控制秦人的目的。
商鞅变法之初,在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下,秦帝国用了很大的功夫终于初步达成了将大家族打散为小家庭的目的,帝国的行政效率得以快速提高。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社会效率提高当然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是它并非毫无代价,这个代价便是统治成本。
对所有小型家庭的直接统治,远比对于少数大家族间接统治成本高得多,也难得多,所以秦帝国必须以高效的社会运行方式,去覆盖直接统治造成的高成本,大量税赋,大量的徭役、兵役等为国家机器服务的人员是必不可少的。
秦帝国统治者通过数代人的努力,能够实现国家内部的内循环,让这架效率和成本都很高的庞大国家机器持续运行。
但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成立:要维持大秦这架高成本的国家机器运行,效率与成本必须是匹配的,一旦这架国家机器的成本与效率平衡被打破,等待它的就是瞬间的土崩瓦解。
六国遗民秦统一后,要将自己的制度推广到整个天下,在秦始皇看来,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秦能灭六国已经充分说明了秦制的效率是高于六国制度的,以高效的秦国新制度去取代低效的六国旧制度,从长期上看这对于全天下来说都是有益的。

但这一切得有一个前提:秦帝国它得能挺到前期。
以血缘关系凝结在一起的组织,它们的存在有着“基因”背书,是人们自然而然地选择,相反,打破血亲联系才是反人性的,是需要统治者下大力气去完成的,所以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让原本在六国内以大家族形式生活的家庭们改为以小家庭形式生活,这本身就是一件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去做的系统工程,它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秦灭了六国后,在秦始皇眼中,那些六国中的大家族都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腐朽势力,得坚决打击,于是把十二万户豪族强行搬迁到关中咸阳附近居住,这里搬的应该是这些大家族的核心成员,原来依附于宗家的边缘人员不在搬迁之列,否则咸阳也没那么大的承载力。
搬走大家族后,“子成年而不分家,税赋加倍”的律法随后跟上,秦始皇认为凭借这套组合拳,应该就能迅速实现变大家族为小家庭的战略构想。
但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六国的很多地区,百姓们以大家族聚居的方式已经生活了几百年了,家族中形成了相对完备的自治体系,哪是你一道政令就能随意改变的。
是,你的政令背后有大秦百万雄兵背书,你可以强迫那些大家族必须分家,但是人们心中的想法不是你百万大军能够掌控的了的,原本宗族内部能够解决的问题,现在全成为你秦帝国的问题了,你必须亲自下场给被你强行分家的人解决问题,这就是直接统治的代价。

大多数百姓可不去考虑你改变统治方式后社会运行效率变没变快,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变没变的更舒服,如果答案是没有,那么对不起,原六国人对秦帝国的态度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国是你灭的,家也是你拆的。
他们会认同这个新生帝国才有鬼。
当然,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去认真思考一个流传很久的说法了:权力与责任的对等。
对等很多人对权力与义务,或者说与责任对等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他们认为掌握了绝对权力的人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但这种想法显然忽略了一点:那些所谓掌握绝对权力的人,都必须要为一件事负责:一旦你的统治失误,你就必须亲自去面对你治下之人的滔天怒火,他治下那些愤怒的人,要扒皮抽筋、挫骨扬灰时,没有人能替你挡着。
绝对权力的背后是无限的风险和无限的责任,这才是权力与义务关系的本质。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更容易理解直接统治与间接统治的区别了:你要绝对统治,你就得对你治下的人负责,他们过得不好,要找的人就是你;而如果你只是间接统治,就不用有这样的烦恼,你只是一个按时收点税的符号,治下百姓的生活状态有人替你管理,你无需安排那么多官吏去直接管理那些百姓的饮食起居,这样一来,他们的怒火烧不到你头上。
好,现在明白了这一点,秦帝国灭亡时的状态就呼之欲出了,秦帝国要直接统治,而且这种直接还非常彻底,要把大家族打散,让天下所有人都以小家庭的形式被管理。
直接管理产生的成本都得由秦帝国自己承担,于是高税负、强徭役和严刑峻法就不能少。
秦帝国把所有中间阶层全打掉了,至少名义上是全打掉了,百姓的所有怒火都会直接发泄到秦帝国头上。
秦末大起义时,有这样一个颇为讽刺的细节,陈胜吴广的起义军三个月就打到秦帝国的腹地关中平原,他们是怎么打过去的呢?是顺着秦直道打过去了。

这黑色幽默般的滑稽剧情正是秦帝国直接统治带来的双刃剑效果的直接体现:你强时,天下任你直接驱驰,但一旦你不强了,没有力量能够构成你统治瓦解的缓冲带,那些反噬力量将直接砸在你头上,没有中间地带。
你要么强,要么死,连一个缓慢衰落的过程都不会有。
不可能平衡集权和轻徭薄赋之间构成了一个不可能平衡。
你要绝对控制,绝对的集权,就不可能轻徭薄赋,因为在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中,最高统治者如果要实行直接控制,越到下层,所有的官吏数量和统治成本越高。
皇帝本身不产生能量和资源,他的能量和资源完全来自治下的国家,如果要维持高度的直接统治,就需要大量官吏去把他的意识执行下去,这份成本皇帝得自己出。
皇帝要想自己出,就得对民间征重税,民间的负担就不可能太轻。
说到这里,可能有些人会有疑问:汉文帝时期,不就实现了集权和轻徭薄赋同步并举了嘛。
事实并非如此,汉文帝时期集权不假,但他集的大多是官僚集团的权,这份权力与皇权一样都属于中央权力,这样的顶层权力争夺对底层的影响是有限的;而对于诸侯王手中的地方权力,汉文帝只是“动”,却没有直接去抢,具体来说,就是汉文帝只是干涉当地诸侯王的继承人问题,有时候把一个大国分成几个小国,但是并没有直接收回,他对于这些诸侯国实行的依旧间接统治。
世间从来就没有完美的方案,想保住一些东西,就得放弃一些东西,而这样的取舍当然是有优先级的。
好了,现在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汉帝国为什么那么强调“孝”。
取舍优先级上文已经说过,直接统治比间接统治要付出的成本高得多,而直接统治成本中,越到下层越高。

所以对于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来说,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讲,性价比最高的选择是把最基层的权力扔给当地,让他们自治,放弃,或者说适当放松权力的“最后一公里”。
说到这里,大家脑子里应该已经闪现出那个著名的说法了:皇权不下县。
其实关于这个说法是有争议的,争议的点是皇权是否真的到县一级就不再产生影响了,历史学家费孝通、秦晖,和著名的三农专家温铁军老师都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不是皇权是不是具体终结在县一级,而是要说明一个现象,汉代开始,皇权对于最基层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放权自治的方式。
由于放弃的权力是最低一级,皇帝暂时不用担心自治下那些地头蛇们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因为他们与掌握皇权的自己相比实在是太小儿科。
权力有很多种形式,有武力,有政令,有律法,还有思想和教化。在不同的层级选择使用哪种权力,是一件很考验统治者能力的事。
以上这些权力中,武力和政令都有成本,律法虽然表面上没有成本,但是你制定的律法如果不被执行,损害的是你皇权的信用和威严,这是一种隐性成本,而思想与教化,却是一种无需付出成本的权力。
如果用武力,用政令去直接统治社会的最基层,需要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但是如果只是进行道德宣传,几乎不用付出什么成本。
让我们再来看看汉帝国用以立国的“孝”吧,他相当于给地方自治定了个调,家庭中,长辈说了算,家族中,族长说了算,但是说了算的人,又得符合“孝”的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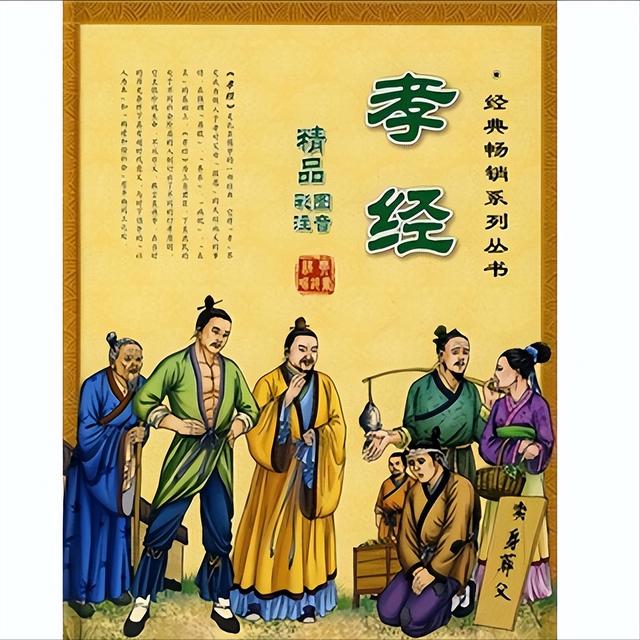
家庭内部的“孝”与国家里的“忠”是相适应的,如果一个人公开忤逆,他也就自动违背的“孝”的原则。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汉帝国在这道权力取舍题上做的一直相当不错,这样的权力艺术被汉文帝刘恒玩到了极致,大汉能摆脱秦二世而亡的命运,享受两段200年国祚,正是来自于此。
但是,依旧如上文所言,取舍之间皆有代价,权力游戏中只有动态平衡,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只不过秦那种完全控制的刚猛方案注定快速崩溃,而汉这种放松对最基层的直接控制的方式也不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自救半世纪汉帝国的基层放权相比于秦帝国的完全控制确实将统治成本大幅降低,统治成本低了,皇帝就可以轻徭薄赋,所以大汉帝国不但没二世而亡,还迎来了文景之治。
这种基层放权的好处是即便地方宗族等势力控制一部分地方权力,其与皇权的差距也是天壤之别,皇帝想收拾你简直轻而易举,但坏处确是这种来自基层的地方豪强,其权力将从最基层开始“稳扎稳打”,一步步向上反噬。由于这种权力是从基层产生的,它的生命力极强,且死而不僵。
文帝、景帝时期,地方豪强的势力还相对稚嫩,一个郅都就能轻松打掉济南郡的豪强群体。
但是时间来到武帝时期,这种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一些大的地方豪强,已经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这些地方势力之强,已经到了让武帝寝食难安的地步。
武帝必须拿起权力的大棒,转动起国家的齿轮,向天下豪强们挥刀了。
武帝一朝,在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频繁出手,其中有妙手,也有昏招,但与豪强群体的缠斗却贯穿了其50年执政生涯的始终,这是他的漫长自救之路。
但汉武大帝终究是一代雄主,他把自救的艺术玩得如此轰轰烈烈。
在接下来的50年中,汉武帝将在一次次试错后将权力游戏臻入化境,他能刚猛无比地将十几万大军砸向千里之外的漠北,也能让百姓间互相检举揭发,在拿走利益的同时巧妙地让矛盾在民间自行化解。
历史是所有一同书写而成的,但历史老人却又像一个无情赶路人,他并不在乎每一个人的感受,只是把一个个历史问题仍到一个个个体手中,有一个叫刘彻的年轻人,他拿到了那张最复杂的考卷,他躬身入局,大时代即将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