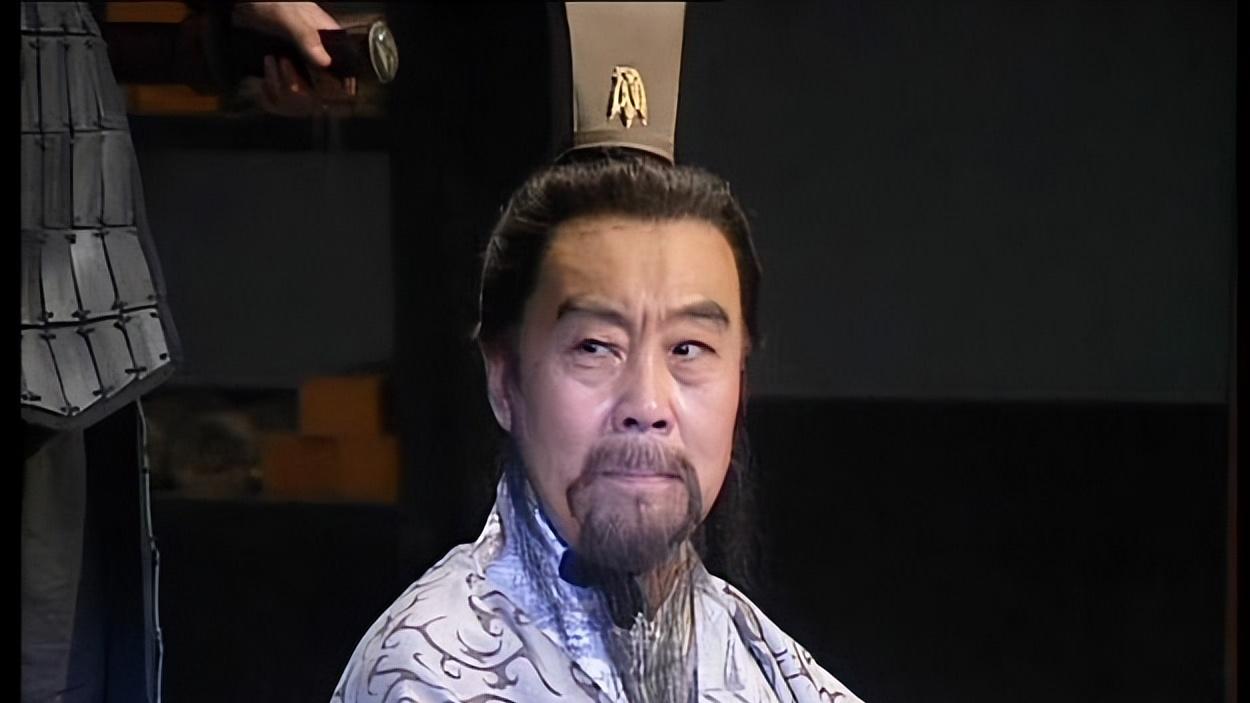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当蒋介石再次请求苏联参战时,斯大林给出了苏联参战的条件——日本侵犯苏联领土。斯大林这次答复,使国民政府认识到争取苏联立即对日作战的想法并不现实。
于是蒋介石将对苏联策略的两个环节调了一个个儿:先争取与苏联订立互助条约,正式结成政治同盟,再伺机提出苏联出兵问题。
苏联不仅成为当时中国抗战事业的唯一支持者,而且这种支持实际上已经上升为实际同盟关系的水平。
张鼓峰事件——签订互助条约的第一次尝试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正出访巴黎的孙科,收到蒋介石令他访问苏联的电令。
恰在此时,发生了张鼓峰事件(又称哈桑湖事件、张高峰事件)。
张鼓峰位于中、苏、朝三国交界处,其南侧为防川湖,北侧为苏联的哈桑湖,西北面有一座叫沙草峰的小山。根据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俄《珲春界约》,中苏边界线经过张鼓峰东侧山麓,整个张鼓峰属于中国领土。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7月日本关东军将张鼓峰被苏军控制的部分夺回,不断挑起伪满与苏联的边界纠纷。8月6日,苏军发起反击,20%的日军被歼,关东军第19师团遭到惨败,余部退回图们。

在哈桑湖事件中,日军攻入了苏联领土,已经符合斯大林原来设定的苏联对日作战条件。蒋介石认为这是签订中苏同盟条约的绝好机会,立即电示在巴黎的孙科,要他再次访问莫斯科,重新与苏联政府商谈签署新条约一事。
8月13日,孙科在巴黎致信斯大林,说在他回国了解情况后,即返莫斯科访问,“以便恢复和保障远东和平与苏联在军事和外交行动上,进行更直接和更全面合作的谈判”。蒋介石同时指示张冲向卢干滋提议,双方军队就订立中苏军事同盟问题立即进行谈判。
但苏联认为,张鼓峰事件仅仅是一次边界冲突,并非是日军大规模入侵苏联的信号,事件本身不足以动摇苏联中立日本的既定方针。因此,在苏军进行第二次反击的前两天,即8月4日,李维诺夫就与日本驻苏联大使重光葵进行停战谈判并很快达成协议,双方军队都撤出了争议地区。这次武装冲突就此和平解决了。
但蒋介石依然以哈桑湖事件为突破点,争取与苏联签订互助性质的条约。
孙科访苏的泡汤他在汉口两次会见回国做第三次访苏准备的孙科,指示其先与卢干滋就中苏签订互助性质的条约交换意见。
8月26、27日,孙科两次拜访卢干滋,并以中国政府和蒋介石的名义,正式提出要与苏联政府立即进行缔结秘密条约谈判事宜。

孙科
孙科说,两个月前他在巴黎得知发生苏联与日本的边境事件,蒋介石来电建议他返回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行新条约的谈判。
回到汉口后,与蒋介石进行两次谈话,蒋委托他与苏联全权代表就条约问题交换意见,条约内容包括军事合作,但不规定苏联有参战的义务;对外严格保密。
这是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向苏联提出的关于进行互助条约谈判最具体、最正式的建议,而且回避了苏联最不愿意接受的军事介入中国抗战的要求;同时严格对条约保密,避免苏联对因中苏缔约而恶化国际关系的担心。
卢干滋回答孙科说,条约一旦签订,想保住秘密绝不可能;还说了一大通订约将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后果的话。但他允诺,将把中国政府这一十分具体的建议通报苏联政府。
8月28日,李维诺夫电示卢干滋:对中国,苏联的立场没有改变。即使孙科到访也不会改变。如果他来,我们当然不能阻挠,但您不应给他造成因他的来访就能改变我们立场的错觉。

孙科
这一电令,将孙科前往莫斯科谈判的一线活路也堵死了。
由于卢干滋说“密约并不能保密”,蒋介石决定干脆订立公开条约。8月30日,孙科派梁寒操向卢干滋作了更正,说中国政府将其建议更改为商讨具有公开政治性质的条约。8月31日蒋介石亲自同卢干滋举行会谈。他指出,必须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并且应该是公开的,蒋介石这次对卢干滋的谈话,一改过去求援口气,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拒绝订约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卢干滋每次碰到这种场合,都大讲不订约的好处,这次他只说苏联尚无改变立场的理由,但表示尽快转达蒋介石的建议。
9月8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致电卢干滋,要他转达苏联领导人对蒋介石的答复:(1)苏联认为,没有英国或美国,苏联孤立对日作战是不适宜的。因为苏联单独行动会恶化中国的国际环境,改善日本的国际环境。其他国家会认为,苏联要将中国布尔什维克化。(2)苏联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会对日作战:①如果日本进攻苏联;②如果英国或美国联合对日作战;③国际联盟责成太平洋国家反对日本。(3)苏联准备在任何条件下都按照已签订的中苏条约帮助中国的防卫能力。
苏联政府的答复,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答非所问。因为蒋介石一再强调缔约目的不在于苏联必须参战,而是为了奠定中苏关系未来的基础。
但斯大林却认为,蒋介石的目的就在于将苏联绑上对日作战的战车,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对中国承担互相援助的条约义务。就实际情况而言,蒋介石确实想通过订立互助条约,一步步地将苏联“拉下水”——参加对日作战。但在公开要求苏联出兵遭到拒绝后,他千方百计地回避这个核心问题,想先通过“扫清外围”的方式,最后达到逼苏联出兵的目的。这样,中苏双方便围绕是否订约问题,不断相互重复多次说过的话语。

孙科
卢干滋在收到上述电报的当天,即按照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精神向孙科解释苏联不能签约的理由。
慕尼黑协定与蒋介石的第二次努力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29到30日,英、法、德、意签订慕尼黑协定,四大国达成交易:将沿德捷边界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苏台德地区划归德国,以使德国将矛头东指苏联。
苏联西部安全面临空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更不可能与中国订立互助条约,去刺激东方的日本。但蒋介石却认为慕尼黑协定使中苏更加接近的条件成熟了,又进行了一番签约努力。
9月30日蒋介石在得到慕尼黑协议签字的消息后,随即紧急会见卢干滋,再次亲自提出签订互助条约的要求。他指出,慕尼黑会议的结果必然导致欧、亚大陆的重大转折:其他国家对英法态度必将发生剧变。在这变化的形势下,中苏转向更加紧密合作的必要性业已成熟”,合作的最低限度应该签订“互助条约”。
欧洲长期稳定是不可能的,欧战迫在眉睫,但日中两国都不会参加欧战,中国将集中全力抵抗日本。苏联等西方大国将无暇东顾,中国会孤军对日作战。以战争解决欧洲问题将抛开远东问题的解决。中国人民担心中国会成为孤岛,而要求与苏联订约;但并不要求苏联立刻采取武装行动,只是希望两国建立密切的相互关系并把中国问题与欧洲问题联系起来解决。
第二天,蒋介石将他与卢干滋会谈内容电告驻苏大使杨杰,指示他“本此意旨再加以斟酌、补充,即向史、伏二当局恳切详言,询其意见,并向苏外交部活动,务宜尽力促苏积极并动以利害大义,并将谈话结果电复为盼”。

蒋瑞元
蒋介石这次缔约努力仍然是南辕北辙。
10月5日,杨杰电告蒋介石:“连日访伏帅及苏外部,叩以国联实施第十六条时苏联如何行动,据称:助我抗战是苏联一贯方针。李维诺夫昨夜始回莫,正整理文件,即向政府报告,政府听取李外长报告后始能决定办法,届时当再详告。”
其实,慕尼黑会议丝毫没有动摇苏联的东方政策。李维诺夫参加会议回来后,于10月9日致电卢干滋说:欧洲的新局势不会改变苏联的立场,苏中互助条约有可能被列强用来孤立和真正背弃中华民国,因为列强会将中华民国说成是东方布尔什维主义的先锋。
实际上,苏联是怕自己被说成是输出“布尔什维主义先锋”而成为西方众矢之的,如订约中华民国将受到孤立云云,并不存在。
武汉保卫战期间是中国军民抗击日本大规模进攻最艰苦的阶段,期间发生了哈桑湖事件并举行了慕尼黑会议。蒋介石以这些大事件为突破口,力争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以鼓舞军民士气,可以说能做的都做到了。但直到10月底,广州、武汉相继失陷,仍然没有获得成功。
武汉会战与蒋介石的第三次努力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国内和国际局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季又发生了日苏之间的诺门罕事件(又称哈拉欣河事件)。国际国内出现的新形势,又促使蒋介石为订立中苏盟约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正如蒋介石所预料的那样,武汉失守后导致了国内投降派的气焰甚嚣尘上。日本也加强了对国民政府的分化、诱降活动。
日本政府发表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声称如果国民政府放弃过去的抵抗政策,更换其人事组织,使其新生,日本不反对它参加建设“新秩序”。
这一声明就是策动汪精卫等一批民族败类公开投降日本。汪精卫当时是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他在日本的利诱下,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1月派代表与日本签订秘密的《日华协议纪录》,12月率领周佛海等人从重庆出逃,并发表公然认贼作父的声明,甘心充当卖国贼。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3月在日本的导演下,于南京拼凑起汪伪政府,组织伪军,为日本强盗聚敛沦陷区财富,奴役沦陷区人民,帮助日寇扩大侵华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已经没有退路,他更加需要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振奋国民精神,坚持进行抗战,维系自己的统治地位。
慕尼黑会议后,欧洲环境不但没有改善,而且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日本扩大对华侵略,触及英、法、美利益,激化了他们同日本的矛盾,开始对华表示同情,并给予一定的物质援助,以便牵制日本。但他们东方政策的核心仍然是以损害中国权益谋求对日妥协,维持其在东方的殖民体系。美国是批评日本最厉害的西方国家,但它并不中断对日贸易,依然卖给日本大量钢铁、石油、机器设备等军事物资。

西方大国这种骑墙政策,一方面促使蒋介石千方百计争取它们,在对外政策上尽量向他们靠拢,另一方面也令蒋介石失望。当时最有条件争取的,对中国来说,仍然是苏联。于是,蒋介石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底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上半年再一次争取与苏联订立互助条约。
孙科在苏联的冷遇这时苏联前两次对华信用贷款已经用完,需要派最高级人物与苏联签订第三次贷款协定,同时争取完成与苏联订立互助条约的任务。
为此,蒋介石任命孙科为全权特使再次访问莫斯科。孙科是立法院院长、国民党中的亲苏派,加之他是孙中山的儿子这一特殊身份,是打开中苏关系最恰当的人选,因此他一再受命出使苏联。
鉴于以前苏联历次拒绝签订互助条约的教训,蒋介石决定,这次关于互助条约谈判,以政治同盟形式提出订约,加强中国与苏联的政治关系,并促进苏、美、英、法等国在远东的合作。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22日,即孙科赴苏前夕,蒋介石委托孙科转交斯大林一封长信和《中苏保障东亚和平协议草案》以及《中国与苏联为巩固远东和平保障两国革命建设应更加密切提携之意见》书。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蒋介石在信中对斯大林给予的援助表示衷心感谢,分析了中国抗战形势,向斯大林提出两项要求:(1)两次总额为1亿美元的苏联贷款在去年已经用完,为弥补军事物资的短缺,需要苏联再给予约1亿5千万美元的贷款,以保障对敌作战的彻底胜利。(2)为了保障战后中国的重建和解除日本对中苏两国的共同威胁,“在未来五年里苏联和中国应该更紧密地结成统一战线。作为对我们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补充,我们两国应该再迈一步,签署远东保障和平公约”,并欢迎其他热爱和平、支持集体安全原则的国家加入这一协议。
为防止中间转达走样,孙科在4月4日临行前的火车车厢上才将上述文件的英文本交给卢干滋。以期由他先行通报莫斯科。孙科从重庆启程,经阿拉木图,于4月7日抵达莫斯科。4月8日拜会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说明来意,表明其主要目的是要求苏联政府对华广泛和有效的援助,但决不指望苏联直接参加对日战争。
他要求会见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转达所带来的文件,讨论政治问题和一些具体问题。
直到4月13日斯大林仍未接见孙科,孙只得将蒋介石致斯大林的信件及预备文件的英文译本交给李维诺夫,请其代为转交。同日,李维诺夫写信向斯大林报告了有关情况。
此时欧洲局势进一步恶化,3月15日德军占领捷克的土地,第二天希特勒宣布将捷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作为保护国并入德国,并将斯洛伐克置于德国保护之下。3月初德国强迫立陶宛将克莱佩达港转让给自己,将侵略矛头直指紧邻苏联边境的波罗的海沿岸。
与此同时,在3到4月间,德国明显地加强了进攻波兰的准备。面对气势汹汹的德国,英法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接受苏联“集体安全”建议的动向。英国于3月21日提出与苏联、法国和波兰签订宣言的建议。“苏联政府把这一宣言视为在建立集体安全体系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全力以赴地争取与英法等国建立欧洲集体安全公约。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暂时无暇关顾孙科的来访;而且来自德国的威胁已迫在眉睫,东方的日本则被置于更加次要的地位。
尽管蒋介石急如星火,一再来电催问孙科交涉的结果,询问苏联对华态度是否改变,孙科却无法做出回答。
5月13日,在孙科抵苏一个多月后,斯大林终于拿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接见了他,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参加会见。根据孙科的报告,会商结果是:“(一)苏联援助中国抗日,始终如一,绝无问题。(二)三次借款美金1万五千万美金,允即照办,日内签约。(三)远东保障和平公约须视英、法、美能否参加,苏联绝无问题,英、法、美若不参加,和平仍无保障。”经过具体谈判,6月13日孙科签署了苏联第三次贷款协定和贸易协定。
等待对西方谈判结果,就是斯大林一再推迟会见孙科的原因。由于英法最后拒绝承担苏联提出的义务,保障欧洲安全协议没有达成。对《保障东亚和平协议》,苏联就更不感兴趣了。所以,在莫洛托夫宣布苏联不能接受英法反建议的前一天,斯大林会见了孙科,只作出给中国贷款的决定。
互助条约的最后一次尝试第三次借款条约签订后的两三个月内国际上发生了三件大事: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日发生诺门罕之战。
按蒋介石的预计,这三件大事直接影响中苏关系的走向。

出乎国民政府意料的是,苏联与其东西方威胁者德国和日本发生了一和一战的情况。对德国,通过公开的和秘密的谈判,苏联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8月23日同德国签订了为期10年的《互不侵犯条约》。这是苏联通过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而与德国达成的暂时协定,但毕竟将战争推迟了两年。
这是苏联外交取得的重大胜利。尽管谈判是在严格保密下进行的,但外界还是出现种种苏德交易的传闻。令蒋介石最担心的是,苏日之间是否也将签署一个类似的互不侵犯条约,而且英日之间也可能达成妥协,这将对中国十分不利。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不到10天,德国于9月1日进攻波兰,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苏联采取何种东方政策令蒋介石极为担心。恰恰这时苏日之间的诺门罕战役正进入高潮,又给蒋介石与苏联结盟带来希望。
任何苏日武装冲突都是中苏亲近的推动力。诺门罕这样大的局部战争自然引起中国的高度关注。还在苏军对日军合围之前,蒋介石于8月1日接见苏联代表谢维尔内,问他“关于满蒙冲突的情况”,“中国专家能否参加红军秋季演习”?所谓“红军秋季演习”,就是暗指围歼日军作战。蒋介石此举意在试探苏联是否允许中国参与一定的军事合作。
谢维尔内让蒋介石去问莫斯科,实际上拒绝回答。但蒋介石仍想借诺门罕事件为建立中苏军事同盟做进一步努力。

蒋瑞元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塔斯社作了报道,蒋介石敏感地感到,苏联对外政策发生了剧变。
与蒋介石预料的相反,诺门罕事件不但没有改变苏联中立日本的战略决策,而且加速了这一战略的实现。
从“满洲国”成立后,苏联一直争取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主要由于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政策,才使苏联没能实现它追求的目标。
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都没能使苏联放弃这一目标。在诺门罕整个事件的全过程中,苏联都以中立日本为出发点采取行动,在军事上对关东军实行狠狠的打击,旨在遏制日军不可一世的气焰,但不求扩大战果;在舆论上不做任何渲染,不像对诺门罕事件那样在国内大肆进行舆论宣传,以免激起两国国民更大的敌对情绪。在外交上则采取灵活策略,只要求恢复满蒙“边界”的实际控制线,预留出回旋的空间。这些措施收到了实际效果。

日本在诺门罕事件中受到一次严重教训,它认识到苏联这根硬骨头是不好啃的。日军参谋本部果断地取消了关东军的报复计划,严令前线部队在9月4日以前,停止一切对苏联的进攻,把军队撤到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哈拉欣河以东)以外;并将责任人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和参谋长矶谷等人免职。
9月15日,苏日签订了解决该事件的善后处理协定,满蒙“边界”恢复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双方的实际控制线,这次事件便就此平息下去。
诺门罕事件后,对国民政府来说,任何可供利用来与苏联签订同盟条约的机会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