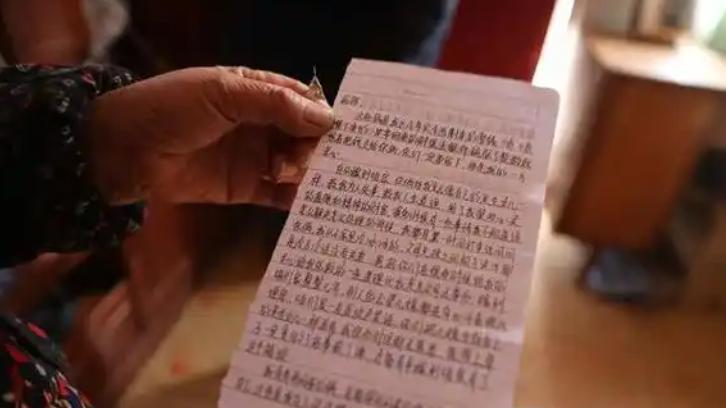“你干嘛做这些东西给我吃啊?咱俩什么关系?”99岁的徐如珍靠坐在轮椅上,吃着儿子李健人刚端过去的半流食早餐,却迟疑着问出这句话。
坐在她面前的李健人,此刻想哭但只能压抑住情绪。
他缓缓地回答:“妈,我是浩铭啊,你的儿子。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是我妈。”徐如珍挠了挠头,没再追问,继续吃着面前的食物。

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李健人家里上演。
51岁的李健人为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已经辞掉了工作,用尽所有的心力去陪伴母亲。
而一位不再记得自己儿子的人,是否真的有必要受到如此精心的照顾?
邻居和家人都劝他把母亲送去养老院,但他始终没答应。
他的理由,是母亲离不开他。
母亲患病后不再认儿子,记忆的混乱让亲情成了考验阿尔茨海默症像是从徐如珍脑海里带走了一切。

以前的她精明能干,在小学当老师,和丈夫含辛茹苦地拉扯着五个孩子。
如今,99岁的她坐在轮椅上,连自己的小儿子都认不出来。
“浩铭是谁?弟弟还是哥哥?”这是徐如珍每天都会问李健人的问题。
多年来,她记不住眼前这个人是自己的儿子,有时以为他是弟弟,有时甚至直接当他是邻居。
但在她心里,儿子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种记忆的混乱,让亲情的表达变得未知而又陌生。
李健人一边照顾母亲的生活起居,一边试图用她曾经喊过的“小名”去唤醒她的记忆,但效果甚微。
尽管如此,李健人依旧坚持留在母亲身边。
他说:“她曾经把我养大,现在轮到我自己一点点把她扶到老。”
辞职在家,日复一日的半流食三餐背后有多少辛酸辞掉工作专门陪母亲,是李健人2015年做出的决定。

那时,母亲腿部骨折,再加上阿尔茨海默症,生活几乎无法自理。
医生的建议是,母亲需要吃易消化的半流食,否则肠胃可能会出问题。
他买来破壁机,每天早晨六点起床,开始洗菜、切块、打碎。
一日三餐如此,每顿都花上不少时间。
弄好食物后,他还要一勺一勺地喂母亲。
母亲吃得慢,他就耐心地等。
虽然这些食物很适合母亲,但她时不时还是会问:“你费那么大劲干嘛?我们是什么关系?”

看到母亲连半点记忆都留不住,李健人不是没有伤心过,但更多的是努力适应。
他后来学会用玩笑赶走这种心酸,比如说:“要不是你要吃,我哪有耐心做这些!”母亲每次都笑了,也就没再多说。
这些年,除了半流食三餐,最让李健人崩溃的还有像“尿急”这样的小事。
夜里母亲需要起身几次,上完还得擦拭妥当,清洁马桶。

有时实在累极了,他只能蜷在沙发上假寐片刻,再起来继续忙碌。
拒绝养老院,李健人坚持“妈妈得有熟悉的照顾”这样的日子,不止家人觉得辛苦,邻居看在眼里也时常提议:“把老人送去养老院吧,你一个大男人,哪能照料这么精细?
”李健人每次总是摇头拒绝。他说:“送到养老院,没人知道她夜里什么时候会叫,厕所要怎么伺候,她需要有人一直陪着。”于是,他坚持把母亲留在自己身边。
李健人的二姐李卫红也心疼小弟,提出轮换照顾母亲的办法,或者大家分摊钱,把老人送到好一点的养老院。

一开始,李健人说会考虑,但后来还是没松口。
他的理由是,自己“更明白母亲的生活习惯”,而且母亲只能吃特殊的流食饭,这些别人都不一定会注意。
二姐最后找到一家提供特殊护理的养老院,说可以每天盯着老人,给她提供细致服务,但李健人依然不同意。
他说:“如果我不在母亲身边,她连名字都叫不上来,你们觉得那样能让她安心吗?”
从含辛茹苦到倾尽全力,他坚持陪母亲走完最后的路其实,这一切的根源,是曾经母亲陪伴他的点点滴滴。

李健人一直记得小时候的一件事:当时家里穷,母亲把仅有的两个鸡蛋煮熟,每人分半个,而她自己一点都没吃。
母亲就是这样,愿意倾尽全力去守护自己最亲近的人。
现在,李健人只是选择用同样的方式,去回馈母亲。
“单身也没关系,重要的是她过得好。”面对别人的质疑和劝导,李健人这样回复。
他似乎很少回顾自己失去的东西,比如事业、婚姻、自由。
他愿意这样单一而重复地陪母亲走完最后的路。

每个人对尽孝的理解都不相同。
有些人选择将父母送去设施完善的养老院,给他们提供专业的生活保障;也有像李健人这样的人,他们觉得亲力亲为才是真正的陪伴。
这两种选择其实都没有对错可言,只是人们心中那份情感的体现方式不一样。
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深思:母亲养育了孩子一生,是否应该将孩子的一生都用来偿还?
也许,孝顺的意义,并不只是日复一日的辛劳付出,而是如何让父母在晚年活得自在、体面。
而这种选择的权利,同样也属于每一个尽力回应爱的孩子。
与其争论什么是对与错,不如试着多看见亲人的付出与用心。

这世上,最长久的相守是心意的互通,而最动人的亲情不一定是形式上的标准,而是一份发自内心的不求回报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