蝼蚁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多:若论绝对数量,今天人口总数比汉唐时期多得多,儿童总数没有可比性;但若论儿童数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与现代相比汉唐时期真的是非常高,这不光是一般看法,我自己的研究也足以说明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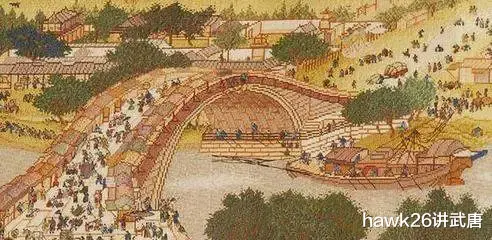
我写的“汉墓《集簿》中的高龄人口数据是否可信?”一文,该文根据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的数据,计算出6岁以下低龄人口占比为18.8%,若论周岁这应该是0-5岁或0-4岁的占比。而根据我国第五、六、七次人口普查结果,进入新千年以来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占比在7%以下,甚至完全可能更低,不及西汉后期东海郡的一半。
在人口统计中的儿童是指年龄在0-14周岁的人,0-5岁占比18.8%,估计儿童占比会在1/3左右或更多,根据我国第六、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最近儿童占比差不多只有西汉东海郡的一半。与现代社会相比,包括汉唐在内的古代社会人口结构是极其年轻化的,汉墓《集簿》不过提供了又一个具体例子罢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古代社会或太平盛世是否自然而然地生机勃勃呢?

恰恰相反,与现代社会相比任何时期的古代社会都显得死气沉沉。除了开头提到的《汉唐盛世中的蝼蚁之妇女》以外,我还发表了我的另一篇文章《汉唐盛世老百姓有好日子过?》,这两篇文章用不同的方法估算了古代盛世中的出生率,并进一步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估算出汉唐盛世的死亡率高达30‰。1960年是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一年,死亡率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峰25.43‰,古代太平盛世死亡率竟比这还高!
全社会平均水平都这么高,具体到高危群体数据会更加可怕:比如古代妇女一次生育过程死亡率就高达100‰左右。考虑本文主题儿童的话,情况可能更恐怖,上网搜索“婴儿死亡率”,可以发现并没有中国进入现代以前的确切数据,但粗略估计在200‰左右,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比率,竟有1/5的新生儿活不到一周岁!怀疑这样的数据也正常:实际情况真有这么可怕吗?

可以根据现有数据估算古代婴儿死亡率,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在国家统计局官网上的“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找到,查询其中的“表6—4”“全国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状况(1999.11.1-2000.10.31)”可知, 全社会死亡率平均水平为5.92‰,在整体死亡率低于6‰的情况下,0岁人口死亡率仍高达26.90‰,是平均水平的四五倍,和古代整体水平差不多。
在人口统计中0岁指的是不满1周岁,也就是婴儿所处的年龄段。在整体死亡率高达30‰的情况下,估计0岁或婴儿死亡率可能高达120‰或150‰这种水平: 26.90/5.92=4.544,30‰×4.544=136‰,这与网传高达200‰的婴儿死亡率有一定距离,但并不算远,无非是1/7或1/8与1/5上下的区别。
这是非常可怕的:即便在汉唐盛世这样的极品盛世中,也有1/8或1/7的新生儿活不到一周岁。如果不在极品盛世或处于乱世中会怎样,我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古代民众的一辈子,从出生开始就是一场大灾难,不光在中国,世界各地都存在类似情况。我写文章揭露中国古代糟糕的生存状态,不是为了贬低中国本身,而是要证明中国古代或其他地区的古代不是某些人口中的田园诗。

当下遇到的绝大部分问题无法通过复古解决:哪怕是古代最强盛的王朝唐朝,在最安定强盛的时期,与现代社会相比死亡率仍然高得可怕,最基本的生存都没有保障,哪里还谈得上其他方面呢?不过有一个方面唐朝或古代做得相当到位,既然生存没保障,为了让统治维持下去,就只有疯狂鼓励生育了。
具体手段网上讲了很多,这里我没必要多讲,只要把结果拿出来大家就能明白唐朝政府催生多么有效了。在《汉唐盛世中的蝼蚁之妇女》中我引用过张瑞华完成于2008年5月15日的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唐代妇女的生育研究——以墓志资料为研究中心》,在这篇硕士论文的“表2.5”“唐代生育率估测”中,可以发现整个唐朝不同时期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变化较小,不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均在5人左右,估测结果还显示,中唐和晚唐的生育率并没有低于初唐和盛唐,大型战乱对生育率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兵荒马乱的时代并没有比太平时节少生孩子,想催生可以参考唐朝政府的做法,对于维持高生育率、高出生率绝对有效:我在《汉唐盛世中的蝼蚁之妇女》中论证过,在古代人口结构比较年轻的情况下,一个妇女平均生育5个孩子意味着出生率在45‰左右,中唐晚唐动乱严重到什么程度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率还能超过40‰,催生是多么有效啊!
即使在目前育龄妇女占比降低的情况下,平均生5个孩子也意味着出生率超过30‰,考虑到现在中国14亿的人口基数,一年超过四千万新生儿绝对不用担心人口危机。唐朝政府鼓励生育的做法是有记载的,具体到生活细节且可操作性强,那么如此有效的方法现在为何不采用呢?有什么后果吗?
仅就妇女而言,变态地鼓励早婚多生会导致祸害一生的大灾难,我在《汉唐盛世中的蝼蚁之妇女》中论证过,大唐盛世中差不多会有2/5的妇女死于生育,算上各种并发症、后遗症这个比例完全能够提高到1/2,说有一半妇女因生育而死并不夸张。这还是盛世各种保障相对齐全的情况,若在中唐晚唐因生育而死的妇女占比只可能更高,这时低龄人口的处境同样会变得更糟。
中唐晚唐人口没有明显增长的趋势,尽管下降也并没有史书记载中的那样夸张,这时候出生率和死亡率应该是差不多的,估计死亡率会达到40‰或45‰这种高水平。婴儿死亡率约为平均死亡率的四五倍,会达到200‰上下这种恐怖水平,网上的搜索结果可不是危言耸听,即便在唐朝某些时期也真的可能有1/5的新生儿活不到1周岁,何况古代史上还有比中唐晚唐更乱的时期!
在那些更可怕的乱世中,婴儿死亡率明显高于200‰、达到300‰这种恐怖水平是完全有可能的。整体上看,古代婴儿死亡率的确可能高达200‰,这不是耸人听闻的虚构,而是骇人听闻的事实,平均看来古代的确有差不多1/5的新生儿活不到1周岁,情况只会比太平盛世更可怕。还有谁想通过复古来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吗?若是真回到古代,连最基础的婴儿生存权都没了!
哪里还谈得上解决别的什么问题呢?不过是在地狱和炼狱间转换罢了,就算是太平盛世,也有1/7或1/8的新生儿活不到1周岁,单看这一点就可以确定是人间地狱了。考虑到古代较高的出生率和高到离谱的婴儿死亡率,每年都有大量婴儿死亡,盛世中按比例看会少一些,但由于人口更多、出生率更高数量却不会更少。在什么年景都大量死亡,也是蝼蚁的典型特征之一。

更可怕的是,婴儿和蝼蚁还有一个共同点:年年都大量死亡,但史书中却少有记载。这一点婴儿甚至还不如昆虫,比如哪年蝗虫多了造成大灾还会留下记录,但年年生了这么多婴儿、同时死了很大一部分却一点儿也不见提及,这才是古代真正可怕的地方,恐怖的事情太常见就熟视无睹了。
对于古代史,一些人持有这种看法:一场乱局或瘟疫或天灾死的人就比历史人物的总数还多,真正了解历史和知晓历史人物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种看法有道理,据说二十多部正史中有传的人物不过三四万,全部历史人物的总数就在这样的量级上,如果古代一场乱局或瘟疫或天灾造成了几万人死亡,那就该谢天谢地了,但却仍没有讲明古代真正恐怖的地方在哪里。
太平时节有三四千万人口不算多,出生率为千分之四五十,每年就有一二百万的新生儿,其中有1/7或1/8死亡,这意味着每年都有十几万甚至二三十万婴儿死去。粗略估计就能发现,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数量比不过一年中死亡婴儿数量的零头,甚至可以小一个量级,要知道这考虑的还是太平时节。
甚至考虑太平时节也是低估,若假定有五六千万人口、出生率45‰、婴儿死亡率136‰,5000×45‰×136‰=30.6,6000×45‰×136‰=36.72,怎么看每年婴儿死亡都超过30万,可以确定比历史人物总数大一个量级。一年死亡的婴儿数量就比几千年的全部历史人物数量多得多,可你见过哪部史书中记录过这样的严重情况吗?至少我没看到过这样的记载,甚至都没听说过。
传统史书中甚至连大瘟疫大饥荒都是一笔带过的,病死饿死不知道多少万人的非常事件都记载得非常简略,只留下一个笼统的印象,哪里有篇幅记载太平年景里有多少婴儿夭折呢?不过,正史中对历史人物的记录可以说是连篇累牍、不厌其详,甚至有足够的篇幅记载哪位皇帝哪天临幸哪位妃子时出了怎样的意外。面对这种情况,谁还能赞美我国的传统历史记录体系吗?

古代真正恐怖的地方不在于自然灾害、战乱、饥荒、瘟疫等非常事件,而在于太平盛世中的正常情况都非常恐怖,更让人毛骨悚然、细思极恐的是这样的恐怖情况甚至连一丁点儿记载都没有留下。像“白骨露於野”、“大饥”、“人相食” 这类简略而笼统的描述,还能够让后人明白曾经的大型灾难有多么可怕,可太平盛世中每年有三四十万婴儿死亡,这样的悲惨情况却连简略而笼统的记述都没有,当然更没有必要以统计数字的方式来记录了!
婴儿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在历史记录者眼中年年都有大量婴儿死亡这件事甚至配不上一个数字,史官们根本不会去调查的:再强调一遍,有时蝼蚁的待遇都比这高。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主角从历史记载“仁义道德”的字缝中看出了“吃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真正恐怖的地方是历史记载的留白:字缝中隐藏的信息还可以根据记载的明文推断,而留白所代表的过去到底有多么恐怖是无法根据明文记载推断的。
古代太平盛世中民众的生存状态具体有多糟糕,往往不能直接依据史料记载推断,而需要综合考古、史料和现代科学成果才能给出结论:整体死亡率有多高、生育过程对妇女有多危险、每年死亡的婴儿有多大量……要想了解儿童的整体处境如何,同样需要类似的方法以揭露历史记载留白的恐怖。
虽然一直都有大量蝼蚁死亡,但同时一直都有更多的蝼蚁出生,这导致自然界中蝼蚁的数量一直很多:一般情况下蝼蚁的大量死亡并不会引起注意。太平盛世中儿童的处境也和蝼蚁类似,数量很多且在人口中的占比很高,由于出生率很高,儿童大量且高比例死亡的同时数量却在增长,在人口中的占比也不会明显降低,所以传统历史记载压根儿不写儿童高比例夭亡的事。
我本来打算根据《唐代妇女的生育研究——以墓志资料为研究中心》和关珊珊完成于2010年5月6日的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唐前期人口死亡年龄研究——以墓志资料为研究中心》这两篇文章的数据估计一下夭亡比例到底有多高,但仔细阅读这两篇文章以后,我发现其中关于少年儿童生死存亡的论述很不确切,有时所选样本太小不具有代表意义,有时不知道到底多岁以前死去算早亡,有时不能正确理解和处理自己收集到的数据……

总之,在研究儿童整体生存状态方面,这两篇我过去重点参考的文章并不能提供可靠依据。我只能以自己估算出的整体死亡率30‰为根据,粗略估计汉唐盛世中儿童的生存状态。婴幼儿时期是最危险的,本文前面估计出汉唐盛世中婴儿的死亡率超过100‰,儿童的早亡率应该比这明显高一些。
现代人口统计每5周岁为一段,如0-4岁、5-9岁、10-14岁……人口统计意义下的儿童是指前三段0-14岁,这里我把没活过儿童阶段称作早亡,那么汉唐盛世期间早亡率为多少呢?或者说有多高比例的人在世上没活过15年呢?这和死亡率直接相关,严格讲死亡率的单位是‰/年,这就给估算早亡率提供了可能,汉唐盛世期间整体死亡率约为30‰/年,可首先估算若干年后的存活率。
新生儿在头一年的死亡率远高于整体水平,但出生后的第二年也就1周岁以后死亡率就会明显下降,到2-4周岁就完全可能降低到整体平均水平上下或更低,而到了5-9周岁这一年龄段死亡率就会明显低于整体平均水平,接下来10-14周岁期间乃至青壮年时期死亡率仍然会保持差不多的较低水平。
30‰=0.03,1-0.03=0.97,0.97×1000‰=970‰,根据这一估算结果,从出生到1周岁的存活率为970‰,结果明显偏高;类似地,可估算从出生到5周岁的存活率,0.97^5×1000‰=859‰,结果仍然会明显偏高。

用类似方法估算从出生到10周岁的存活率,可得:0.97^10×1000‰=737‰;由于期间0-4岁死亡率明显高于30‰/年,5-9岁明显低于30‰/年,估算结果大体合理。活不到10周岁的比率相当高:1000‰-737‰=263‰,差不多是同时期婴儿死亡率的两倍。超过1/4的人只有个位数的寿命,多么可怕!
估计10-14周岁这5年间的存活率明显不能再用整体平均死亡率,不妨减半为15‰,15‰=0.015,1-0.015=0.985,0.985^5=0.927,对于已经活到10周岁的孩子来说,避免早亡已经不困难了,绝大部分或超过九成可以顺利活过10-14周岁这一年龄段,在10周岁前已经损失超过1/4的前提下。
据此可计算从出生到15周岁的存活率:737‰×0.927=684‰,也就是说只有不到七成的人能活过人口统计意义下的儿童阶段。1000‰-684‰=316‰,也就是说汉唐盛世期间早亡比例超过三成或接近1/3。出生率虽然高,但仅仅在儿童阶段就要损失差不多1/3,盛世中的生存状况竟然惨烈到这种程度!

就像对待每年有三四十万婴儿死亡一样,早亡比例大约1/3这么恐怖的情况在历史记载中也是留白,儿童的地位并不比婴儿高些。考虑盛唐七八千万的人口,出生率为45‰的话每年有超过三百万人出生,其中差不多有百万人活不到成年,哪怕对成年的定义只是达到15周岁。这是比任何天灾、饥荒、动乱、战争都残酷的情况,但你在传统史书中找到过对这种正常情况的记载吗?
反正我是没看到过这样记载社会整体情况的,可能史官不了解这样或是习以为常、熟视无睹了吧!传统历史记录中的真正恐怖就在于此,儿童和婴儿类似,地位甚至不及一些太多了就会成灾的昆虫。本文题目中把蝼蚁和儿童相提并论,其实儿童的地位还不如蝼蚁:其实古代盛世也是恐怖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