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月,保定市报社筹建《连心桥》编辑部,保定市报韩总编任《连心桥》总编辑,星期刊编辑室恒主任改任《连心桥》常务副总编辑,具体主持《连心桥》的编辑出版工作。责任编辑有凤编辑、平记者、管编辑、阿梅编辑。

恒副总编
《连心桥》是一份双拥共建刊物,双月刊,是保定市唯一国内发行的综合性刊物,因创刊时以反映保定市军地共建精神文明活动情况为主要内容,故名《连心桥》。原由相关部门(忘了是哪个部门)主办。创办于何时不详。大概是在一年前停刊。保定市报社接手主办后复刊。可能是在1994年4月出刊复刊后的第一期,为1994年第3 期,总第9期。之前可能出版了8期。之所以用“可能”二字,是因为我看了1994年第3 期的不清晰的封面,但无法查找更详细准确的信息(我保存着1994年第4、第5 、第6 期)。新编辑部的人员中阿梅不是报社的,我猜测她是原编辑部的人员,名字叫郭大梅。



恒主任拥有报社编采人员这个资源,自然要利用,常约编辑部的人写稿,6月,我应他之约写了一篇杂文。1994年8月出版的《连心桥》1994年第五期,刊登了这篇文章。内容如下:


公平的断想
文/苑战国
有人说,想生气就看中国队踢足球。就我的体验,还有好办法———读史,当然是中国史,最好近代的。
任你多么平和,不过一个时辰,也会恨不能钻进时间隧道,杀回那个时代。
大概是这太多的不平的刺激,中国人对贫富悬殊,格外敏感,格外警惕。
细怨起来,也许还有遗传的影响。孔圣人就提出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著名论断。老子也有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高论。
作为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最高理想也是“均贫富”。宋之王小波首举此义帜。明之李自成则喊出“均田免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向信徒们许诺创造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堂。
可翻遍历史,都是不平,西洋炮舰送来鸦片之后尤甚。哲人的论证,农夫的刀枪,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2
元代有歌曰∶“天遣魔军杀不平”,“杀尽不平方太平”。歌者慨然献出热血,可并没有浇出公平的花。于是又有了新的歌者,新的热血。
六百年歌荡神州,血沃中华,歌者终于可以亲手来安排世间公平。
脚上还没有洗净农田粪土的新的领导阶级,对于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公平,还不可能马上就做出科学的回答。
北方邻国已有模式的影响,中国农民千百年的梦想,于是便有了计划生产与计划分配。平均主义被作为公平的原则供奉起来。
长者喜欢怀旧,我便常接受“再教育”,虽没有说“一代不如一代”,可言必称五六十年代。幸好我也早生几年,虽然那时尚小,却已记事,在虔诚聆听之余,却不由地想∶这般公平的时代,何以那般穷?
3
自己的农田,自己的工厂,劳动不为剥削者,而为劳动者自己。人们相信,劳动热情会像火山般喷发,一定能够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可后来的发展,却令人瞠目。
新的公平,忽略了机会的均等,过份突出了结果的均等,当人们最终领会了它的真谛,竞然变成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人们既没有为了自己而关心大家,也没有为了大家而完善自己。
新的公平,没有创造出人们盼望的丰富的财富,只是创造出了平均发放的丰富的票证。
当然,除了票证还有口号。现在还记着一句,叫作“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放眼的结果,便是庆幸自己没有生在“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国度,幸免了“水深火热”的煎热。
后来,中国懂得了自己需要世界,我也知道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靠才干取得报酬的价值取向,竞然创造出了多于任何时代的社会财富。经过几十年的追赶,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拉得更大了。
4
一个新词产生了,它叫“反思”。一个新的比喻出现了,它叫“打破大锅饭”。于是有了竞争,有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看看吃穿住行,人们难以否认,分配的变化,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巨大丰富。听听周围的议论,人们也难以否认,这一变化已使分配不公的呼声日炽。
现代市场经济学院院长赵履宽认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所体现的公平,其内容类似有规则的体育比赛,它追求的是规则与过程的公平,而不是结果的均等。
“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是有关分配不公的最典型的议论。本人没有卖过茶叶蛋,不知它收入几何。但我想,这一职业向所有羡慕者敞开着大门,因为它绝不像造原子弹那样需要高深的学问,也不要文凭和职称,可街上并没有出现卖茶叶蛋者如云的壮观。
没人抢抓这一“机遇”,却依然议论如故,看来赵院长还难觅知音。
某企业在生产车间实行了记件工资,科室人员看一线工人有的多拿了钱,忿忿不平。厂长于是宣布,凡感觉分配不公者均可下车间,但至今没人报名。
工人们对此也忿忿∶干的不一样,就应该拿的不一样,收入拉不开,才是真正的不公平。
5
晋代诗人左思爱鸣不平,有几句诗突出表现了他的这种心境∶“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我的一位朋友,也有同样的心境,他说,他的电器维修技术相当不错,是厂里公认的骨干,可一个月不过拿二百多元。这在他们厂还算多的呢。可他的弟弟并无一技之长,在厂里连班组的先进都没评上过,可每月却拿四五百元。因为这在他弟弟厂里,他是拿得较少的了。
朋友表示,他无意与弟弟搞“平均主义”,只是想有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
但是,从目前情况看,职工还不能任意选择企业,企业也不能任意选择职工。社会分配不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没有完全实现机会的均等。
看来,我们面临的改革任务还十分艰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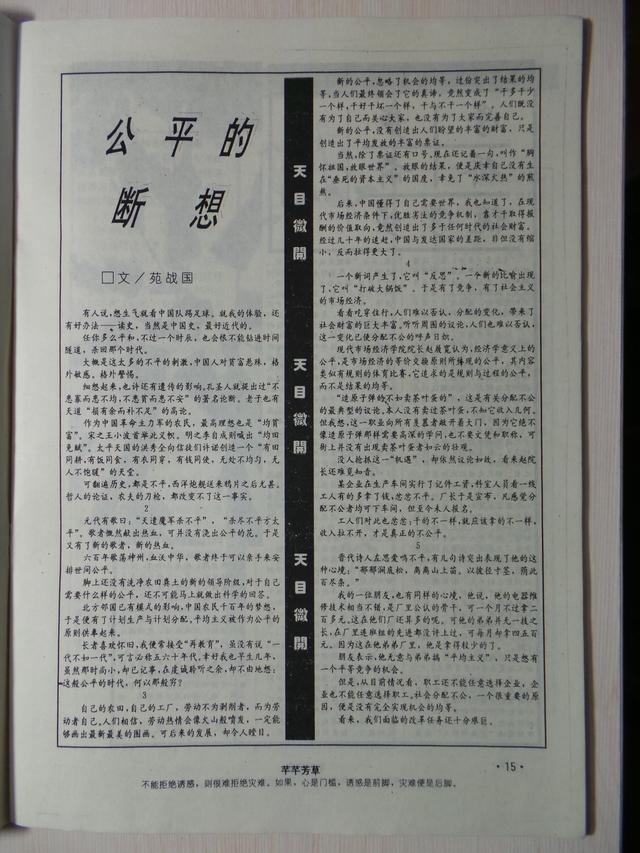
《连心桥》后来是个什么情况,我已记忆不得。但我的工作日志记载,1994年12月15日报社召开全体会时,韩总编曾要求大家,多抓重点稿件,并要求《连心桥》配合。看来那时《连心桥》编辑部还在正常运行。




(除《连心桥》3期,其余照片原件由笔者本人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