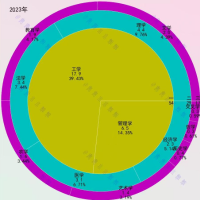本篇以苏东坡曾停留过的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为背景虚构创作。
宋绍圣三年腊月,岭南梅岭驿道积雪未消。
苏轼戴笠披蓑,跋涉在浈江水汽氤氲的石板路。谪居惠州三年后,再贬海南的谪令已传至曲江,但他的竹笠边缘还凝着惠州的雨痕。
驿亭外寒梅疏影横斜,忽然一阵暗香袭来,他摸过砚台,笔尖却意外晕开一片血红斑驳——
宣纸上"梅岭"二字竟渗出血珠,顺着"岭"字沟壑滴落在青砖路上,转瞬凝结成枚朱砂印。
"苏学士可否借宿寒庐?"不知何时,守林老人的草庐已现身寒梅深处。
屋内煨着罐陶罐,白雾漫过梁柱时,隐约浮现苏轼曾为巢谷刻的字迹:"士之生,死而异兮......"老人拂去陶罐上霜花,露出罐底篆印:政和年造。

苏轼惊问:"巢谷殁于元符二年,政和年间已是宣和之后,此罐何来?"老人笑抚梅桩:"岭上梅树,皆因学士《惠州一绝》活至今。"
话未落音,罐中茶汤忽地溢出,茶面映出梅关烽火台残影,烽火间依稀立着个披蓑老者,正是三年前惠州送别的自己。
是夜朔风卷雪,苏轼独对寒梅作画。案头狼毫笔忽然凝滞,纸面浮现出个穿青衫的书吏,抱来卷《岭表录异》。
书吏指着其中一页:"学士可看这荔枝记载?开宝七年,陈尧叟疏浚梅岭古道,曾在关楼壁画倒悬双鲤......"
话音未断,苏轼惊见窗外枯木垂枝竟幻化成张九龄祠的飞檐,祠前廊柱分明刻着张文献公的诗句,只是"海上生明月"中的"月"字,此刻却渗出墨色水珠,正滴在他砚台尚未干的荔枝图上。
大庾岭晨雾中,苏轼遇见个牵驴村童,斗笠下渗出本《陶渊明集》。
童子说:"先生莫走古道,昨夜岩崖落石,压死个吟'采菊东篱下'的书客。"苏轼瞥见石壁上镌着陶诗残句,最后六个字竟是"采菊东......有鬼"。
他突觉背后寒意,回头便见牵驴童子站在三里外的梅关关楼,驴背驮的不是行李,却是座微型梅岭,梅枝间悬挂的不是积雪,而是当年岭南贬官的流放诏书。
渡浈江时,渔夫高唱采莲曲,船桨拨碎水面月影,每道波纹里竟显出个被贬谪的影子:柳宗元举杯饮霜,李德裕焚稿痛哭,李纲被押时仍摩挲《易传》。
苏轼长篙点水,忽听得渔家女唱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最后一个"州"字未落,整片河面腾起白梅,花瓣上的寒霜凝结成她腰间玉佩的纹样,而那纹样分明是苏轼给朝云绣的同心结。
月圆之夜,苏轼枕着行囊在梅岭茅屋休憩。
月光渗进窗棂,将《赤壁赋》的墨迹染成暗红。他摩挲着砚台边角未干的朱砂,忽然想起陈太守送别时塞的半块糕印,此刻却显出文字:"坡老北归时,梅岭梅树尽焚。"
窗外风雪愈急,墙上的《寒食诗帖》被吹得字句纷飞,那些字在空中重组,拼出两句:"问汝平生功业,不是黄州惠州儋州。"
最后"州"字沉入地板裂痕,裂痕深处竟蜿蜒出条通往梅关的古驿道,道边石碑刻着:"绍圣四年甲子春,风雪压折梅枝三万株"。
梅关晓色朦胧时,苏轼倚着第三块"梅岭古道"界碑。
忽然看见界碑侧面浮现父亲苏洵的笔迹,写的是二十年前《上枢密韩太尉书》的片段。
字迹渐淡时,远处的粤北群山回荡起钟磬之音,原来是岭南道观的撞钟僧与僧伽大师对坐论禅,撞钟僧说:"昔年韩文公贬潮时,梅岭积雪四十九日。"老僧轻敲木鱼续道:"然坡翁贬儋后,梅岭每三年逢甲子必降瑞雪......"
渡口传来欸乃,苏轼登上北归孤舟。
船夫撑篙时,篙底沙砾里竟渗出张九龄的《感遇》诗,"兰叶春葳蕤"一句最末的"葳"字化作水珠坠入江中,激起涟漪绘成苏轼与朝云的剪影。
对岸传来歌谣:"坡公行过梅关后,满岭梅花尽点头。"船行深处,苏轼看见二十年前惠州丰湖书院的石碑在浪中浮沉,而浪尖上浮现的字迹分明是大赦诏书:"提举成都玉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