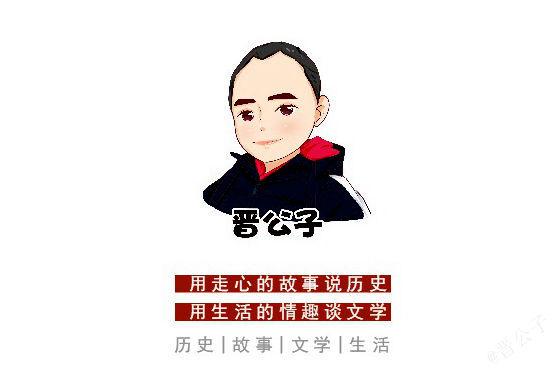本期话题
对西汉王朝来说,最大的边患莫过于北方的匈奴。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问题,亲率32万汉军与匈奴冒顿单于的40万精锐骑兵战于平城。
本来冒顿单于已经设下包围,将刘邦团团围困于白登,可是最终他却主动撤围放走了刘邦。为什么冒顿单于要放弃这擒王破军的千载良机?难道真是听信了一个女人的说辞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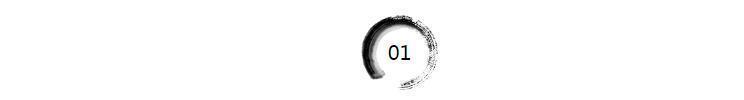

遥远的地平线的尽头,凛冽的北风掀起大漠黄沙滚滚而来。风声里,有杂沓纷乱的马蹄,有声如响箭的啸叫。渐渐地,黄尘卷近,大地开始了震颤。影影绰绰地,有无数身背长弓、手执利刃的勇士闪烁在昏暗的日影中。
正当人们努力睁大双眼,想要看真前方究竟是何人物的时候,那些马背上的勇士已经遮天蔽日地冲到了夯土的城墙之下,接踵而至的,便是血腥的屠戮……
公元前166年,戍守在朝那塞(今宁夏彭阳)上的汉军士兵所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恐怖的场景。那年冬天,匈奴老上单于亲率14万骑攻破朝那、萧关,一路烧杀抢掠,前路军锋直逼渭北的甘泉宫。站在渭南的长安城上向北眺望,广阔的平原处处狼烟,烽火星布。
敌人已经打到家门口来了!虽然怒不可遏的孝文帝刘恒钦点了六大将军,举尽全力以反击匈奴的侵略,但汉军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将匈奴人“礼送”出塞而已,丝毫伤不到那些强盗的皮毛。从攻破朝那到全身而退,老上单于在西汉的腹心之地——渭河平原上大模大样地逗留了整整一个月,而近在咫尺的孝文帝却拿他毫无办法。
在中原王朝对抗北方民族的历史上,大概也只有明末的崇祯帝,在清太宗皇太极发动的那几次入口之战中才品尝过这么窝囊的滋味吧?朝气蓬勃的西汉不是行将就木的大明,一手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孝文帝更不可与刚愎自用的亡国之君崇祯同日而语。但奇怪的是,西汉王朝最严重的边患都集中发生在孝文帝执政的这24年间:
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趋骑入侵上郡,长安告警……;
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天,老上单于亲御戎行,陷朝那,破萧关,烧回中,至甘泉……;
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冬天,六万匈奴铁骑兵分两路,攻入上郡、云中,首都保卫战的警报再一次响彻长安城的上空……

《中国军事通史·西汉军事史》一书就此评述说:
从汉高祖到汉文帝初期的20多年间,西汉王朝由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限制,对匈奴基本采取妥协政策,用和亲、开放关市的办法,以换取边境的安宁。
——《中国军事通史·西汉军事史》
孝文帝真是因为国力不敌,才无奈地任匈奴人在塞南为所欲为吗?恐怕未必。
文帝时期投靠匈奴的燕人中行说曾经对老上单于说过:“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史记·匈奴列传》)。对那些使用冷兵器作战的古代国家来说,人口数量是决定国力与军力的关键因素。而囿于极其有限的传世史料,中行说的这句话几乎成了描述匈奴人口规模的权威论断,直到今天还在各类历史研究著作中被一再引用。
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句话的描述其实相当模糊。以《汉书·地理志》所载汉郡资料来说,大郡如颍川、汝南,人口都在二百万以上,至于人口稀少的小郡如武陵,人口还不足二十万。同为汉郡,差距何止10倍?到底中行说口中的“汉之一郡”是多大数目呢?
要解索答案,我们不妨参考一下《汉书·西域传》里边的这段旁证资料。据班固所载,与匈奴同俗的大月氏国:
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万人。
——《汉书·西域传》
从这里看,北方游牧政权治下的人口总数和军队人数比例最高可以达到4:1。而根据《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公元前200年发生在汉高祖刘邦与匈奴冒顿单于之间的白登战役,匈奴总计投入了40万精锐骑兵参战。
照此推论,鼎盛时期的匈奴应该拥有约160万左右的人口——当然,40万参战军队的数字并不一定准确,司马迁在别处提及匈奴军力,总说30余万。因此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记述白登之围,便将这40万改作了30万,要照这样算来,匈奴的人口总数还要更少——的确还抵不过规模最大的几个汉郡。


不但人口基数差距很大,在军队装备和军事素质等方面,汉军相对于匈奴骑兵也有更多优势。太子家令晁错曾在给孝文帝的上疏中仔细分析过汉、匈两军的优势与劣势,他说:
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
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
——《汉书·袁盎晁错传》
相比于汉军,匈奴骑兵的主要优势是善于长途奔袭。匈奴马匹的越野能力超过汉马,骑兵的骑术优于汉骑。因为战士与战马的耐受力都很突出,匈奴武装力量的大范围长距离机动能力要明显强于中原军队。但是游牧骑兵的劣势与他们的优势一样突出:从武器装备来说,匈奴骑兵的弓箭射程和铠甲防护能力都比不了汉军。
至于战术素养,差距就更大。汉军在车、骑两兵种的相互配合下,于平原作战中能够利用密集突击轻易冲散匈奴骑兵的队形。经过严格训练的汉军骑兵可以做到万箭齐发,而匈奴的革甲木盾却难以招架倾泻而下的箭雨。更不必说匈奴专倚骑兵,作战样式单一。一旦离了战马,步行格斗就更不是汉军步兵的对手了。

晁错说,面对匈奴骑兵,汉朝军队在纸面上更有优势。可书生口里的这支优势军队真上了战场,表现却令人沮丧。这其中最刻骨铭心的失败无过于公元前200年的白登之围。在楚霸王项羽跟前儿尚且无所畏惧的刘邦居然落入了冒顿单于设下的包围圈,差一点让土木堡之变的故事提前一千多年上演。高祖皇帝御驾亲征的失利在汉人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刘邦死后,冒顿单于致书刘邦的遗孀吕雉,言语之间颇多轻慢调戏之意。刚毅的吕后勃然大怒,召集诸将,议欲出兵。她的妹夫、上将樊哙第一个站出来,拍着胸脯表态说:“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耿介的季布当场厉声批驳樊哙道:
“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众,困于平城,今哙柰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此言一出,朝堂之内鸦雀无声,出兵之议因此无疾而终。“连高皇帝都败在匈奴人手里,我们又能做得了什么呢?”后来的许多年里,面对匈奴频繁的南侵,只要有人提出武力反击的动议,这个声音就会像魔咒一样响彻在未央宫的大殿上。谈匈色变,畏敌如虎。

汉朝因白登之围而产生的恐慌似乎有些过分了。白登之围真的败得那么惨吗?让我们来还原一下这场战役的经过。据《史记·匈奴列传》所载:
匈奴大攻围马邑,韩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详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
——《史记·匈奴列传》

公元前201年,匈奴大举南侵、被刘邦徙封于马邑的韩王信为图自保,变节投敌,汉朝北疆由此藩篱洞开。匈奴骑兵长驱直入,逼至晋阳。刘邦被迫御驾亲征,发起反击。司马迁接下来的叙述较为笼统,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刘邦甫一北上就轻敌冒进,陷入了重围。
但这并非事实。在《史记》的另一篇《韩信卢绾列传》中,太史公对战役的前期进展有更详细的描述:
七年冬,上自往击,破信军铜鞮,斩其将王喜。信亡走匈奴。其与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立赵苗裔赵利为王,复收信败散兵,而与信及冒顿谋攻汉。匈奴仗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与汉兵战,汉大破之,追至于离石,复破之。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汉令车骑击破匈奴。匈奴常败走,汉乘胜追北。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战役的开始阶段,刘邦的反击其实进行得相当顺利。韩王信一再为刘邦所破,力不能支,只得向新主匈奴请求援手。但即便匈奴左、右贤王率军赴援,与韩信并力御敌,仍然无法抵挡汉军的凌厉攻势。一败晋阳,二败离石,三败楼烦。匈奴节节失利,且战且退。战场形势的发展印证了晁错的论断:平原交锋,游牧骑兵不是汉军车骑的对手。

战役的转折点出现在追亡逐北的路上——刘邦得到情报,冒顿单于就在代郡、上谷间。汉军挟战胜之余威,若能击败冒顿单于,或可一劳永逸地解除匈奴的威胁。这个愿景当然美好,但刘邦毕竟是百战余生,还不至于愚蠢到不打探敌情便贸然出兵。史载:
闻冒顿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晋阳,使人视冒顿,还报曰“可击”。
——《史记·匈奴列传》
决定向冒顿单于开战前,刘邦曾派使者到彼以探虚实。而《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显示,刘邦派往匈奴的使者不是一批或一人,而是前后共计十批。这些人回来之后异口同声地向刘邦禀报说,匈奴人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
在这种情况下,谋士刘敬独持异议,提醒刘邦要小心匈奴的诱敌之计,他的声音就太微弱了,高祖皇帝当然听不进去:
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逾句注,二十余万兵已业行。上怒,骂刘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械系敬广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陷入白登之围,并非汉军实力不济之故,而是由于初次交锋,汉军统帅不了解匈奴“善为诱兵以冒敌”(《史记·匈奴列传》)的战术战法所致。冒顿单于以示弱伪退的办法吸引机动力强的汉军车骑脱离步卒的掩护,独进白登。然后将刘邦率领的这支先头部队和后续的步军主力分割开来,造成局部包围之势。
如果此时冒顿单于决意要吃掉包围圈中的刘邦,包围圈外的几十万步军必然拼死营救皇帝。白登将会因为双方70余万军队的惨烈厮杀而变成一架恐怖的“绞肉机”。
但是,就在决战打响之前,冒顿单于主动撤围,放了刘邦一马。倘若换做项羽,或者其他任何一位中原军队的统帅,恐怕都不会放弃这破敌擒王的天赐良机,冒顿单于为什么要卖刘邦这个人情呢?司马迁在《史记》中给出了两点解释。

其一:
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
——《史记·陈丞相世家》
其二:
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
——《史记·匈奴列传》
坦率地说,我认为这两点解释都不足以令人信服。在此前的战斗当中,王黄、赵利一败涂地。这群散兵游勇来与不来,能对汉、匈两国倾力相搏的大决战产生多大影响?
至于陈平,我不否认他的奇谋密计曾在楚汉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史记》、《汉书》所载的匈奴历史中,还没有哪位阏氏展示过足以左右匈奴单于的强大影响力,就像吕氏、窦氏之于西汉皇帝那样。“其计秘,世莫得闻”,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夫人外交”恐怕是太史公采自故旧耆老之口的传闻吧。
冒顿单于究竟为何撤围?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汉、匈百年战争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汉、匈两军的历次主力决战无一例外都爆发在匈奴境内,在汉朝的国土上则从未有过。换句话说,只有汉军主动出击、深入敌境,才能引发大战。换做匈奴为主动方,大战就打不起来。同利军《汉朝与匈奴战争述评》一文说:
从战争方式上,匈奴大都是“盗边”、“寇边”,而且一遇汉军主力,即撤回本土,从不敢“占领汉地”,或夺取长城以内的汉朝地界。
——《汉朝与匈奴战争述评》
匈奴民族的习性,“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史记·匈奴列传》),唯利是逐,轻进易退。南下盗边,匈奴人的目的端在抢掠财货,攻城略地甚至入主中原,则历代单于从来不做此想。这就好比一个入室行窃的小偷,盗得了值钱的东西就要赶紧撤,不到万不得已,没必要跟主人家搏命。
冒顿单于集兵白登,结结实实地吓了刘邦一跳。逃出生天后,刘邦马上采纳了刘敬的建议,对匈奴和亲纳贡。往后不必鞍马劳顿、亲自南下,汉朝就会自己乖乖儿地送来金银绢帛,冒顿单于的战略威慑已经达成了目的,他干嘛要在白登与刘邦拼个你死我活呢?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同利军《汉朝与匈奴战争述评》;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国军事通史·西汉军事史》。
本文系晋公子原创。已签约维权骑士,对原创版权进行保护,侵权必究!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
欢迎分享转发,您的分享转发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
— THE END —
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图片|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