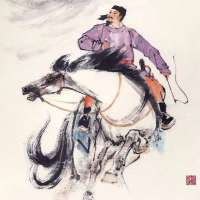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越接近皇帝,即意味着越接近于荣华富贵。但要接近皇帝又谈何容易,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在明清两代,自宫者屡见不鲜,他们之所以如此,即是为了进入皇宫当宦官。
这种现象并不是零星出现,而是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成化十五年二月,两千名自宫者涌向礼部请求入宫;天启元年,更有两万名自宫者在礼部喧哗,要求进宫为宦官。
但一个人要下自宫的决心谈何容易,这对身体和意志无疑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所以古人也说:今使人断一指以易王侯,虽有悍者不愿为之吗,而彼奴则为之。其求太监能忍若此,则其谋富贵何所不为。
最后一句话“则谋富贵何所不为”包含了两个意思:第一,一个人为了谋求富贵,竟然可以自宫;第二,自宫者如果如愿当上了宦官,他在捞钱上也是不择手段的。
太监的恶行,在历史有太多的记载,我也就用不着在此复述。这背后的逻辑是:一个可以连自己都可以阉割的人,在收割别人的时候,当然更不会手软。
太监做事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让皇帝满意,以全天下数万万民众而侍奉一人;太监做事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皇帝的话是毋庸置疑的,以皇帝的对错定义天下人的对错。
皇宫是世界最变态的地方,这里面只有一个男人,和上万的女人,以及上万不男不女的宦官。但整个国家都在这种变态格局下运行。在明代,皇帝最信任的就是太监,无论是军队、财政、还是政治,权力都掌握在太监手里。因为太监上没有子女,没有强大的背景,他们是皇帝最忠实的奴才。甚至明朝灭亡之时,唯一陪在末代皇帝身边的只是一名太监。
如果说生理上的阉割已是如此的恐怖,那精神上的阉割又何尝不是如此!
乾隆六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旗人张广泗在给乾隆上疏的时候上书时自称为“臣”,乾隆对于此称谓极为重视,就下旨说:张广泗所请之事为私事,应该自称奴才,不应该称臣。
原来,在清朝统治之下,旗人在私下场合是可以自称为“奴才”,在处理公事的时候就应当自称为“臣”。而如果是汉族的官员,无论什么场合都只能自称“臣”。也就是说,“奴才”这个称呼是皇帝给旗人的一个特权。这就是所谓的:欲称奴才而不得。
鲁迅在《灯下漫笔》说:
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那些可以自称为“奴才”的旗人,则是自鸣得意,因为他们是皇帝家奴,对于他们来讲,这是一种特权,是一种无上的荣耀。而这种奴化思想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细胞,甚至即便是统治者自身都无法避免。不然,慈禧太后也不会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而这种奴才化的思维,其本质就是人格太监化,进行自我精神阉割,夹着尾巴做人,卑躬屈膝,趋炎附势,为腐败提供了无尽的养分。
他们为何愿意自我精神阉割?这与宦官们的肉体阉割其实一个道理,因为这种阉割可以带来无尽的荣华富贵,可以人上为人,成一人之奴,而奴天下人,这账他们会算。因为他们之所以如此自我精神阉割,为的就是个人的荣华富贵,贪腐也成了必然之举。
明朝最终的灭亡,究其根本原因,不在李自成,不在努尔哈赤,而在自身的腐败。朱元璋算是反贪最狠的人了,动辄杀几万人,但腐败很快就死灰复燃,究其根本,奴化思想不出,等级制度尚存,腐败是去不掉的。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主子,有了主子,就有一批围着主子转的人,他们或阉割了身体,或阉割了精神。而更让人唏嘘的是,这种阉割是自愿的,是前赴后继的。
最后,用鲁迅的话结束: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