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意盎然之际,上海京剧院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了《智取威虎山》的排演工作之中。历经数月的精心筹备,同年8月,这部京剧力作在南京中华剧场首次与观众见面,紧接着,于9月17日,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拉开了正式公演的序幕。此时的《智取威虎山》,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十二场精彩绝伦的戏码:从“乘胜追击”的紧张刺激,到“雪地侦察”的智斗勇谋;从“深山庙堂”的神秘莫测,到“审讯”环节的步步紧逼;从“开山”的壮志凌云,到“试探”中的心理较量;从“整装待发”的蓄势待发,到“滑雪”的轻盈飘逸;再到“百鸡宴”的热闹非凡,每一场都让人目不暇接,拍案叫绝。

次年6月,备受瞩目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盛大开幕,《智取威虎山》作为佼佼者进京参演。剧组对1958年的原版进行了从剧本到演出的全面而细致的修改与打磨,力求精益求精。
岁月流转,1967年5月23日晚,上海京剧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上演了《智取威虎山》,领导亲临现场观看,给予了高度评价。5月3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的社论,将《智取威虎山》列为了八部“革命样板戏”之首,并同时刊载了该剧的剧本,其地位之显赫,可见一斑。两年后,即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智取威虎山》作为“献礼之作”,在大会期间为与会代表们献上了精彩的演出。同年10月,经过无数次的锤炼与打磨,这部“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每一处细节都经过反复推敲与雕琢的《智取威虎山》,再次在首都舞台上绽放出了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

至此,可以说,《智取威虎山》已经完成了它“脱胎换骨”的华丽蜕变,文艺激进派们创造“无产阶级文艺”的理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剧组不遗余力地刻画杨子荣的内心世界,展现他是如何用思想武装自己,以“宏伟理想”、“阶级爱和阶级恨”、“大智大勇”等“光辉品质”来深深感染和教育每一位观众。在“深山问苦”等场景中,杨子荣对受苦人民的深情厚谊令人动容;
而他以“机智和犀利的口才,迷惑了老奸巨猾的座山雕”,并以“把小炉匠置于死地”的果敢行动,展现了对敌斗争的智勇双全,这绝非单纯的“大智大勇”所能概括。20世纪60年代初,人们对杨子荣的评价就充满了多元与深意,有人赞赏他“临难不畏、临危不惧”的英勇与智慧,也有人对他“随机应变”和“周旋能力”赞不绝口,这些评价背后所蕴含的道德评判,既丰富又复杂。
《智取威虎山》故事内容的改编与主人公的更换,既是京剧艺术形式本身客观要求的体现,也是舞台空间与时间限制下的必然选择。

这种发挥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物语言的精炼与升华。唱段是戏曲表演艺术的核心要素之一,戏曲改编在保留原著精髓的基础上,加强了抒情性与文学性语言的表达,使得人物唱段更加动人心弦。例如,那首经典唱段“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便是对英雄豪情壮志的生动诠释。二是对剧情的巧妙压缩与整合。
受限于戏曲演出的时间和空间,戏曲创作者巧妙地删去了原文中冗长的支线情节,将文本重新整合与再塑造,使得剧情更加紧凑有力,更符合戏曲艺术的呈现规律。对于戏曲文本的观看者而言,《智取威虎山》的观赏重点已经由初始文本的文字内容转向了戏曲文本的舞台表演,包括演员精湛的唱念做打、生动的身段表情;以及舞台场景的巧妙布置、灯光的巧妙运用与音效的精准把控等,共同构成了一场视听盛宴。
样板戏中的角色设置,可以说精简而富有深意。这些角色不仅类型化鲜明,更蕴含着深刻的原型意义。其他角色也都有其各自的原型对应:共产党员或解放军,尤其是样板戏中那些“满腔热情、千方百计”的第一号人物,正是鲍特金笔下“英雄”的现实写照;而“人”的概念被缩小,特指“普通人”,群众便是这一概念的具象化;至于那些需要被打倒的“人”,则沉入地狱,降格为“魔鬼”,敌人和叛徒便是这“魔鬼”的现实对应。

在样板戏中,“英雄”是不在场的“神”的人间代言人,他们因领受了神的思想与力量,而拥有了拯救人间的非凡能力。《智取威虎山》中的英雄杨子荣,其多个唱段便深刻展现了“神”与“英雄”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多萝西娅·克鲁克在探讨悲剧英雄的理想模式时曾指出,悲剧中的理想人物通常具备两种普遍且固定的主要特征——勇敢和高尚(心灵的伟大)。
勇敢是高尚的一个表现,而高尚则主要由勇敢来定义。她进一步引用柏拉图的观点,将勇敢视为灵魂某个部分的外在美德,称之为“精神的”因素,或简称为“精神”。也就是说,勇敢和高尚是两个相互定义、相辅相成的特征,它们共同凸显了“精神”的核心地位。显然,只有当英雄的“精神”与“神”的精神一脉相承时,英雄才可能拥有“神”所赋予的力量和拯救的合法性。

看完智取威虎山,我们在看看《红色娘子军》。
“红色娘子军”这一传奇故事,最初在电影银幕上绽放光芒时,其核心主题便聚焦于吴琼花的蜕变与成长。编剧梁信心中有着坚定的创作目标,他要讲述的,是琼花如何在党的教育和革命斗争的洗礼下,从一个懵懂无知、满怀个人复仇之火的女奴,逐步成长为一名拥有无产阶级觉悟的革命战士,以及她最终的人生归宿。这一主旨,导演谢晋不仅深刻理解,更在影片中巧妙呈现,从开场那个勇敢而热辣的琼花,到结尾那个坚毅而成熟的革命者,她的每一次转变都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

随后,这一感人至深的故事又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被搬上了芭蕾舞台。尽管舞剧与电影的艺术表现手法截然不同,但编导们在改编过程中,始终坚守着原作的主题精髓,对情节进行了精心的集中与删节,却未曾动摇其根本。
舞剧的编导之一李承祥在回忆《红色娘子军》的创编历程时,曾感慨万分:“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生动展现琼花的成长历程,让她从一个满腔个人复仇思想的女奴,逐步蜕变为一名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革命战士。”他坦言,这一主题的深化之所以成为难题,一方面是因为以往的芭蕾舞剧鲜少涉足人物的发展变化,导致编剧们缺乏可借鉴的先例;但更为关键的是,“琼花的成长”如同贯穿全剧的灵魂,唯有将其刻画得淋漓尽致,方能成就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舞剧佳作。李承祥的这一见解,与原版电影的编剧和导演不谋而合,共同铸就了这部作品的不朽传奇。

当然,舞剧《红色娘子军》并未忽视“斗争”这一核心思想。相反,在编导过程中,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李承祥在谈及创作体会时提到,创作团队在领导同志的悉心指导下,不仅在思想上得到了升华,更在技巧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他坦言,在剧本的初创阶段,团队曾过于聚焦于琼花个人的家仇和娘子军的独立行动,而忽视了更为广阔的阶级斗争背景。幸而,在剧本初稿的讨论中,领导及时指出了这一问题,并明确指示:不应孤立地描绘琼花与南霸天的个人恩怨,而应将其置于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之中,凸显阶级的压迫与反抗;同时,娘子军也不应被视作一支孤军奋战的队伍,而应将其与海南的整体斗争形势和琼崖独立师紧密相连,从而在剧情安排上加强男红军和人民武装的篇幅,使整部舞剧更加饱满、立体。
在《红色娘子军》芭蕾舞样板戏中,红色标语作为重要的视觉元素,常以横幅的形式出现在舞台之上。特别是在批准吴清华加入娘子军的那一场控诉舞蹈中,战士们与群众的情绪达到了沸点,舞台上后排的群众高举着“打土豪分田地”、“活捉南霸天”的横幅标语,这些简洁而有力的标语与舞剧中激昂的民众情绪交相辉映,既充分表达了群众对地主恶霸的深恶痛绝,也展现了战士们誓要打倒南霸天的坚定决心。

在舞剧的音乐创作中,“吴清华主题”成为了贯穿全剧的重要线索。第五曲“清华反抗”中,紧随“南霸天主题”之后,便响起了那充满愤怒与仇恨的“吴清华主题”,敌我双方的二元对立与不可调和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一番激烈的棍棒拳脚对打之后,吴清华伴随着那撕心裂肺的旋律倒下了,昏死过去,这一幕深深震撼了每一位观众的心。
而在接下来的第六曲“清华独舞”中,“吴清华主题”又在独奏小提琴的悠扬旋律中响起,细腻地描绘了吴清华“遍体伤痕钻心痛,腹中饥饿身上寒”的孤独与无助。值得一提的是,这段音乐中还巧妙融入了“首演版”序曲中的《鞭痕满身仇难忘》的音调,使得其悲剧色彩更加浓厚。第七曲“洪常青指路”中,随着《指路三人舞》的结束,洪常青掏出两枚银毫子递给吴清华,这一举动让从小饱受奴役的吴清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与关怀,她激动得热泪盈眶。此时,独奏大提琴缓缓奏出“吴清华主题”,那是一个充满感激之情的慢板旋律,吴清华的反抗性格在这一刻得到了升华,取而代之的是对党和人民的无限感激。
在第一场中,“吴清华主题”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与深化,成功塑造了一个具有强烈反抗精神且爱憎分明的吴清华形象。而在第二场“清华控诉,参加红军”中,“吴清华主题”则仅在第五曲“清华参军”中短暂出现。当《清华来到红区》的旋律响起时,“吴清华主题”再次响起,标志着这个人物的华丽登场。而在《清华诉苦》一段中,管弦乐队与独奏大提琴的交替演奏,将吴清华内心的阶级仇与苦难史展现得淋漓尽致。

进入第三场“里应外合,夜袭匪巢”,“吴清华主题”更是在多个段落中频繁出现。在《清华与战友侦察的舞蹈》中,单簧管独奏出的“吴清华主题”刻画出了一个机敏、警觉的吴清华形象;而在《清华、战友双人舞》中,该主题则展现了一个疾恶如仇、“怒火满腔”的吴清华。
当吴清华在《清华开枪打伤南贼》一段中再次遇到仇人南霸天时,“抑止不住的仇恨”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此时乐队以“全奏”的方式奏响“吴清华主题”,将一个勇敢反抗的吴清华形象再次呈现在观众面前。而在第八曲“常青号召,开仓分粮”的结束部分以及第九曲“常青关切的询问情况”中,“吴清华主题”的再次响起,则巧妙地表现了连长卸下吴清华的枪、党代表关心此事的温馨情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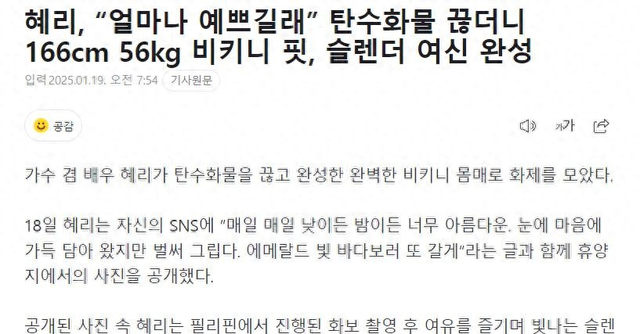

样板戏反应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经典中的经典,精神上的享受!
模式化制作,正字的应景之作,经典个屁。当然,部分唱段比较出彩,这是事实
为何老是拿历史说事。为何不切实为解决民生问题提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