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按钮,方便以后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新的文章,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动力~

《——【·前言·】——》
裴老四说这话的时候,脸没红,心也不跳,他盯着瞄准镜,像在林子里蹲守一头野猪。
那年他五十三岁,枪口下不是野兽,是活人。
五十三岁,还能杀敌吗?
裴天来是滦南人,河北滦南,不出名,地势平,老百姓都靠种地为生,可有一个行当,只有极少数人干得来,裴老四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从小练的,跟父亲上山,背上干粮,扛着老土枪,一待就是三天三夜,山里冷,狼多,枪走火,就可能永远回不来。

打猎不是靠胆子,是靠眼力和耐心,十岁时他就能在五十米外一枪打掉松鼠脑袋。
十三岁,父亲让他独自守林,一夜没睡,眼睛红着,但野兔一只都没放走。
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只叫他“老四”,因为他家兄弟四个,他最沉默。
后来大家都叫他“裴老四”,这个名字,从山林传到了战场,从猎人变成“死神”。
到了三十岁,裴老四已是滦南有名的猎人,一杆李恩菲尔德步枪,从黑市买来,价值能抵三亩地。
那是英国造的好枪,退壳顺,准头稳,他摸着枪,就像摸着老伴的手。

可打猎渐渐赚不到钱,大户请他护院、护送粮车,土匪多,枪响过三次,三次都死人,他从不多说一句话,枪响,人倒,没废话。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河北,首当其冲,日军南下,烧、杀、抢,样样不落。
裴老四亲眼看到一个八岁孩子,被推到沟里,刺刀直接穿胸,连哭都没来得及。
他没说什么,回家后,把老枪擦了三遍,第二天,他去了冀东军区。
五十三岁,照样打鬼子
那年他五十三岁。身高一米六八,不高;体重不到一百斤,不壮。
可冀东军区副参谋长李健之看了他三枪之后,亲口说:“这样的人,不上战场,是浪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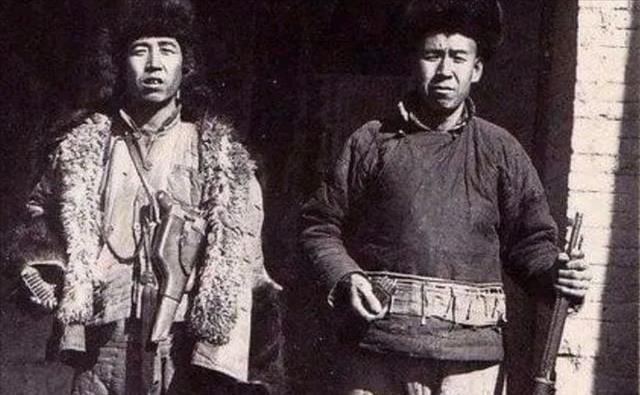
八路军把他编进特科,任务只有一个:杀敌。
他不跑远程,他不打正面,他只伏击,每次出发,他只带两样东西:李恩菲尔德步枪,一头小毛驴。
毛驴背上不载弹药,只载干粮和毯子。他会趴在冷地上等三天,只为等一个日军军官露头。
1943年7月,冀东军区发动对乐亭大庄河据点的围攻,鬼子火力猛,有轻机枪,点射速度快,我军攻了三次都没破。
“你能干掉那个机枪手吗?”有人问他。
裴老四没回话,爬走了,带着枪,带着一袋炒面,他在灌木中趴了整整十个小时。

下午三点,太阳毒,鬼子以为安全,机枪手出来透气,裴老四慢慢举枪瞄准,他不是瞄头,是瞄胸口,因为胸口更大。
砰,第一枪,鬼子机枪手倒下,没等反应,第二枪把一旁副手爆头。
第三枪打空,他没慌,翻滚,滚进一条沟,鬼子发疯地扫射,他不还击,只等机会。
当夜,我军突袭成功,日军据点陷落,缴获大量物资。

有人清点尸体,数了数,周边树林里有十几具日军尸体,全是单发击杀,子弹打得极准,胸口、眉心,几乎无误。
“是老四干的。”李健之只说了一句。
此战后,他的名字开始在冀东传开,不是靠宣传,是靠“鬼子的尸体”。
他只杀关键人物,每次出战前,他都要知道目标是谁、穿什么衣服、站哪边,他杀的是“指挥”,不是“随便的兵”。

战士们开始学他,可没人能像他那样,趴一整天不动。
蚊子咬脸,他也不抬头,腿麻,咬破嘴唇,有人问他疼不疼,他说:“打猎时,腿上生过蛆。”
伏击专家,不靠运气
裴老四不打无准备之仗,他出发前,一定先摸地形、看风向、记敌哨兵换岗时间。
不和敌人拼运气,更不拼胆子,他拼的是信息、时间和一颗稳得像石头的心。
1944年初春,冀东山地仍被日军分割,他们强占村庄,修碉堡、拉铁丝网,把冀东变成一个个“孤岛”。

八路军缺枪、缺炮,打据点只能靠人命填。
一天夜里,冀东军区接到线报:滦县以东一个新修据点刚完工不久,守军松懈,还有一个小型联络站藏在据点东南方向,设有电话线。
指挥部打算偷袭这个联络站,切断敌方通讯,给大部队争取转移时间,任务危险,不适合正面打。
最后点了名字:“派裴老四,带三人,干这票。”
他没说话,点头,背起枪,他不习惯带人,但任务重,必须带通讯员和两个搬电台的兵。

他第一步,是不让新兵添乱,他把两人安置在五里外的土窑洞,只身进村踩点,花了整整两天。
他躲进牛棚,扒草堆,从牛粪堆里爬出来,他记住了所有哨兵换岗时间、武器种类和碉堡死角,还画了个草图,没有纸,就在鞋底上刻。
第三天晚上,他动手了。
第一枪,他不打人,打狗。
哨兵旁边一条狼狗,是日军养的,狗太灵,稍微一响就狂叫,夜里狗叫,鬼子就乱开枪,根本接近不了。
他趴在一堵断墙后,瞄了一个多小时,狗动了,他瞄狗脖,扣扳机,狗扑倒,没声,鬼子没反应,第二枪已经送进哨兵下颌。
他示意两名战士靠近,进村后,他直接贴近联络站东墙,用匕首割断一根裸露在外的电话线。

然后翻入院中,三人潜入操作室,直接掀开电台帘布,拔线,拆机。
一名日军军官刚好回来,裴老四反应比他快,没有开枪,直接上去,一手捂嘴,一手持刀,刀插咽喉,没出声。
干完后,他照旧带人撤退,走到半路,埋伏在南边山坳里,他预判得没错,敌人天亮必然派人巡查线路。
不到凌晨四点,一辆军用摩托开进沟里,两名日兵下来检查,正好钻入枪口。
他举枪,一枪两个,打完收枪就走,没留一秒。

第二天,敌军惊觉,电台没信号,电话也断,送信人死在半路,指挥层忙乱三天,主力部队已经全部撤出。
军区发通报嘉奖,他没出席,他说:“别浪费纸。纸能擦枪。”
终局之战
1945年,春天来得早,日军却疯得快。
冀东地区残余日军开始疯狂“清剿”,村庄一个接一个烧,老百姓死伤惨重。
那年,裴老四已经55岁,眼睛花了,腿也有点拐,但他没退。

他接下任务:深入乐亭县外围,刺杀敌指挥官,掩护部队转移。
3月,他带着毛驴和枪,悄悄摸到某村外围,村子里住着一个伪军头目,常与日军往来,屠村不止一次。
裴老四在一户烧炕的老乡家藏了三天,炕洞里,他一边吃炒面,一边擦枪,每天黄昏,他在屋顶观察,找目标。
第五天下午,那人出来,骑马,戴皮帽,带五六个伪军,身后有一名日本军官。
枪口稳稳架在窗框上,他吸一口气,屏了五秒,那一枪,从窗缝穿出,打穿了马脖,子弹擦破军官下巴。

对方没死,他不慌,撂下枪,翻窗出去,掏出匕首,贴着土墙趴行。
战斗开始,枪声、日语喊叫、小孩哭声,全混在一起,裴老四看准时机,从墙后窜出,刀尖直插进军官腰眼。
那天他杀了三人,但腿上中了一枪,他咬牙爬回土屋,靠着驴睡了一夜。
八路军来接他时,他已经烧得胡话连篇。
他被送往乐亭一户老中医家中养伤,可日军很快就追到了,他没能走动,被人出卖,当场抓走。
十天后,传来消息:“裴老四被日军枪杀,连尸首都没找回。”
冀东上下,所有曾和他打过仗的人,全沉默了好几天,冀东军区为他立碑,碑上刻着:“神枪手裴天来,为国捐躯。”

他没读过书,没喊过口号,没写过请战书,可他杀敌最多,也死得最狠。
他常说:“打鬼子比打猎容易,猎物要藏,鬼子光走,直挺挺地往枪口撞。”
这句话,说得轻,可每一枪,都要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