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2年正月,前秦荆州刺史都贵派遣的部队在竟陵郡(今湖北钟祥)遭遇惨败的消息传到了长安。然而,天王苻坚对此无暇顾及,因为他正忙于处理一起内部谋反事件。
这次谋反涉及三人:苻阳、王皮和周虓。

苻阳时任大司农、东海公,是苻坚庶兄苻法之子。苻法早在357年苻坚即位时便被苟太后诬陷杀害。
王皮为员外散骑侍郎,乃名相王猛次子,但其才德平平,曾被王猛评价为不堪大用。
周虓则是尚书郎,原为东晋梓潼郡太守,于373年十一月被俘,其间虽曾有一次谋反记录,但被赦免后仍留在前秦任职。
三人密谋造反,事情败露后被捕,并交由廷尉审理。苻坚亲自审问他们为何要谋反。
苻阳首先回答:“《礼记》云:‘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父王无罪却被杀害,我理应为父报仇!春秋时期,齐襄公尚且能报九代之仇,而我只是想为父亲讨回公道!”
听完这话,苻坚不禁泪流满面,说道:“卿父王之死,责任并不在我,卿难道不知吗?”
苻阳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接着,苻坚转向王皮。王皮答道:“我的父亲官至丞相,功勋卓著,而我却一直贫贱度日。我之所以谋反,是为了追求富贵。”
苻坚闻言叹息道:“令尊临终前曾托付于我,只给你十头牛作为治田之资,劝我不要让你担任官职。真是知子莫若父啊,现在看来,令尊何等英明!”
最后,苻坚看向周虓。周虓坚定地答道:“我家世代受晋朝恩惠,生为晋臣,死为晋鬼,你还有什么可问的?”
由于周虓此前已多次谋反,左右大臣纷纷劝苻坚将其处死。但苻坚却不愿杀他,说道:“周虓乃刚烈之人,性格如此,他本就不怕死,杀了他反倒成全了他的美名。”
最终,苻坚决定赦免三人,但将他们分别流放。苻阳被发配至凉州高昌郡(今新疆吐鲁番),王皮与周虓则被流放到朔方(河套地区)以北。
后来,周虓在朔方去世。而苻阳因身强力壮、勇力过人,又被进一步流放到西域鄯善王国(今新疆若羌)。一年后,前秦发生大乱,苻阳企图劫持鄯善王国宰相返回长安,结果被鄯善王诛杀,这便是后话了。

针对苻阳等人谋反事件,苻坚的兄弟阳平公苻融感到深深自责。他上书苻坚,请求辞去官职。苻融认为自己身为宗正,却未能阻止苻阳等人的叛乱行为,因此请求被贬回封地以接受进一步惩罚。然而,苻坚并未批准苻融的辞职请求,反而打算给他加授更高的官职。
就在382年四月,苻坚刚刚处理完苻阳、王皮、周虓等人的谋反案件后,他颁布诏书任命苻融为司徒、征南大将军,并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
与此同时,苻坚还任命扶风郡(今陕西省兴平市)太守王永为幽州刺史,任命苻朗为使持节、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值得一提的是,王永是王猛的长子,也是王皮的兄长。
与王皮不同,王永以清廉好学著称,因此受到苻坚的重用。在担任太守期间,王永不仅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而且政绩斐然,这使得苻坚决定提拔他为刺史。

苻坚对苻朗和王永的任命,实际上是为了调回各地的将领,为即将发动的攻打东晋荆州和扬州的战役做准备。此外,苻坚还将谏议大夫裴元略调至梁州,担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并命令裴元略秘密建造舟船,为即将到来的对东晋的战争做好充分准备。这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和军事部署,表明苻坚再次燃起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
在苻坚秘密筹备进攻东晋的同时,前秦幽州地区爆发了严重的蝗灾。这一情况可能是由新上任的王永上报,且确有其事。
根据史书记载,这场蝗灾仅限于幽州,影响范围达千里之广,但并未波及其他州郡。
然而,从后续发展来看,其他州郡可能因畏惧权威而未如实上报问题,这反映出前秦官僚体系中已逐渐滋生出欺瞒虚报的不良风气。

苻坚是在公元382年五月得知幽州蝗灾的消息,正值王永刚刚到任不久。接到报告后,苻坚立即派遣散骑常侍刘兰组织幽、并、冀、青四州百姓共同扑灭蝗虫。由此可以看出,蝗灾的实际影响范围可能超出了幽州一地。
然而,史书又记载当年秋天前秦全国粮食大丰收,优质农田每亩产量高达七十石,普通农田也有三十石。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蝗虫似乎只停留在幽州,并未扩散至其他地区,而且它们竟然不吃麻豆作物,导致幽州的某些农田甚至达到每亩百石的惊人产量。
这些相互矛盾的记录表明,要么是史书存在错误,要么就是前秦地方官员在汇报时弄虚作假。通过这些不一致的描述可以看出,当时前秦各级官员已经开始出现腐败现象,为了迎合上级而不惜篡改数据。这种行为或许正是苻坚未曾察觉的隐患之一。

历史上记载,苻坚曾经坚决反对谶纬之说,但后来却突然对它深信不疑。就在这个时候,新平郡有人献上了一件玉器,这让苻坚想起了多年前被他处死的新平人王雕。
当时苻坚刚刚即位,王雕为苻坚解读图谶,苻坚听后非常高兴,任命王雕为太史令。
王雕曾对苻坚说道:“在谶言中有这样几句话:‘古月之末乱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这三句正好对应陛下和三位祖先。此外,还有这样的预言:‘当有草付臣又土,灭东燕、破白虏,氐在中、华在表。’这说明陛下将会消灭燕国,平定关东六州。同时,陛下还将把汧、陇地区的氐族迁到京师,而将关中的豪强大户安置到边远地区,以应验谶言。”
当时苻坚犹豫不决,于是向王猛请教。
王猛强烈反对相信谶纬之说,并且认为王雕是一个旁门左道之人,请求苻坚将其处死。苻坚当时十分信任王猛,于是下令处死王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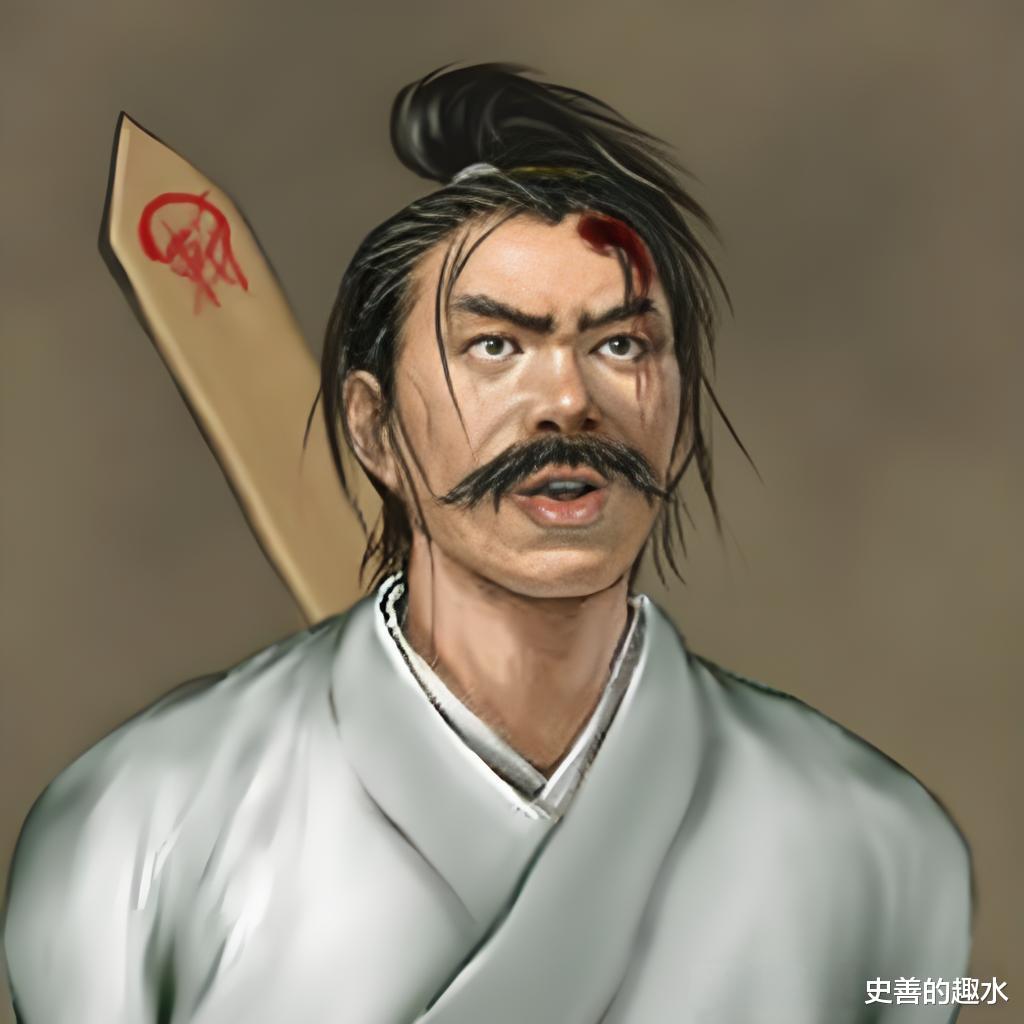
王雕临刑前,请行刑者转告苻坚:“我在石赵时期就跟从刘湛学习,精通图谶之学。刘湛曾对我说过:‘新平是古代颛顼之地,将来会出土一件帝王的宝器,名字叫做延寿宝鼎。颛顼还预言,他的子孙中如果有‘草付臣又土’的,就会应验此预言。’我恳请陛下记住,当平定六州之后,这件宝物一定会出现。”
如今王雕已死去二十多年,前燕已被灭亡,六州也已平定,这时新平郡果然有人发现了一件宝器。
苻坚目睹了这件玉器,其上刻有篆文,内容依次为:一曰天王,二曰王后,三曰三公,四曰诸侯,五曰伯子男,六曰卿大夫,七曰元士。再往下则是历代帝王名臣的名录,从天子到王后,内外秩序井然,与天文相对应。
苻坚看过之后,想起王雕曾经的预言果然应验,于是下诏追赠王雕为光禄大夫。从苻坚开始相信这种谶言的现象可以看出,他逐渐变得喜欢听奉承之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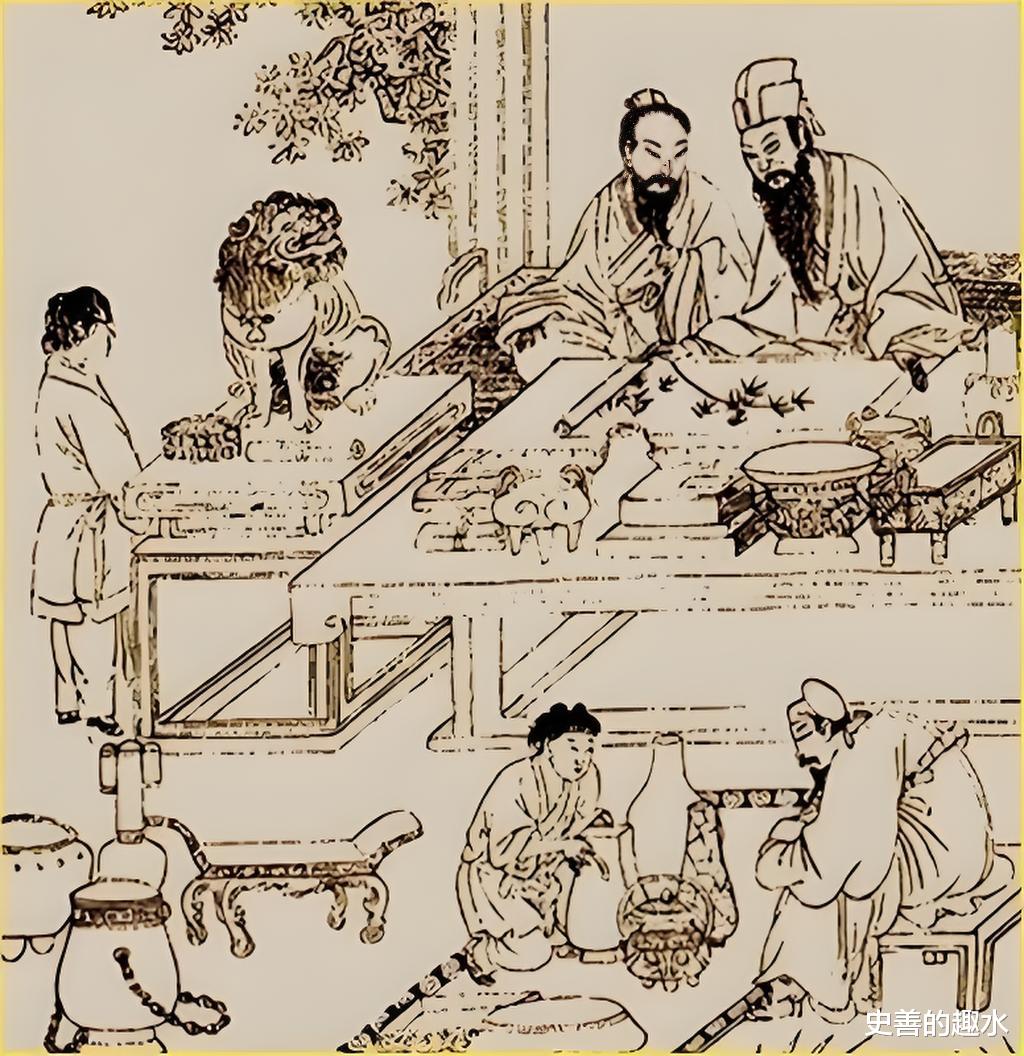
实际上,这些所谓的谶言大多是在事后被人附会而来的。那些被挖掘出来的带有文字的物件,往往是一些人提前精心准备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讨好苻坚。
这些人敢于用虚假的言语来取悦苻坚,正是因为苻坚喜欢听好话,愿意被迎合。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苻坚竟然对此深信不疑。
要知道,此时距离王猛去世仅仅七年。在王猛生前,哪容得下各级官员欺骗或虚报?在王猛的时代,那些解读谶言的人恐怕连性命都难以保全。王猛建立起来的法治国家,到了这个时候已经被悄然改变了。
九月,西域车师前部王弥田与鄯善王休密驮抵达长安,朝觐前秦天王苻坚。
苻坚赐予二人朝服,并于西堂接见。

弥田与休密驮目睹前秦皇宫的宏伟壮丽,以及仪仗卫士的威严整齐,深感敬畏,当即表示愿意每年进贡。苻坚仁慈宽厚,考虑到西域路途遥远,决定改为三年一贡,九年一朝。
觐见结束后,二王向苻坚提出,西域仍有部分国家尚未臣服于前秦,请求派遣军队进行征讨,并愿为向导。同时,他们还建议在西域设立都护府,仿效两汉时期的治理模式,加强对西域的管辖。苻坚听后十分高兴,当即决定出兵征讨尚未归附的西域诸国。
苻坚任命骁骑将军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与凌江将军姜飞、轻车将军彭晃、将军杜进、康盛等人率领十万步兵、五千骑兵共同讨伐西域。
然而,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苻融坚决反对此次出兵。他劝谏道:“西域荒芜偏远,即便得到其民众也无法驱使,占据其土地也无法利用。当年汉武帝征讨西域,得不偿失。如今陛下兴师动众,远征万里之外,恐怕会重蹈汉武帝的覆辙,实在令人痛惜。”

苻坚却不以为然,说道:“昔日两汉虽未能完全制服匈奴,但仍能出兵西域。如今匈奴已平定,出兵西域如同摧枯拉朽般容易。虽然兵马需长途跋涉,但只需传檄即可平定。出师西域,可让教化覆盖昆仑山,流芳百世,岂非美事?”
尽管朝臣多次劝阻,苻坚始终未采纳意见。最终,他下令吕光准备三个月,计划于次年正月从长安出发,率大军远征西域。
苻坚当时面临着东晋的威胁和西域的征伐任务,尽管国内还在与蝗灾作斗争。
就在苻坚专注于准备攻打东晋,尚未发布全面进攻命令之际,东晋车骑大将军桓冲却派遣扬威将军朱绰对前秦荆州的襄阳发动袭击。
朱绰率领部队北上进攻襄阳,前秦荆州刺史都贵未能及时阻挡,导致朱绰成功渡过汉水,并在汉水以北地区纵火焚烧村庄。朱绰还掳掠了六百多户百姓后撤退,同时破坏了汉水以北的屯田区。

当桓冲派兵袭击襄阳的消息传到长安时,苻坚自然十分愤怒。
苻坚也深知,仅仅九个月前,都贵就已经损失了两名将领和两万士兵。因此,苻坚决定将灭东晋的计划提交到朝会上进行商议。
苻坚筹谋讨伐东晋公元382年十月,苻坚在太极殿召集众臣商议攻打东晋的计划。
苻坚对群臣说道:“朕自即位以来,将近三十年。如今天下四方基本平定,唯有东南一隅尚未归化。朕粗略统计国内兵马,可集结九十七万之众。朕打算亲自率领大军讨伐东晋,诸位爱卿以为如何?”
秘书监朱肜立刻出列称赞道:
“陛下顺应天时,恭行天罚,一声令下便可使五岳崩塌、江海断流。若能出动百万雄师,必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东晋君主自当献上玉玺,跪拜于军前请降。倘若他执迷不悟,必将逃亡江湖,届时只需派遣猛将追击,即可一统江南。中原南渡之人也可重返故土。到那时,陛下可登临泰山告成封禅,成就千古未有的盛事。”
苻坚听后十分激动,忙说:“这正是朕的心愿啊!”

然而,也有人反对此时攻伐东晋。尚书左仆射权翼劝谏道:“臣认为不可伐晋。当年商纣王无道,天下离心,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前来会盟,但周武王仍以‘彼有人焉’为由,选择班师回朝。直到微子、箕子、比干三位贤臣被杀,武王才挥师牧野。如今东晋虽然国力衰退,但并未听说有失德之处,君臣和睦,上下齐心。谢安、桓冲皆是江南俊才,可谓晋国有可用之人。臣闻军队取胜在于团结一心,如今东晋内部和谐,实非我军可轻易图谋。”
苻坚一向重视权翼的意见,此刻听到权翼也反对攻伐东晋,心情顿时低落,沉默许久,大殿内一片寂静,无人再敢言语。
良久之后,苻坚缓缓开口说道:“请各位爱卿畅所欲言,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前秦天王苻坚执意南征东晋,朝堂之上围绕是否出兵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太子左卫率石越以深邃的智慧和谨慎的态度表达了反对意见。

石越奏道:
"晋室凭借长江天险偏安江南,不尊奉陛下号令。然而陛下御驾亲征问罪吴越,确实是天下人神所望。但今年镇星正照斗牛,福气在吴地。天象昭示不可违逆。况且司马睿当年身为藩王却能获得夷夏拥戴,至今恩泽犹存。其孙司马曜(字昌明)据有江东,国内无昏庸奸佞之臣。臣以为当以德服晋,不宜用兵。孔子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恳请陛下休养生息,静待良机。"
面对石越引经据典的劝谏,苻坚却毫不动摇,他反驳道:
"朕听说武王伐纣时也不合天象。天道幽远难测。昔日夫差威震中原却被勾践覆灭;孙权割据江东,到孙皓时不过三代便亡国。纵有长江天险亦难保全,最终君臣皆为俘虏。如今我军百万,若将马鞭投入长江,足以断流。"

石越听后继续进言:
"臣闻商纣无道,故天下视之如寇仇。夫差荒淫,孙皓暴虐,致使众叛亲离,所以败亡。今晋虽无德,但亦未见大罪。愿陛下励精图治,积蓄力量以待天时。"
群臣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苻坚最后断然说道:"此乃众人筑舍于道旁,议论纷纷难以决断。朕将自行定夺!"这段对话充分展现了苻坚一意孤行的性格,也为后来的淝水之战埋下了伏笔。
苻坚虽然表现出希望独自决断大事的姿态,但实际上并未如此。他先让众臣退下,仅留下自己的兄弟苻融来商讨攻伐东晋之事。
苻坚对苻融说道:“自古以来,成大事者往往只依靠一两个人制定策略。众人议论纷纷,只会让人困惑迷茫。我打算和你一起作出最终决定。”
然而,在太极殿上一直保持沉默的苻融,却明确表示反对攻打东晋,这令苻坚始料未及。

苻融提出,当前有三个理由不宜讨伐东晋:
第一,今年镇星位于斗牛之间,这是吴越之地的祥瑞之象,预示着不应征伐;
第二,东晋君主贤明,朝中大臣齐心协力,国力稳固,不可轻易进攻;
第三,我国连年征战,将士疲惫不堪,已有惧敌之心,此时不宜再发动战争。
苻融还补充道:“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可伐晋,这才是最好的策略,恳请陛下采纳。”
苻坚听后大感意外,脸色骤变,语气严肃地说道:
“如果你继续这样固执己见,那天下大事我还能与谁商议?如今秦国兵强马壮,兵力达百万,物资储备如山。我虽非十全十美的君主,但也绝非昏庸之人。凭借多次胜利积累的余威,去攻打那个濒临灭亡的贼寇,怎么会不成功?我不想把东晋这个隐患留给子孙后代,让它成为国家的祸患。”

苻融见苻坚动怒,不禁痛哭流涕地劝谏道:
“攻打东晋实属不明智之举,道理十分清楚。即便倾全国之力南征,也必将徒劳无功。我所忧虑的远不止于此。陛下对鲜卑、羌、羯等族恩宠有加,让他们遍布京城,而将自己的同族人迁往四方。一旦我们倾尽全力南征,若发生意外,又该如何向祖宗交代?
再说太子苻宏只率领几万羸弱之兵留守京都,而那些鲜卑、羌、羯之人犹如密林般环绕四周,他们本就是我们的死敌。因此,我不仅担心南征会毫无成果,更担忧局势无法完全掌控。我的见识浅陋,建议或许不足为外人道也。但王猛乃是一代奇才,陛下常将他比作孔明,请不要忘记他临终前的忠告。”
尽管苻融苦口婆心地劝谏,苻坚仍然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公元383年的十一月,苻坚前往东苑游赏,特意邀请道安和尚同乘一辇。
道安原本在东晋荆州襄阳弘扬佛法,直到379年前秦攻下襄阳后才来到长安,深受苻坚敬仰。

当时,尚书左仆射权翼目睹天王与和尚共车的场景,内心颇为不安,急忙向苻坚进言:“臣闻天子出行,应由侍中随行,清道而行,举止有度。然而夏桀、商纣等亡国之君,却因一时情感用事而违背人伦,其丑行被记录于史书,遗臭万年。道安不过是一介卑微之士,实在不应亵渎圣驾。”
苻坚一向对权翼极为敬重,以往他的建议总能得到采纳。但这次听到权翼如此贬低道安,苻坚面色明显不悦。
苻坚回应权翼道
“安公(道安)的学识境界精妙高远,德行广受世人尊敬。朕即便拥有天下,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并非安公因与朕同车而荣耀,而是朕因安公的存在而增光添彩。”说完,苻坚还命令权翼亲自扶道安上车。
苻坚与道安同辇出游时,仍不忘提及南征之事。

苻坚兴致勃勃地对道安说道:“朕打算与您一同南下游历吴越之地,整顿六军进行巡视,前往疑岭拜谒虞舜之陵,在会稽瞻仰大禹之穴,泛舟长江,亲临沧海,岂不快哉!”
道安虽然深受苻坚敬重,但他依然保持独立的见解。此前,许多大臣都认为道安是苻坚最信任的人,因此纷纷劝他向苻坚进言,希望他能为天下苍生考虑,阻止苻坚的南征计划。
道安也认为南征并非明智之举。在听完苻坚的理由后,他说道:
“陛下顺应天命治理天下,居于中原而掌控四方。您平时悠然自得,顺应天时,身体安康。出行时有銮铃清道,静止时心境无为,以拱手之姿治国理政,与尧舜这样的圣君齐名。如今为何要让自己奔波劳累,口干舌燥地谋划战略?为何要风餐露宿,饱受风尘之苦呢?更何况东南一隅,地势低洼且多疫病,当年虞舜巡游至此却未能返回,大禹也因东南之地而未归家。难道陛下要让上至圣驾、下至百姓都陷入困顿吗?《诗经》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如果文德足以感化远方,自然可以不动干戈而使百越臣服。”

苻坚听后回答道:
“朕之所以决定南征,并非因为国土不够广阔或人口不足,而是为了统一天下,造福苍生。朕作为天下黎民的君主,理应为百姓消除烦恼和混乱,怎能畏惧劳苦?
既然朕顺应天时,就应当替天行罚。昔日高辛曾有熊泉之战,唐尧也有丹水之师,这些事迹都记录在典籍之中,为后世所效仿。若真如您所说,帝王岂不是连巡视四方的记载都不该存在了吗?再者,此次南征实为正义之举,旨在帮助那些南渡士族的后人重返故土,恢复家园。朕的目的在于救济苍生,而非穷兵黩武。”
道安见苻坚心意已决,知道无法改变他的南征计划,于是转而劝说苻坚不要亲自出征。
道安说道:“
倘若陛下执意要亲征,也请不要深入长江、淮河一带。您可以移驾洛阳,制定必胜的战略部署,并将檄文送达丹阳(今江苏省南京市),迫使东晋君臣主动臣服。如果他们仍不屈从,再派遣军队讨伐也不迟。”

苻坚被南征的想法深深吸引,甚至一意孤行到连道安的劝谏也充耳不闻。他的宠妃张夫人得知苻坚即将发动南征后,也前来试图阻止。
张夫人说道:
“妾听说天地生育万物,圣王治理天下,都应该顺应自然规律,这样才能事半功倍,无往不利。黄帝驯服牛马,是因为了解它们的习性;大禹疏通九川以抵御洪水,是顺应地势而为;后稷播种百谷,是顺应天时;商汤、周武率领大军讨伐夏桀、商纣,是因为顺应了民心。凡此种种,顺应条件则成功,违背条件则失败。如今朝廷内外都说不应伐晋,而陛下却执意要出兵,妾实在不明白陛下遵循的是什么道理?
《尚书》有云:‘上天的智慧来自于民众的智慧。’连上天都懂得顺应民意,何况我们凡人呢!妾还听说,王者兴师动众,必须上观天象,下顺人心。现在人心都不支持,请陛下再观察一下天象。俗话说:‘鸡在夜间鸣叫不利于出兵,狗群哀嚎预示宫室将空,军队出动时马匹惊慌,则意味着士兵无法凯旋。’自去年秋冬以来,鸡群夜间啼鸣,犬只成群哀号,马厩里的马匹频频受惊,武库中的兵器自行发出声响,这些都不是出兵的好兆头啊。”
苻坚听后勃然大怒,说道:“军事行动乃国家大事,妇道人家不该插嘴。”

苻坚的小儿子中山公苻诜,是张夫人的亲生子,一向深受苻坚宠爱。他也前来劝谏道:“儿臣听说,季梁在随国时,楚国人不敢轻举妄动;宫奇在虞国时,晋国也不敢贸然用兵。这是因为这些国家拥有贤能之士的缘故。等到他们的计谋不再被采纳,国家往往一年之内便走向灭亡。前车之鉴,后世应当引以为戒。阳平公是国家的智囊,然而陛下却不采纳他的建议。晋国有谢安、桓冲这样的能臣,陛下却执意要讨伐他们。这次南征,儿臣实在感到困惑不解。”
苻坚听后,轻蔑地对苻诜说道:“国家有重臣可以谋划大事,朝廷有公卿可以决定进退。你一个小孩子家,竟敢议论军国大事,这是要杀头的大罪!”
苻坚一心惦记着南征东晋,转眼间时间已来到382年十二月。然而,负责灭蝗的散骑常侍刘兰却迟迟未能完成任务。

在朝会上,有司向天王苻坚启奏,请求召回刘兰至京都,交由廷尉治罪。但苻坚并不认为这是刘兰的过失,他回应道:“此灾乃上天降下,并非人力能够完全避免。这或许也是朕施政有过所致,刘兰又何罪之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