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祖父静静地站在灵堂门口,低垂着头,声音颤抖地问:“你说,她会不会怪我没能赶得及见她最后一面?”他的话犹如从喉咙深处挤出来,每一个字都带着砂砾般沉重的沙哑,让人刺痛。

灵堂里,橘黄色的昏暗灯光洒满空间,白布随微风轻摆,像在诉说什么未知的情感。祖母安静的遗容,让人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平静。然而空气中弥漫的淡淡香烛味,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满堂的白菊花映衬下,唯一不变的,是她曾经温暖家里的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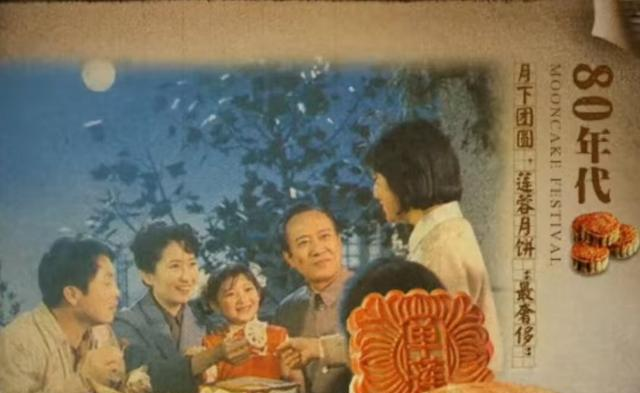
祖父黯然跪下,在木棺前久久不语。他拉近手中的祖母旧围裙——那个陪着祖母种田养鸡的围裙,早已泛黄,但仍存有岁月的皱褶。他的目光像是穿越了时光,回到了那个她还躺在阳光里的午后。

祖母的一生是平凡的,却以坚韧、热忱浇灌了我们的家。村里人都说,她总是一副精神抖擞的模样,最热衷于在院子里晒太阳,还喜欢拿点小零食逗孩子们玩笑。谁知道,前两天的清晨,家里突然静得出奇,没有饭香,也没有她忙碌的身影,只有一束晨光穿过窗户,洒在她安详的脸庞。那一刻,她的表情如同在午睡,将生命的最后一刻定格成永恒的宁静。

噩耗传来时,我正在城里奔波事务。爷爷的电话只有短短一句:“你奶奶走了。”倘若有人亲历这句话的冲击力,便能理解我当时的恍神与无措。车子驶向村口时,天已擦黑,满院子的哭声和人声交织在一起,像是一曲痛楚的挽歌。

丧礼的准备忙乱而有序,院子里堆满了白菊,家族中的叔伯们四处奔走,联系木匠制作灵柩。爷爷疲惫得没有力气参与任何事,他只是守在灵堂,眼神呆滞,仿佛陷入了记忆的深渊。
受村里流传的风俗影响,人们认为狗能看见人看不见的真相。次日早晨,村东头老王家的狗突然发出狂躁的吠叫,冲着灵堂方向奔来。乡亲们面色凝重地议论着,而祖父却在闻声赶出灵堂后,轻声说了一句:“别吵了,她走得很安稳。”
就在仪式结束后的第二天清晨,祖母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封信,字迹虽然潦草,但每一个字都充满力量:“弟弟,这一生你太苦了,我走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爷爷久久地握紧纸张,将痛不欲生的情感转化为一声轻轻的叹息:“她还惦记我。”
祖母的葬礼如同她的这一生,无声无息,却又在平凡中彰显伟大。尽管亲人们都说她离去是“喜丧”,因为得以见证子孙满堂,后事也尽善尽美。然而对于家中那些晚辈来说,心底的落空感却始终挥之不去。
送葬那天,爷爷始终走在队伍最后。他没有哭泣,也没有言语,只是一边低头默默走着,一边似乎在与某种深刻的回忆对话。当木材缓缓入坟,他跪下磕了三个头,声音坚定而低沉:“姐姐,你放心走吧,我一定会照顾好这个家。”
然而,真正的意外仍藏在后来。当葬礼完成的第二天,祖父突然病倒。医生诊断并无大碍,只说是心里过于沉重,情绪波动过大。躺在病床上的祖父安静得异常,当我走进病房时,他正静静地注视着窗外蓝得发亮的天空。他笑着对我说:“你奶奶一定在看着我呢。”
我陪着他聊了一会儿,直到他忽然问我:“你说,我是不是欠了你奶奶一辈子?”当时的我哽咽不知所措,只能摇摇头。他却自问自答:“她总说我拖累了她,可其实,她才是我的命。”
后来,祖父的身体渐渐康复。他开始帮忙打理家里的事情,无论是种地还是养鸡,总是忙得不亦乐乎。他说,这是奶奶留给他的责任,他得替她好好完成。
一天傍晚,他感慨地对我说:“你奶奶啊,活着的时候总操心这个操心那个。她走了,我得替她把这些操心的事情接过来。”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这份爱是那样深厚,无需华丽语言,却能点亮所有在阴暗中徘徊的灵魂。
就这样,故事画上了句号。
奶奶的面容,她的微笑,还有她与爷爷之间那份深沉的感情,成为了我们一家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时间过去,留存下的,是不灭的温暖,是祖父和祖母生命中交织出的那段交响曲,犹如一盏长明灯,照亮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