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6年的莫斯科,演播厅里满满当当坐了几百人,安静地等待着。台上放着麦克风和一架钢琴,镜头扫过观众席里的男男女女,他们衣着鲜艳,年纪和职业各异,其中可能有语文老师,也可能有铁路工人,他们把参加诗人的朗诵会当作最普通的饭后节目,而穿着军装、戴满勋章的人们,很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击纳粹而获得军功。或许,在铁幕另一边的西方世界,这样规模的观众在期待摇滚、爵士乐和迪斯科的震荡,可在这里,苏联人在静默中等待着诗人,贝拉·阿赫玛杜琳娜,这个在苏联解体三十余年后,在中文世界仍然陌生的俄语名。
很快,一个朴素的女人走上舞台,用清晰而旋律化的声音背诵自己的诗歌,关于友情和孤独,关于创作的焦虑和与文学前辈的对话,关于音乐的馈赠,关于日常生活最普通的幸福,和瞬间中倏忽闪现的永恒。镜头缓缓扫过观众专注、微笑、沉思的面孔。
《玫瑰的行为:阿赫玛杜琳娜诗选》面世,介绍的不仅仅是一个俄语诗人,还有她的观众、她的时代。诗人的视野照亮的六十和七十年代苏联文化生活,是国内俄语文学书架上缺位已久的拼图。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后开放的文化氛围,让思想的土壤终于松动,新的抒情语言从中发芽。动荡的战乱让人们原先对苏联社会的期待得到考验和沉淀,对文艺的热情在趋向稳定的市民生活中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内省、独立的诗歌语言,得到了响亮的声音和热忱的观众。

《玫瑰的行为》,作者:[俄]贝拉·阿赫玛杜琳娜,译者:王嘎,版本:译林出版社 2025年1月
那么,阿赫玛杜琳娜是谁,在浩瀚的俄语文学界,为什么偏偏阅读她?我们已经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十九世纪的经典作家翻烂,我们反复阅读不同译者翻译的、超新星一般璀璨的白银时代,熟悉茨维塔耶娃短促而剧烈的抒情、阿赫玛托娃在个人和时代间游走的崇高语调,熟悉曼德尔施塔姆的诡谲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清新……在这些独特的星体间,怎样的文学星辰才能引人注意?
阿赫玛杜琳娜对诗性自我的言说,离不开她实际的和虚拟的对话者:她的生活,她的好友和爱人,还有上述每一位无法忽视的俄国诗人。最后,她离不开终极的对话者:她自己。在这一系列对话中,阿赫玛杜琳娜锻造出独一无二的声音。

 撰文|习蓝
撰文|习蓝

诗人登场
阿赫玛杜琳娜的诗行往往内省的嗓音与外界的声音间交错,形成中性、清晰的语调。在《这是我》这首自我介绍性质的诗中,她的语言在两种不同的尺度间来回运动:她骄傲于自己的诗人天赋与身份,以童话般的轻盈幻想着自由驱策语言:“我傲慢,年轻,体态丰满……/‘做词语的新郎和新娘!’——这是我在说和笑”;另一方面,她倾听着外界的细微声响,谨慎地掂量着现实的重量,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疏散、见证了真正的死亡:“云层里是替我死去的人/那一张张模糊的面孔。/……/这是我,在巨大的预感中/听见比声音更微小的声音。”
诗人在轻与重的平衡间,同时看到自我想象中自己的形象和自己在外部世界中的位置:她既是浪漫的歌手,幻想着自己具有与众不同的使命,也是芸芸众生的一员,在电车上瞌睡,在人群里排队。在诗歌结尾,她把自己放在了商场、电影院和火车站的队列中间,向读者指认和任何普通人一样的诗人。

贝拉·阿赫玛杜琳娜。
然而,这种中性语调并不说明阿赫玛杜琳娜是个平淡的诗人。恰恰相反,它成为表达戏剧性的工具。她运用具体物象和现实事件的规则,赋予抽象之物以感官上可信的细节,化飘渺为有形。正是凭借这种专注而清晰的视野,她的《寒战》“把自己感冒时的颤抖抬升到了宇宙失序的高度”(约瑟夫·布罗茨基语):
“‘您的病情并不复杂,
甚至有可能完全无碍,
但我没办法看清您——
您抖动的频率妨碍观察。
好比物体发生震颤,
而运动的幅度过于微小,
视觉上近乎为零,
它会显得一团模糊。’”
诗人妨碍诊断的抖动,正如诗歌末尾所揭示,和寒战同样是灵感的某种征象。灵感引起身体的高热失序、邻居的不满、医疗仪器指数超标,使医生写下科学的诊断并辅以药物治疗,一个往往存在于主观中的概念,通过破坏现实秩序而获得具体的形状。当感冒痊愈,诗人却想念起生病时异样的激情,这种激情实体化为超出温度计限度的热力:“指针和刻度顿时坠入恐慌!/疯狂蹦跳的水银兴奋异常!”
诗性冲动在这里外化为身体的疾病,与“我”意图掌握身体的意志搏斗,又在与邻居的互动中引发喜剧效果。阿赫玛杜琳娜把灵感放置在看似客观的“科学诊断”下,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感伤色彩,并且把自己与灵感的关系、受灵感控制的自己与外界的关系,设置成一出不无滑稽的情景剧:邻居对感冒的她表示不满,她会见医生,治好了感冒,随后怅然若失,失去下笔的灵气,而邻居的态度也并未恢复。这样的剧本,把本诗实际上的主题——写作激情的身体化——置于微微扭曲的镜片之下,呈现出夸大而又精细的戏剧性。
 对手戏
对手戏 阿赫玛杜琳娜是高度戏剧化的诗人。如果说在与日常生活的对话中,她欢迎现实物象制衡自己的浪漫幻想,那么她在假想的对话里放任自己去构造戏剧性的布景。所谓假想的对话,往往是其他诗人的交锋,致敬、戏仿、挑战。在我们前文提及的白银时代诗人之中,帕斯捷尔纳克在她的创作和生活中有特殊的地位:他们的住处相距不远,且他们确实相遇过。可是,现实的相遇让阿赫玛杜琳娜胆怯,在她看来,帕斯捷尔纳克是“美妙语言的古老舞台”,这一身份让他的实际在场显得不真实。在他亲切的邀约面前,阿赫玛杜琳娜没有上门拜访。
她缺席的答案,在《登上舞台》一诗中揭晓。与这位前辈相遇的方式,只能是成为他的对手,建立新的舞台。伟大诗人的注视催促她铤而走险:“我要把笨拙的姿势变成鞠躬,/不再惋惜自己的词语和苦难。”观众的目光鼓励诗艺的表演家迎接最残酷的挑战,同时,这种注视本身就是创作险象环生的一部分:经典作家的影响既是馈赠也是锁链,阿赫玛杜琳娜在其中焦虑挣扎,也吸纳了前辈作家的风格和遭遇:写茨维塔耶娃,借她意象的凝练和爆发力,反复写她自杀身亡的小镇叶拉布加;写阿赫玛托娃,以她优雅的节制,给她作线条简练的画像;写普希金,用他的讽刺和调皮,仿写《叶甫盖尼·奥涅金》里达吉亚娜蹩脚的法语情书。
诗歌史被排演成历史剧,阿赫玛杜琳娜既是演员,也是导演。她表演前辈们的形象和语调,再设计一幕幕场景敷演他们的命运,参与他们一生的情节,对自己手造的诗人偶像表达爱慕和嫉妒。诗人们在她的假想世界中获得无限的舞台,帕斯捷尔纳克居住的街道“打开长度和宽度,/从容地收取全世界/所有的雪和所有的月光”;逝去的诗人也重新获得了具有隐喻式特征的身体,喜爱甜食的曼德尔施塔姆成为“嘴里塞着异物的歌者,失去口粮的美食家”。在一场场超越时间、与前辈对话的戏剧中,阿赫玛杜琳娜对自己并非天才的叹息,也成为发展个人风格的表演戏码。
幸运的是,与天才假想的角力远非她世界的全部,阿赫玛杜琳娜的诗篇常常充满友人相聚的喜悦,这让诗人暂且忘却自己“缺乏天才的光辉”:“如今我更成熟,也更清醒,/我想和朋友一道用餐——/只有他们的问候才是温馨的。”甚至在她向朋友呼救、请他们帮助饱受孤独折磨的自己以前,朋友们就早早赶来、报以回应:“他们没等召唤就来了,/对我说:您的表走得快。”无需请求就已经来到的朋友们,甚至自责没有来得更早,温暖的情谊让诗人忍耐着啜泣,让友人们包围自己,如同海浪涌上孤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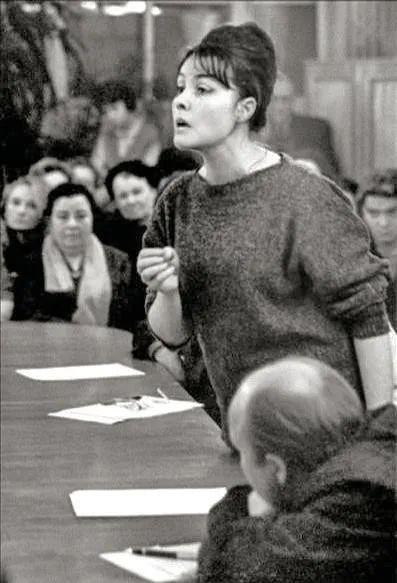
贝拉·阿赫玛杜琳娜。
可孤独不可能被一劳永逸地缓解。对于阿赫玛杜琳娜,是孤独顽固的存在感,让她尤其鲜明地体会友情的质地。诗歌《年复一年,从我的街边》,由于被改编成歌曲在《命运的捉弄》中响起而闻名,作者用多么冷峻的物质细节去捕捉朋友们离别后孤独的质地:“哦,孤独,你是多么强硬!/你像铁质的圆规闪烁微光,/你如此冰冷,将圆形闭合,/对无谓的告白置之不理。”
孤独在诗人的感知里,是坚硬的、冰冷的、蓝色的。她把它拉伸、延展,转化成一个个可以行走其中的世界,变成树林、图书馆、音乐会……孤独成为一种广阔的知识,她与其说是接受或忍耐它,不如说是探索、游玩它。在孤独的教诲下,或者说,在与孤独的朝夕相处中,诗人达成了与自然、与真理的秘密沟通。最终,在孤独的深处,朋友们的面庞再次出现,又很快消逝。对孤独的体认,仿佛更加真切地召回了友人在记忆深处的存在:
“我会探究智慧和哀愁,
事物向我交托隐含的意义,
大自然也将依偎在我肩头,
道出它童年的秘密。
直到那时,透过泪水和幽暗,
透过往日可怜的无知,
我的朋友们美好的形象
才会重现,又再次消逝。”
朋友们的美好形象倏忽即逝,与世间万物一样脆弱而短暂。然而,阿赫玛杜琳娜在恒常如新的孤独中持续发掘着友情的意义,哪怕友人们离去的脚步声年复一年响起,那些珍贵的面孔对于诗人将会不断浮现——孤独的持久,巩固了友人们的面孔。在这里,冷静的风格根植于丰沛的、深涌的热情,阿赫玛杜琳娜善于在后者的激流中找到锚点、脉络、形体。
正如孤独在阿赫玛杜琳娜的诗歌中不是封闭的,是开敞的经验,它朝向友谊的回归,爱情在她笔下也不是微妙的心理室内剧,而是打开新世界的交响乐。在献给她的丈夫鲍里斯·梅赛勒的诗《楼房》中,诗人气喘吁吁地跑进爱人的画室,她爱上了途中的一切,兴奋地描画事物的特征:墙面的涂鸦多么荒诞,上了年纪的邻居多么亲切!灵魂把热恋平等地投向目之所及的一切,听到世界无限的声音:“别人的哀愁、婚礼、闲言碎语,/步入猫的号哭和孩子的呢喃。” 爱情并没有聚焦于情人的特征之上,而是扩大了主人公感受存在的范围,她写道:“爱有多深,就有多仁慈和博大,/对美的含义就有多敏感!/我的城市,像一座新城,/向我呈现自己的特征。”

与第一任丈夫、著名诗人叶甫盖尼·叶夫图申科合影。
爱情拓展了空间,也改变了时间。诗歌的最后两节:
“林荫路旁有过一座楼房,
不仅有过,而且一直都在。
为何总是说:我来过这里,
而不说:我就在这里?
依然活着,依然被爱着,
这一切现在全都属于我,
可我又觉得,所有这些
好像很久以前就结束了。”
诗人反思自己回顾性的视角。或许是个性使然,或许是职业习惯。她总是戴着回忆的镜片去追溯事物的在场,而爱情把她与此时此刻连接,不再需要通过怀旧的视觉噪点看向现在。她说:我在这里,我依然活着,依然被爱,我拥有一切。即便这样坚定的宣言仍然带着忧伤的不安全感,诗人说:“只存在一时的纪念碑,/……可我相信/我能经受春天的热情。”也就是说,她要完整存在于此刻,迎接它蕴含的全部热情,哪怕也必然全部承受失去此刻的痛苦。
对于阿赫玛杜琳娜,与伟大的诗人对话是在文学史中打开时间的纵深,而友谊和爱情把她从写作的抽离感中拯救,重新连接到当下存在的喜悦。在与他人或假想或实际存在的关系中,她不忌惮表达自己的哀求、嫉妒、爱慕、谦卑,无论多么激烈涌动的思想和情谊,都被准确地装订为明晰的诗行。
 独白
独白 那么,当诗人不居于任何关系中,在她独处的时候,面对的是什么?
唯有时间。
阿赫玛杜琳娜在流动的时间中追求着冷凝的形式。她关注季节和永恒的关系,企图捕捉两者微妙的联系和差别,就像区分两种密度不同的流质:“我爱逝去的春天,爱它的/房子和花园,山的作用/使它盛大的自然悬在半空,/高过大地,低于天穹。”悬在半空的自然是超现实的,然而它完美地概括了在回忆中被提纯的季节的抽象性:诗人寻找的,不是一再逝去的、具体的春天,而是与永恒关联的春天。从“阳台窥望永恒的本质”这一野心,像阿赫玛杜琳娜的众多激情一样,是冷的:“一股凉意掠过我脑际,/我仿佛逾越了理智的界限,/竟然像宇宙表示亲昵。”
诗人反复叩问,这野心是否太过放肆,太过逾越理智?在速朽的片刻,追求与宇宙的连接,是不是一种太过剧烈的燃烧?在这里,阿赫玛杜琳娜的理智对激情说话,两者的对话构成一种美妙的均衡,正是走在钢丝上的艺人所需要的:一边是对永恒的贪婪,另一边是对此刻的审视。诗人没有得出答案,只是用温度计不断测量这种热情的温度,在后者任性地膨胀时,尽量精确地追随它的形状。

1977年访美期间与布罗茨基合影。“我驾车离去,来到即将燃尽的雪地。我的诗人从哪里接受春天的影响?那幅布满丁香雀斑的陶瓷画像,我打算赎回或者从国库里窃取。
阿赫玛杜琳娜时常陷入永恒与当下的拉锯,比如,她在《黄昏》中发现昏暗光线照亮的花园入口,仿佛通向时间之外的小径,具有超脱于时间的自由。走入这个时空的她,仿佛误入了他人的世纪,充作陌生人命名日的来宾,在喧闹的舞会中,她始终能听见这一切最终“注定化作天空和水的寂静”。与上一首诗不同的是,在这里对永恒的体验,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满足,而是已然发生的迷失:“视觉的偏差,精神的迷悟/将我归还于昔日的林荫路,/使我徘徊其间。”而相似之处在于,当诗人流连忘返于永恒的体验,她的理智再一次醒来,把她引回原本的时间:“但理智受到暮色的惊扰,/渐渐清醒,它想要寻觅/并重新认识那些生灵的写照,/认识我的世纪、我的时光、我的桌子和床。”理性就是这样一次次把朝永恒扑去的灵魂牵回诗人的身体。
追求永恒是可能的吗?在诗人与稿纸挣扎之际,季节变换,她与不同的鲜花和果实交谈,和它们演出一场又一场微型的悲喜剧,在它们的绽放和成熟中看到诗歌的形式趋于完整,花园是她观察的对象,也是培育诗艺的场所。最终,花园蜕下物质的表壳,演化为语言的花园,成为写作的园地。逝去的生命和失落的时间,只要回返这里,就能得到复苏:
“如果走出去,我进入的
又是哪里?五月,泥土坚实。
我来到一片荒凉的空地,
从中读到,生命逝去了。
逝去了!生命匆匆向何方?
它只抿了抿沉默双唇上
一丝苦涩,说了句:一切
都是永恒,我却是片刻。
那一刻,我没能看清自己,
也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花园。
‘我走进花园’,我写道。
是我写的吗?这就是说,起码
存在着什么?是的,不仅存在
而且奇妙,出入花园——并非凭借
行走和脚步。我哪儿都没去过。
我只是这样写过:
‘我走进花园’……”
语言的花园拯救了必死的荒凉,让生命和时间拥有栖息、休养、复苏的地方。我们无法责怪诗人“偏爱回忆,胜过拥有”,因为只有在回忆里,我们才怀抱已逝之物回返的希望,而那些离开的、被遗忘的友人面庞、那些有朝一日也会失落在历史中的热恋时光,从孤独锤炼出来的诗行里,再度浮现。
说到底,我们阅读一个诗人并不因为她比其他人更好或更加特别,而是因为我们需要诗歌帮助我们抵抗死亡和遗忘的恐惧。我们可以信任阿赫玛杜琳娜的智性,为无处流泻的、生的热情,提供荫蔽和容器,让即将失去的时间得到形状和保存。
现在,诗人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也可能在观众的心灵里,刚刚开始。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习蓝;编辑:宫子;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2024书评周刊合订本上市!
点击书封可即刻下单
 了解《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合订本详情
了解《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合订本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