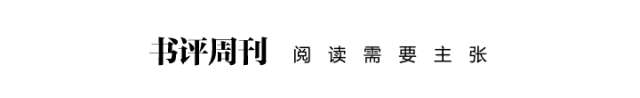
在抒情诗歌方面,俄国诗人已经在往昔的世纪里建立了庞大甚至可以说沉重的土壤,让后来者只能仰望并承受它的重量。那么,贝拉·阿赫玛杜琳娜的诗歌就像是一支破土而出的玫瑰,它延续着抒情诗歌的传统,并且创造了属于这位诗人自己的边界。
阿赫玛杜琳娜的诗歌语言非常简洁,往往就是在四到六句诗行构成的段落中发出内心的回响。她的诗歌意象也看似非常简单,街边的楼房,大海,月亮,花园——都是看起来非常质朴的风景,同时她处理这些诗歌意象也没有采用特别标新立异的方式,往往也是延续着这些风景在人类整体审美中的形象,但是在这些看起来简单明了的语句中,阿赫玛杜琳娜却有着非常深远的诗歌主题。尤其在后期的诗歌创作中,阿赫玛杜琳娜的诗歌渐渐变得不那么简洁,在她一直书写的个人化内心中开始出现更多繁杂的情感与思考。她的诗歌就像是抒情花园里的一支玫瑰,看似轻盈,但在抚摸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身上遍布着触及社会感知的棘刺,以及在这支玫瑰的深处,有着一个更为庞大的根植于俄国历史、宗教、社会以及个人哲学等维度的复杂根系。

 撰文| 王嘎
撰文| 王嘎 无论外在形象还是精神气质,贝拉·阿赫玛杜琳娜都极具魅力,恐怕没有哪位俄罗斯诗人像她一样,身上贴满女神的标签。传记作家德米特里·贝科夫称她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最美的女性,拥有著名的水晶般的嗓音”,同时也是“最无助和最坚韧的一个”。作为苏联六十年代诗人群体的一员,她的名字经常与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等人并列,但她的诗歌风格却与这些同时代的佼佼者迥然有别。通过扩大词汇和句法,她将现代口语融入俄罗斯古典抒情诗的音韵系统,赋予诗以新的生命力,暗自回应现代社会复杂深刻的变迁。
德国文学评论家沃尔夫冈·卡萨克指出,诗歌对阿赫玛杜琳娜而言是自我揭示。在她的诗作中,内心世界总是与外部对象相结合,隐喻和象征的意义普照日常事物,“一切都可能成为灵感的源泉,激发大胆的想象,产生狂放的形象,引发异乎寻常、超越时空的事件;一切都可以获得灵性,恰如任何自然现象。”尽管阿赫玛杜琳娜的创作被一些批评家指为“形式主义”或“自我封闭”,主题和意象也较狭窄,时有重复,但是在俄罗斯现代诗歌史上,她的地位和影响“已得到相当清晰的确认,而且只能在历史视角下重新审视”。

贝拉·阿赫玛杜琳娜雕像。
 “我与持花女子有何不同”
“我与持花女子有何不同” 1937年4月10日,阿赫玛杜琳娜出生在莫斯科,父亲是来自喀山的鞑靼裔官员,母亲有意大利血统,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МИВ),精通多门外语。按照阿赫玛杜琳娜的自述,母亲在三十年代对西班牙非常着迷,她请祖母为新生儿取了个西班牙名字——伊莎贝拉,因为祖母以为有位西班牙女王就叫伊莎贝拉,而实际上女王的名字是伊莎贝尔。“但我很早就发现这是个错误,于是改用‘贝拉’这个简称。”
战争的阴影伴随阿赫玛杜琳娜的童年,饥饿让她懂得“所有生灵都徘徊在深渊边缘”,生活的残酷课程教会她在孤独中“构筑整个世界”。从首都疏散到后方期间,她远离父母,是祖母用摇篮曲和普希金的诗为她开启了文学之窗。而贝拉也是天资聪慧,早早就“啃完”祖母留下的旧书。她曾用木炭描绘防空洞里读过的《战争与和平》,也曾在阁楼上与“果戈理的幽灵”彻夜对话,“普希金的韵脚渗进骨髓”。
二战结束前夕,阿赫玛杜琳娜回到先前居住的莫斯科旧城区,这里的花园、老广场、林荫路、街巷和庭院,投映于她日后的诗作,使她有理由自称为“莫斯科院落的儿女”。贝拉对文学的热情和痴迷远超同龄的孩子。她很早就开始写作,不仅写诗,也写小说和戏剧。她十三岁时的诗作已经俨然成年人手笔:“我与持花女子有何不同,/与抚弄戒指的少女有何不同?/她嬉笑着转动手上的银环,/却总是握不住指间的流年。”
在回顾少年期的诗歌创作时,阿赫玛杜琳娜强调,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对她影响至深,可怜的黑人男孩、无辜的黑奴和残酷的种植园主,成为她当时挥之不去的诗歌形象。贝拉经常在少先队营地分享这些诗作,总觉得自己写得很不错。有一次,她忍不住给《少先队真理报》写信,为命运悲惨的汤姆辩护。信件发表之后,她收到一位女性读者的来信:“亲爱的小姑娘,看得出你为所有遭受苦难的人感到心痛。这确实很仁慈,但你毕竟是个学生,周围还有许多孩子,你却总盯着远在天边的受难者。当然有必要同情,尤其对远方无助的人们,但或许你也该看看身边,把目光投向离你更近的事物?”这封信令贝拉终生难忘。她的写作渐渐贴近现实生活,虽然自感还十分稚嫩。

贝拉·阿赫玛杜琳娜。
中学时代的贝拉加入莫斯科“少先队之家”的文学小组和戏剧小组,立志成为文学家。大家都说贝拉多才多艺,对她的文学幻想赞不绝口。阿赫玛杜琳娜在回忆录里写道:“我沿着林荫路走回家,脸颊因这些赞美而发烫,脸上的雪都融化了。”大约十五岁时她便意识到,一切皆为虚妄,只有严肃的事情才有意义。1954年,阿赫玛杜琳娜从中学毕业,因为声称没读过《真理报》,未能通过莫斯科大学新闻系面试。她以自由记者身份在《地铁建设者报》工作了一年。第二年,发生了阿赫玛杜琳娜人生中的三件大事:首次在苏联报刊上发表诗作;进入全苏最高文学殿堂——高尔基文学院;嫁给即将成为“解冻”年代诗歌先锋的叶夫图申科,由于“爱与忧的离心的激情”,这场婚姻仅持续了三年。
 “年复一年,从我的街边”
“年复一年,从我的街边” 阿赫玛杜琳娜是早慧的诗人,她的才华和美貌很快引起文学界关注。在写给高尔基文学院的推荐信中,与帕斯捷尔纳克同时代的老诗人谢尔文斯基盛赞她的双重禀赋:“男性化的强大力量”与“孩童般的纯粹和女性化的敏锐”兼而有之。此种特质成为她诗歌的独特标识——在社会议题与私人体验之间保持微妙平衡,在众声合唱之外守护私密的情感空间。她笔下的生活情境也显得迷离飘渺,颇具神秘的仪式感。
阿赫玛杜琳娜步入文坛之际,正值苏联“解冻”时期。
“解冻”一词源自爱伦堡同名小说,暗示严酷的旧秩序正在消融。俄裔美籍学者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在《日瓦戈的孩子》一书中就此评述道:“在这个濒死和残缺的社会中生存了数十年的美好、健康、道德的东西,开始像死海表面下的喷泉一样沸腾,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如同俄国历史上屡屡出现的情形,文学是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和化身。”(Vladislav Zubok,Zhivago's Children: The Last Russian In⁃telligentsi,72)。伴随革命叙事的瓦解和个人主体意识的春潮,兴起空前的诗歌热,一个年轻的诗歌群体迅速崭露头角,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等人正是这一群体的领军人物。叶夫图申科主张把诗歌当作医治犬儒风习的道德良药,“创造善意的社会氛围,让人们敞开心扉并绽放自我”,沃兹涅先斯基则试图以“原子般的风格”,为新时代增添新颖实验性的语言。他们在各种公共场所朗诵新作,用个性化的声音说出禁忌的话语,一时间,引得追随者蜂拥而至,如痴如醉。他们的诗集一上市就被哄抢,甚至五万册也可能在一天内售罄。叶夫图申科的语调热情且又欢欣:“仿佛蒲公英的种子,/思想轻轻一吹就散开。/我们的手欢笑般鼓掌,/我们的脚步乐滋滋舞蹈。”
在这些稍后被命名的“响派诗人”及“舞台诗人”中间,阿赫玛杜琳娜却发出“铜管的呼喊”和“弦乐的悲泣”,她的语言的清透与真挚,为彼时苏维埃女性文学所罕有。阿赫玛杜琳娜对其诗歌同行的创新精神和道德理想颇多认同,她也曾自豪地宣称:“我不能说出违心的话语,/哪怕是一句小小的谎言。”然而,身处喧嚣热潮中,她逐渐认识到浪漫主义“舞台诗歌”之缺陷。文化空间固然重要,亢进的公共活动却意味着诗人对大众的迎合与主体性的丧失。叶夫图申科式的舞台表演遭到质疑,有人揶揄说,以这样的“表演才能”,即使在台上朗诵电话号码簿,也会博得掌声。阿赫玛杜琳娜开始审慎对待“舞台上的死和速朽的事业”,越来越排斥政论体抒情诗的口语化倾向。为了给艺术“降温”,维护艺术应有的纯度,她的诗歌表达采取了更隐蔽的方式,更多运用精巧的隐喻,以传达精神状态的细微变化,使作品更具音乐性和饱满张力。正因如此,布罗茨基认为阿赫玛杜琳娜是远胜于叶夫图申科和沃兹涅先斯基的诗人。

初登文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
随着与六十年代“响派诗人”渐行渐远,加上命运的波折和爱的失序,阿赫玛杜琳娜对友情格外珍惜。在她看来,朋友之间的“联盟”胜过苏维埃联盟。她像茨维塔耶娃一样,将友情径直当成爱。故而友情向来是她喜欢的主题,爱情诗的数量,反倒远不如献给奥库扎瓦、维索茨基、阿克肖诺夫等朋友的诗篇。阿赫玛杜琳娜流传最广的一首诗,便出自这些抒写友情的篇章:“年复一年,从我的街边/脚步声响起,朋友们离去。/他们缓缓别离的身影/与窗外的幽暗交织在一起……”这首诗于1975年被谱写成歌曲,作为梁赞诺夫执导的经典电影《命运的捉弄》插曲之一,至今已传唱半个世纪。而她的友人也时常对她报以诗的回应:“如果您心肠太硬,想让它变软,/别去喝伏特加,去找贝拉吧。/如果您感到有什么堵在胸口,/贝拉那里有足够的痛苦和温柔。”(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
至1962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琴弦》,阿赫玛杜琳娜已成名多时,1968年由俄侨出版社在德国推出她的第二部诗集《寒颤》,随后是《音乐课》在苏联国内出版,使她获得更广泛的知名度。大多数论者认为,她的审美直觉和诗意想象力出类拔萃,对周遭声音和色彩极为敏感。她的意象具有印象派的模糊和流动感,比喻和联想出人意料。但也有人批评她脱离时代,“政治淡漠”,公民立场缺失,国外评论界则将这些看作独立性的标志,称“阿赫玛杜琳娜的道路,是通往纯艺术的道路”。
 “俄罗斯古老词语的泛音”
“俄罗斯古老词语的泛音” 即便是初识阿赫玛杜琳娜的读者,也不难发现其艺术创作的典型特征:源于俄罗斯经典诗歌的传统形式一目了然,音韵、格律和语汇方面的传统色彩格外鲜明,仿佛前人已为她设置了时间的入口,任她回返并徜徉于“远处灯火摇曳的幽深花园”。而早在五十年代末,阿赫玛杜琳娜尚未摆脱青春期写作的滞涩和稚拙,就认定古朴的文体对她更有吸引力,古老的语言比“我们的话语”更现代,意蕴更浓郁。多年以后,她依然不假掩饰地说:“在我笨拙而纯洁的喉咙里,/有着俄罗斯古老词语的泛音”,并自称为“现代封皮之下老旧的动词”。在晦暗不明的转折时期她躁动不安,发出声响,寻找回音,最好的倾诉对象不是别人,恰恰是俄罗斯诗歌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众神”。她的“语言崇拜”的精神谱系,由普希金、莱蒙托夫延伸至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尤其是她所悲怜和钟爱一生的茨维塔耶娃,让她确信相对于当下还有另一种现实,那里才是她的主题、形象和抒情的不竭源泉。
阿赫玛杜琳娜的“普希金情结”始于六十年代初,继而贯穿她整个创作生涯。普希金像诗的守护神,在她的花园里漫步,在她的桌子和天花板之间游荡。在《蜡烛》一诗里,作者写道:“在普希金温存的目光下,/夜色淡退,蜡烛熄灭。/母语纯净、柔和的气息/使你的嘴唇冷却。”普希金的目光是她夜间劳作的见证,更是诗艺传承的见证。而面对季节变换、人世冷暖,诗人也会黯然喟叹:“我的世纪愈渐残酷,我的天赋百无一用。”但值得欣慰的是:“到处都是普希金的影子,/或者说,只有他还留在脑海和自然界。”

贝拉·阿赫玛杜琳娜
在阿赫玛杜琳娜的诗作里,通过与普希金相关的典故和回忆,客观存在与艺术现实的界限被淡化,艺术现实甚至更具真实感。以《六月六日》为例,普希金生与死的时刻戏剧性地容纳在“轶闻”的复杂嵌套中。彼得堡的六月六日,尽显“白夜的妩媚”,让人“快乐得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这是普希金诞生的日子。到了诗的后半段,“冰与火交集的崖面”却只留下“蛇的皮囊”,喻示诗人之死。作者在此处化用了俄国词典学家达里的记述:从达里那儿,公认词汇量最大的普希金第一次学到“皮囊”这个词(выползина,字面意思是“从里面爬出来”,词典释义为“昆虫或蛇蜕下的皮”)。之后普希金穿着一件新外套来找达里,开玩笑说:“这是一副好皮囊吗?嗯,我不会很快爬出这皮囊。我会在里面写很多东西!”1837年1月27日,普希金与丹特士决斗时穿的正是这件外套。两天后,精通医术的达里目睹普希金重伤致死,并写下尸检报告。
阿赫玛杜琳娜将自己交给语言的力量,因为语言也向她“交托隐秘的含义”。
在她看来,语言决定着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阿赫玛杜琳娜曾经引述茨维塔耶娃先前表达过的观念:“我不知道任何死去的诗人,对我而言,死去的诗人永远是活着的,是需要呵护的鲜活个体。”这表明阿赫玛杜琳娜与传统之间的关联,绝非个人偏好所致的“审美自闭症”,而是体现着普遍人性意义上对他人命运的理解与关爱。因而她所崇敬的诗歌先辈,不仅同她展开无休止的对话,激发她的灵感,赋予她以庄重语体和古朴音韵,还时常转化为具体的文学形象,在她笔下重获鲜活的生命。例如,当“日瓦戈风波”席卷知识界之时,年轻的阿赫玛杜琳娜拒绝加入声讨的浪潮,两年后她写下《回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一诗,赞颂他扮演了那唯一的角色,“将全世界的抚爱投向人与兽”。
当然,她赞颂和悲悼的人物远不止帕斯捷尔纳克一个。在因浓厚书卷气而被视为“室内诗”写作的生涯里,阿赫玛杜琳娜写给茨维塔耶娃的献诗数量最多,从早年的《音乐课》《履历》《我发誓》到成熟期的《塔鲁萨》(1977—1979年),读来无不感人至深。在《嘘,别作声》一诗里,她写到茨维塔耶娃曾渴望安息在那里的塔鲁萨女教徒墓地,缅怀其如梦幻泡影的悲剧人生,不禁自问:“我为什么不去拜访自己的影子?”可见茨维塔耶娃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大于所有人,尽管她的诗歌语言的黏稠质感和滔滔不绝,与前者“电报式”短促简洁的文体大不相同。
 “花开的次序”
“花开的次序”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阿赫玛杜琳娜的诗歌创作臻于成熟,将近十年的丰产期由此开始,《诗篇》《蜡烛》《暴风雪》《格鲁吉亚之梦》《秘密》等多部诗集相继出版,但可观的数量背后,却是一波三折的出版过程,种种压力和变故使她身心俱疲,处境艰难。
1977年,阿赫玛杜琳娜获选美国艺术文学院荣誉院士,并于当年春天赴美访问,受到诗人布罗茨基和作家奥莉加·卡莱尔(《巴黎评论》访谈记者)的欢迎。布罗茨基和卡莱尔事后分别撰文,发表在《时尚》杂志上(Vogue, No. 7, July 1977)。布罗茨基称她的诗开出了“一朵玫瑰”,厚实的花瓣呈螺旋状;而卡莱尔则以更为细腻的笔触写道:“看着贝拉带来的红色银莲花和蓝色鸢尾花,令人联想到花朵的神秘力量——它们在每个冬天凋零,又在春天重生。我也想起贝拉身上的这种力量。在堪称严酷的环境中,这位女性与诗人不但生存下来,而且大放异彩。”从阿赫玛杜琳娜的创作中,两位评论者不约而同地看到花朵的绽放,这的确耐人寻味。十年以后,一度淡出文坛的阿赫玛杜琳娜将其第九部诗集命名为《花园》,也绝非偶然。她仿佛仅仅从封闭的室内移向近旁的花园,这狂野而浪漫的“花园”却已超越她早年偏爱的、象征内心隐秘世界的“房子”,成为诗的稳定的同义词,也成为她的整个世界的同义词。
阿赫玛杜林娜对花园的日常景观并不感兴趣,“花园”的概念被她赋予多重文化意涵:既可透过昔日渺茫的光影(“让我们留在往昔岁月的花园里”),呈示“另一个时代”存在的证据,也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像白纸一样容纳诗的语言,容纳孤独脆弱的生命:“我走进花园,但繁华和幽寂/不在这里,在‘花园’一词。”而词语一旦接受自然的滋养,则变得“比土壤更肥沃”,比周围的空间更加开阔和自由。
在阿赫玛杜林娜的花园文本中,各类植物和花卉频现,依照时节更替,次第开放,抑或无声地凋零,一如《传道书》所云:“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然而,作者对这些花卉本身并未增添更多特定的意义,它们如同其他自然现象,最大限度地避开拟人化和主观化,主要用于构成语义的序列,进入植物的花期,或者参与构建一个色彩的小宇宙(参见《被遗忘的球》《花开的次序》《再见了,我的山崖》等)。屡次出现的玫瑰形象也不是为满足爱的抒情,营造轻松的观感,而是暗示俄国文史当中某些经典情节,与之形成互文关系,例如在《玫瑰的行为》一诗中,对一位溺亡的俄国艺术家的悼念,正好与弥漫在屠格涅夫散文诗里的感伤情调相呼应。互文手法在《花园骑士》《玫瑰的幻影》等诗篇里也很突出,超现实主义的片段同时介入进来,汇聚为交响和复调。文本自身的“扩容”,激发并延长着审美的感受。就此而言,阿赫玛杜琳娜在传统道路上显然已走出很远。
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玫瑰,“花园”主题更多是献给稠李和丁香,前者犹若白桦,是俄罗斯自然与文化的典型象征,标志着“自己的”空间;后者更适应相对温暖的地域,譬如作者为之动情的高加索,终归是属于“他人的”空间。植被的差异及文化的跨度,也说明绵长思绪所能抵达的纵深地带,这一点似乎同样有别于前人,而更显某种现代意味。
当然,阿赫玛杜琳娜的后期创作也不乏现实关怀。她时常将目光投向普通人尤其是农村居民的凄凉景况,用民间语言和声腔与之歌哭,同情共感。苏联解体之后,她的一些被禁止发表的诗作得以问世,包括带有宗教内容的作品。阿赫玛杜琳娜晚年视力严重衰退,几乎停止创作,这位诗坛女神的生命之花凋谢了,直至2010年11月29日在莫斯科郊外病逝,落葬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墓碑上镌刻着她最后的诗行:“无论如何,都不会诅咒,/我只为这轻盈祝福:/那是你短暂的烦忧,/是我长眠的静寂。”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王嘎;编辑:宫子;校对:薛 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2024书评周刊合订本上市!
点击书封可即刻下单
 了解《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合订本详情
了解《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合订本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