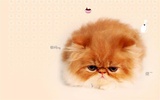火色有爱[招财进宝]欢喜自在
为什么明治维新能够成功?

今天周末,去了横须贺逛了逛,久闻那里有佩里上陆纪念碑、三笠号纪念舰和驻日美军基地,是一个能贯穿整个日本近代开国历史的崛起、歧路、复兴三个阶段的地方。

但真的到了当地,才发现横须贺其实首先是一个宁静的小镇,有修得很漂亮的民居一户建和不错的餐馆,除了停泊港内的美军军舰,给人感觉首先其实是风景优美、人口不多、适合居住。
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一个不被任何旅游攻略提及的小小纪念馆,它位于JR横须贺站门前最显眼、港内风景最好的地方。而且这个纪念馆也不是纪念日本人的,而是一个同样看似不起眼的百年多前的法国人——弗朗西斯科·朗斯·韦尔尼(Franccois Leonce Verny)。

这个人做了什么,值得日本人如此纪念呢?
1853年的时候,美国海军提督佩里率舰队来到横须贺,以武力强迫日本开国,这件事情在日本被称为“黑船来航”,因为美国当时的军舰都已经使用了蒸汽轮机,用铁皮包裹。技术水平还处于中世纪的日本人感到很震惊,他们眼中极为金贵、用来打日本刀的钢铁,美国人居然拿来造船——而且造的还是那么大的船,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与同期的大清虽然已经打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但把所有的战败的罪责都推到个别“汉奸”“卖国贼”头上,试图继续关起门来喊皇上万岁万万岁不同。在日本,其实即便是后来被定义为是腐朽落后、最终在倒幕运动中被推翻的江户幕府,也对学习西方技术文化颇为好奇。1853年的时候被逼着开了过,1859年的时候,幕府就借着去跟美国人换约的机会,派了一个规格颇高的考察团,远渡重洋,想去看个究竟。

这个考察团当中担任目付(监察)的人,名叫小栗忠顺,此人是德川幕府中的改革派三杰之一,他到了美国就被美国人当地的技术能力震惊了,不等回国就马上写信给幕府,说“西洋技术能力之强,已非我国所能望其项背。若不锐意改革,则亡国之危不远矣。”
幕府问他怎么办。小栗忠顺给了一个影响后来日本国家走向的正确建议——直接花高价聘请国外的人才,到日本去帮助该国建立近代工业产业。
这个建议幕府也很快就批准了,但想聘请真正一流西方技术人才何其之难?当时绝大多数愿意到这个西方人眼中“半开化国家”去碰碰运气的人,其实都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另外西方各国政府也确实看到这个借向日本输送顾问来对该国施加影响的机会,愿意把这些在本国也没什么大用的二流人才输送给日本——反正自己不送、别的列强也会捷足先登。你看,其实当时西方的技术封锁,没后来想象那么严密。

与东坡吟 共东坡醉
所以从幕末到明治维新时代,仅登记在册的,被日本官方和企业雇佣的外国人才就高达近三千人,这些人的专业包括了日本最开始急需的技术、科学,后来则慢慢延伸到法律、社会、文化,甚至艺术。
而这个韦尔尼就是其中之一,非常让我这个中国人感到喟叹的是,这位韦尼尔其实是小栗忠顺从当时的大清那里“挖来”的,当时这位法国小伙子刚刚从海军造船大学毕业,听闻大清在引进西方技术,就远渡重洋到宁波的造船厂碰碰运气,结果去了以后就被大清当时官办工厂的作风搞郁闷,一看正好日本在招人,才选择了这个当时看来更弱小的邻国。
但韦尼尔后来在日本一待就是十一年,不仅指导日本建立了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炼钢厂——横须贺制铁所,而且还在横须贺当地建立了一整套职业教育体系,包括培养工程师的技术大学和技工学校等等。甚至横须贺这个小镇,最初的西洋道路设计、市政规划都是韦尼尔操刀代办的。
因为见识了西洋的技术力,决心锐意向西方学习的小栗忠顺对这个首个招来的法国青年工程师十分信任,一来就让他担任了横须贺制铁所的所长。不仅如此,小栗忠顺还利用自己在幕府的影响力,帮助这所新兴的制铁所申请来了大量的资金。后来每次韦尼尔找到小栗忠顺,提出要修铁路、要办技术学校、甚至是邀请传教士建教堂,小栗忠顺都几乎照单全收,提供鼎力支持。

火色有爱 欢喜自在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国内的政局也并不十分太平,幕府在民意压力下,在“开国”和“攘夷”之间态度变了好几次,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后,幕府自身的统治更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手下不止一次劝过小栗忠顺——有这个钱还不如多买一些洋枪洋炮,毕竟现在倒幕的那几个强藩闹得那么凶,这日本将来还不知道是谁的天下呢?
可是小栗忠顺怎么说呢?“买枪炮只有一时之用。但即便幕府不在了,建一所好的制铁所,也能留给将来的日本啊。”
其实相似的话,日本幕末的海军创始人胜海舟也说过,有人劝他不要开办海军学校,目前幕府和倒幕强藩的主要矛盾在陆上,胜海舟说的也是:“这是未来的日本所需要的。”
只不过与明治维新后被封伯爵、得了善终的胜海舟不同,小栗忠顺在倒幕战争中支持幕府失败后,因为坚决不向明治新政府军投降,被官军斩首了。临死前小栗忠顺特地留了一封信给已成为他好友的韦尼尔,恳请他继续留下来为新日本效力。
而明治政府在这一点上倒也通融。按说法国在倒幕战争中是隐隐站在支持幕府那一边的,但倒幕战争结束后,明治政府丝毫没有因为韦尼尔的法国人身份而介怀,继续以高薪聘请他出任横须贺制铁所的厂长,直到1876年(明治九年),韦尼尔才功成回国。
而他留下的横须贺制铁所,是日本近代产业自主的先声。十余年后的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联合舰队与大清的北洋水师在接战时,一个重要的隐形优势,就是当时的日本已经有了自己完整的造舰产业链,丰岛海战中发挥巨大作用的秋津洲号,就是1894年当年刚刚在日本完工下水的,而大东沟海战后,之所以日本重伤的四艘军舰能在短时间内修好,而北洋水师在这一战之后就彻底失去了战斗力。正在于两国产业链上的差距。

欢天喜地 事事如意
而在这座小小的纪念馆里,日本人把韦尼尔这位原本在法国和大清都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年轻工程师,奉为了他们工业上的恩人,纪念至今。
当你看到日本人给他的纪念馆,给他立的塑像时,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感触。
你可能会想起,好像在我们的近代历史上,除了一个白求恩医生,我们似乎没有这么隆重的纪念过某个来华的洋人——虽然在洋务运动中,受聘来华的洋人其实同样不少:
比如官居北洋水师副提督,事实上帮助北洋水师建立了一整套训令、作战系统的“洋教头”琅威理,

比如给大清当了将近半个世纪海关总税务司司长、创造了大清历史上首个廉政高效的政府职能部门的英国人赫德。
再比如美国共和党的创党元老,但晚年又受聘于大清,成为中国首个驻外使节,帮助中国真正“开眼看世界”,并最终也算为大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美国人蒲安臣。

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想过,为这些帮我们走向近代化的欧美“洋教头”们专门开个纪念馆什么的。
恰恰相反,你今天去问一个不专门研究历史的普通中国人:你知道琅威理、赫德、蒲安臣是谁么?很多人估计都答不上来。极少数能答上来,对这些人观感估计也会是怪怪的——
比如,赫德的确帮大清管过海关,也确实让关税成了晚清赖以吊命的主要财源,但这小子是不是别有用心啊?比如在给咱干活的同时帮着他本家英国操控我们的关税?着实可恶。
再比如,蒲安臣的确帮大清当过外交使节,但谁能保证他出使欧洲的时候没有和他的昂撒兄弟英国人沆瀣一气?出卖我大清的情报甚至利益?这种洋人也不值得感谢和纪念。

生意兴隆
还有那个琅威理,那就更是当年就早有定论了。给他个北洋水师副提督的职位,就是个名号,跟他客气一下而已,谁想他还自己当真了,真想在丁汝昌不在的时候节制北洋水师军舰。最后还居然因为此事负气出走了。间接导致北洋水师甲午战败,我们凭什么感谢他?
实话实说,以上三位的能耐和贡献,我觉得个个都比眼前这位韦尼尔强,但我们从来都没有认真感谢或者纪念过这些人。
所以,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搞成了,而大清的洋务运动失败了,我觉得在这个纪念馆前,我悟出一点道理了。
我们总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又何止是非我族类才其心必异,按照董明珠老师的最新发言,所有留过学的留学生,她都觉得不能用,因为害怕是帝国主义派来的间谍。这就是说,哪怕是自己人,喝了一点洋墨水、甚至沾了一点洋思想,就要被怀疑了。

那按照这个理论,当年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建北洋水师,步子还是迈的太大了。北洋水师那些管带们,除了一个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邓世昌,其他全得革职查办才对啊!因为这帮人,不都是留过洋的潜在奸细么?
所以有的时候,看着董总们的这些雷人发言,我真觉得有些恍惚——有些人,有些思潮,是不是越学越回去了?
就这认知水平,可能还不如当年的大清。
像董明珠老师这种强势老板,我是懂她的审美的:这种人对他人忠诚、恭顺乃至绝对服从的那种病态的苛求,总会戕害到她的选人用人的智商。
所以她只能用"进退自如"的王自如和认定”我妈就是董明珠“的员工。
我是怀着这样的想法,结束对这个小小纪念馆的参观,临走的时候我发现公园里维尼尔和小栗忠顺这对跨国好友的雕像并肩而立。
我在想,对于倒幕运动后的日本来说,这两个家伙,一个洋鬼子、一个反动派,本都是不足以被纪念的,但他们却依然立在那里,被今天的日本人所感谢……(来自忘川边的但丁)



东坡玖肆 有爱有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