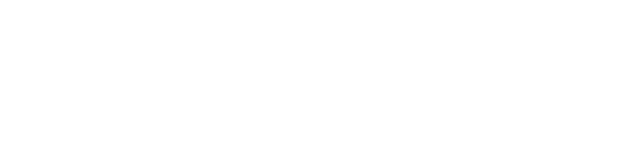

文|华觉史界
编辑|华觉史界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沉默,无论它多么可能,都不构成一种出人意料和以难以理解的方式出现的音乐停止,而是宣布和等待的沉默。
事实上,卡西娜的音乐沉默可以用元戏剧的编舞表演来解释。当奥林匹翁被伪装成新娘的奴隶查利努斯压碎时,音乐停止了。
其他三个类似摘录的教学,有助于我们在这里重建场景:在所有这些音乐停止而不离开舞台的情况下,角色的脚或腿都被镣铐铐住。
因此,正是这种阻碍的手势通过阻止演员跳舞来阻止音乐!这样的游戏是这种音乐表演的特征,其中心不是歌手,而是舞者。为了结束音乐,我们不会像在音乐剧或歌剧中那样堵住歌手的嘴(例如斯特拉文斯基的耙子进步中的土耳其人巴巴),而是固定舞者的脚。
01舞者的逐渐固定

这种元戏剧的变化并没有使将沉默和退出舞台联系起来的预期编纂无效,但它验证了它,因为元戏剧情境的喜剧暗示了它(它不是产生笑声的唯一舞蹈中断,而是它在不是音乐传统的时刻中断)。
最重要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沉默,无论多么特殊,都是合理的:这是一种奇观,就像音乐上的沉默一样,它通过一整套公告向AV发出信号,这些公告重新构成了一种闭幕式。
因此,即使在音乐被打断之前,观众就知道,在没有出口的情况下,将会发生沉默。因此,舞者奥林匹翁的痛苦呐喊,和他对自己原因的解释并没有立即导致音乐的停止。
这意味着观众见证了舞者的逐渐固定——这一奇观起到了对即将到来的音乐沉默的手势表达的作用。
同样,Lysida通过命令他保持沉默来使我口头表达音乐沉默:tacesis。事实上,这不是要求文本沉默,而是手势沉默:奥林匹克不会停止说话,而是在diuerbium中跳舞。
也是由贯穿整段的一组元素宣布的。事实上,将老利西丹、他的奴隶和卡西娜结合在一起的舞蹈立即被呈现为一种难以表演和维持的舞蹈——这立即产生了悬念。
Lysidame和Olympion已经是竞争对手,每个人都声称拥有casina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有权紧紧拥抱躁动的舞者,并表演两人的舞蹈-在三个人的场景中!
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进化的空间使得Lysidame作为奥林匹翁所渴望的色情舞蹈变得不可能。这个场景确实是用坎蒂库姆多度计写的。
然而,这个悬臂,因为它在传统的编纂中起作用,划定了一个可竖立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角色之间的任何空间和解都是不可能的。
在多米悬臂中,角色在远处跳舞,同时做旁白,因此,从康蒂库姆开始就在这里提供的奇观是与预期传统的激进第一次背离,因为两个人试图粘在卡西纳上跳舞。
音乐说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这样的舞蹈注定要失败,不能持久。因此,最终是舞台的整个奇观宣布了舞蹈和歌唱即将停止。
因此,我们发现一整套类似于闭幕式的宣布和沉默的声明。这种激进的变奏曲停止了音乐,没有任何舞台上的sor,并没有打破音乐沉默的预期编纂。
它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激活了它,因为元戏剧事故消除了看到这种预期的编纂的可能性[再做一个比较,就好比一个演员,“不小心”,在演出结束前就落下了帷幕。
初秋而这个窗帘的元戏剧性会通过回忆它来使窗帘掉落的代码起作用,它还通过再现沉默的宣布系统,甚至在第二步中,通过重新发现沉默和离开舞台之间的联系,与它联系在一起。
二氧化钰最终导致角色退出舞台。Lysidame和Olympion的最终目标不是回家庆祝并与新娘完成新婚之夜吗?与预期编纂的根本变化使得退出舞台得以完成,也就是说,最终允许遵循和验证传统的编纂。
02期望范围

因此,这两段摘录表明,如果不考虑观众所共有的这种期望范围,就不可能理解普劳图斯的喜剧,这种期望构成了编纂。他们还表明,变化构成了奇观。
观众这样认为,它并不标志着与预期的编纂的突破,而是使其发挥作用并验证它——即使它是一个激进的变体——并产生笑声。
现在是界定“编纂”的含义,并将这一概念与变化的概念结合起来的时候了。简而言之,用理论和方法论的反思来扩展这两个音乐沉默的例子所显示的内容。
我们已经看到,变异即使是根本的变异,也不会使编纂无效。它不与这个或那个规则相矛盾,原因很简单,编纂不能由规则组成。
这是我们的第一点:喜剧不能被设想为一套规则的应用。事实上,“规则”一词具有双重含义:既是解释行动的原则,也是支配行动的规范。
但是,找到解释并不等同于找到标准,确定常规操作并不授权制定一套规则。规律性并不意味着规范。皮埃尔·布迪厄在他的《实践之词》中写道:使规律性也就是说,以一定频率发生的事情,统计上可衡量的。
意识地颁布和自觉尊重的法规的产物,它正在从现实的模型滑向模型的现实:考虑'火车经常晚点两分钟和火车晚点两分钟是规则之间的区别。
规律性只创造了一个等待的视野,它不假设任何预先存在的规范知识。同样,人们也不能从普劳图斯喜剧中某些操作的规律性中推断出一组规则的存在。离开舞台和音乐沉默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是“规则”,而是观众的期望。
因此,第二点,重建一个模型,甚至一个理想,是不可能的。恢复编纂并不意味着重建一个在罗马从未存在过的模式,正如我们所说,罗马没有关于演员或舞台游戏的话语。
写喜剧是一种没有理论的实践,旁观者心中没有一个理想的模型,就像普劳图斯没有应用规则一样,即使是口头传播。
03二进制模型

将喜剧视为模型的单独执行,也将变化视为不规则性,并将每个片段视为理论模型的发散更新。
简而言之,这相当于提出了一种历史和进化的方法,有一个模型的精心设计时期,一个开花的时期,然后是一个退化的阶段。
根据这种推理,有些喜剧不会——即使它们被代表,也就是说,也会履行它们的仪式功能,因为让我们记住,在古罗马,剧院确保了仪式功能。
如果我们愿意承认喜剧不是模型的单独执行,我们仍然必须认识到,我们努力研究某些事件的规律性,并且我们必须将常规元素与只出现一次的元素区分开来。
挑战在于这样做,而不是走得太远。不走得那么远,即脱离模型的二元系统及其执行,意味着不要激进化我们在所识别的各种元素之间识别的常规链接,并考虑逐渐变化的频率。如果没有什么是固定的,那么一切都是可变的。
因此,喜剧可以被认为是一组变量,或多或少是反复出现的。这种或多或少大复发的概念是根本性的。
它不会将系统冻结成一个可以吸收变化的结构——这最终会重现一个二进制模型/执行系统,在德勒兹的启发下,最好谈论或多或少重复变量的排列。
在一千个系列中,吉尔斯·德勒兹通过反思标准语言的概念,反思了模特和标准规则的概念,这适用于我们在模特喜剧方面的工作,他写道,在同一语言中,有两种思考变量的方式。
有时以提取常数和常数比率的方式处理变量,有时以使它们处于连续变化状态的方式处理”。
常数(变量)的思想导致假设母语的存在,也就是说重建一个模型,从而在不同的实现之间提出一个层次结构:将有一种主要语言,它将有一个次要的ngue,它将使这些变量连续变化,因此这些变量将不再是恒定的。
同样,对于罗马喜剧,人们可以假设存在理想的喜剧,此外,喜剧会改变理想喜剧的恒定变量,而理想喜剧将不再是任何变量。
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必要避免模型的思想,并且有必要将常数变量和连续变量一起处理,因为常数变量也会发生变化。
“常数并不反对变量,它是对变量的处理,与另一种处理,即连续变化的处理相对立”。
因此,回到罗马喜剧,不会有两种类型的喜剧,一种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是当前的,而是通过识别(最)常数变量和连续变化中的变量来思考喜剧的两种方式。
现在,我们可以将编码定义为常量变量和不断变化的变量的排列。因此,退出舞台与创造音乐沉默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一个恒定的变量;输出涉及所有字符或仅涉及一个字符:这两种可能性构成了常数变量的第一个变体,即连续变化中的两个变量。
这第一种安排被其他变量进一步丰富,这些变量构成了我们所说的闭幕式,即口头发音和退出的手势,相机看。
04喜剧效果

例如,言语发音是一个连续变化的变量,因为它可以用手势发音或相机凝视代替,并且可以由外出或看着他出来的角色制定。
简而言之,常量变量和连续变化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完整的连续统一体。在喜剧中,不同的变量在恒定极点和连续变化的极点之间逐渐振荡。这就是为什么说“常变量”比“不变”更准确。
因此,这些不同的数据并不构成规则,而是一套“惯例”。正是这种常数变量和t在连续变化中的排列,我们称之为精确地“编纂”。
我们没有用这个术语来指定一个固定的规范性代码,这个定义并不意味着编纂和变异之间的任何矛盾。编纂的戏剧是一组变量,是传统传播和作者发明的实践,不是一套编码规则,而是没有理论的实践艺术的成文方式。
我们借用德勒兹的这种对常数和连续变化这两种变量的渐进区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使人们有可能理解在一切都是变化的安排中变化如何变得滑稽。变化和笑声之间的联系是我们的第四点。
事实上,喜剧的变化并不涉及喜剧的所有变量。它只关注(大多数)常量变量。漫画“移位是由一个受不连续变化影响的常数变量产生的。观察者的方法与两个层次的变量无关。
连续变化中变量的变化不会产生惊喜,更不用说具有喜剧效果了,惊喜只能来自恒定的变量。因此,研究的两个例子揭示了不同的喜剧力量。
一个拒绝离开舞台的角色演员的奇观,不如一个伪装成新娘的男人以大象的优雅跳舞,并破坏任何色情编舞的奇观那么有趣。
在Pseudolus中,变化涉及连续变化中的变量:我们站在微笑的一边在卡西纳中,“移位”很重要,因为场景改变了音乐沉默的恒定变量。
进一步强化卡西纳喜剧的是其他常数变量的变化,这也强调了对滞后的感知。因此,我们看到,在异常的沉默之前——并宣布——是一个不寻常的景象。
这种不寻常的印象不仅来自音乐沉默的常数变量的变化,还来自属于其他类别的常数变量的变化。舞者们站在多媒体空间中靠近年轻的卡西纳,其特点正是演员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空间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