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然怎么说?男一号的生母,荣国府的当家太太,难道能直说“这娘儿脑子不够用”吗?

说王夫人是“天真烂漫之人”,发生在传唤晴雯之时、抄检大观园之前。当时王夫人一见晴雯,开口就骂:“好个美人!真像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你干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儿揭你的皮!宝玉今日可好些?”

晴雯平时“不敢出头”,一向躲着王夫人。今天被点名叫来,一见面又不分青红皂白就一顿输出。晴雯马上“便知有人暗算了他”。只是地位太过悬殊,不敢反驳讲理,只好“见问宝玉可好些,他便不肯以实话对”,编了一堆“不大到宝玉房里去,又不常和宝玉在一处,好歹我不能知道”的话。

其实晴雯和宝玉亲近,人所共知,并不是怡红院内部的秘密。而“这一二年间”,袭人为“自要尊重”,“总不与宝玉狎昵”,推了晴雯来值夜班,“夜晚一应茶水,起坐呼唤之任,皆悉委他一人。所以宝玉外床只是他睡”,这在怡红院绝对是人所共知的。如果王夫人平时稍微留心,不应该不知道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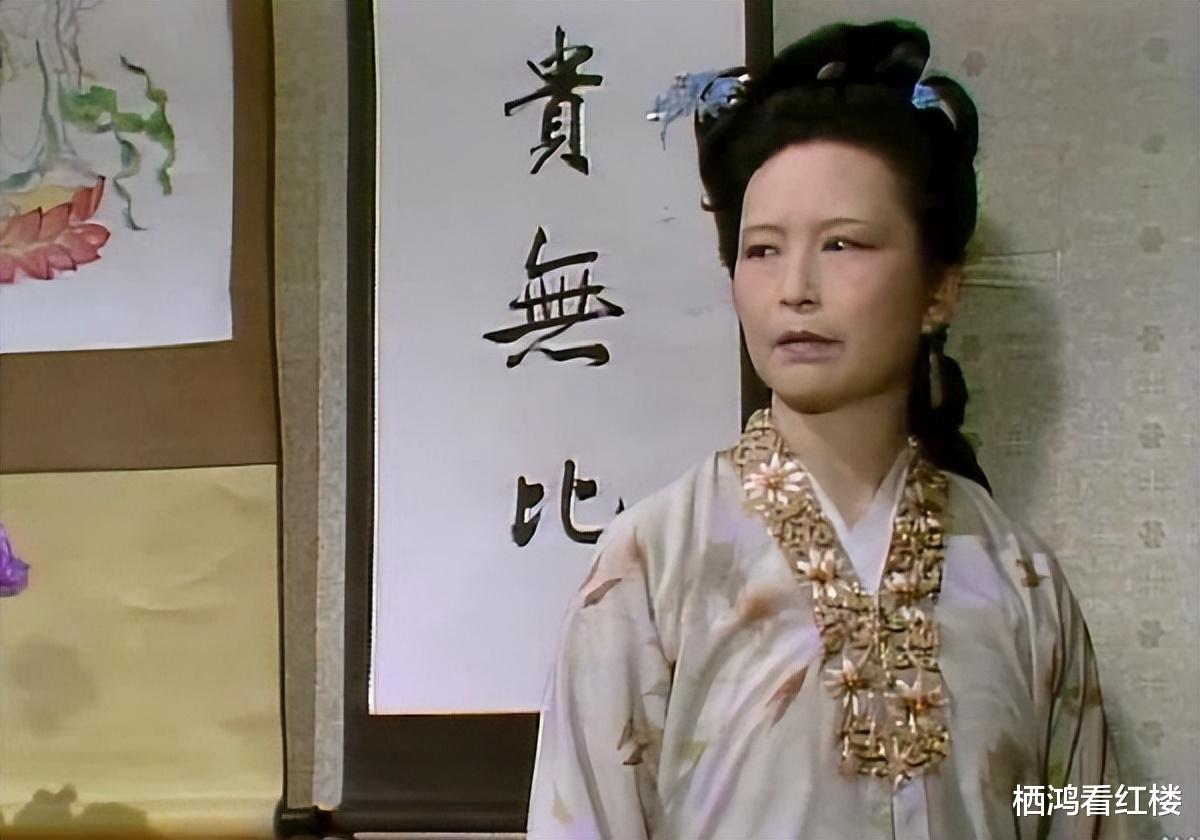
可是呢,王夫人就是不知道,听晴雯一说,就信了。有人说王夫人是假装相信、憋着“秋后算账”。这未免演绎太过。以王夫人的身份,要处分一个小丫头,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何必“假装”什么,来配合晴雯的表演?况且,敢对太太撒谎,多么现成的理由,正好抓住这个错,把晴雯打发出去。干嘛要放着这个,去找“狐狸精”的罪名?舍近求远不说,对宝玉的名声好吗?

排除一切不可能,剩下的就是真相:王夫人的确相信了晴雯信手拈来、临时编造的一段谎言。
宝玉喜欢漂亮的,晴雯恰好是丫鬟中最漂亮的;晴雯又是贾母派给宝玉的,“便是老太太、太太屋里的猫儿、狗儿,轻易也伤他不得”。有了这些条件,哪怕用脚后跟想想,也不会相信晴雯只是个“看屋子”的吧?可是王夫人就信了。

王夫人年近半百了,晴雯才十六岁;王夫人管理家务多年(王熙凤是在她领导下),晴雯伺候宝玉还不到六年;王夫人出身大家,经多见广,晴雯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是侍候少爷的,清虚观打醮也不能去;她又没有父母,司棋偶然能请假回家,她也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怎么对比下来,也应该是王夫人经验丰富阅历老练吧?

可她就被晴雯轻轻骗过了。这智商也真是没谁了。
作者不说她“蠢物”、“蠢才”或者“心性愚顽”,只说她“木头似的”(贾母语)、“佛爷似的”(探春语),已经是委婉讽刺了。这里又用“天真烂漫”来形容她,真是春秋笔法、皮里阳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