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种工作,AI完全可以取代。”
阿钱还记得自己在银行工作的最后几天,挂断电话,望着一排排忙碌的同事,她心里闪过这个念头。
2017年,她通过校招进入了一家知名银行,担任理财经理,收入稳定,福利完善。但她一直想走,因为工作内容千篇一律,而且做出的成绩,与金融政策、银行福利等“外部因素”挂钩,个人获得的成长很有限。对于电话销售,她不明白,“这种完全能由机器代替的活儿,为什么要人来做?”
2021年,元宇宙的概念正火热。一家AI独角兽公司闯入她的视线,其推广的AI产品,恰好击中阿钱。与其让AI取代自己,不如自己先投身AI。

投递简历后,一切都极为顺利:金融学背景,加上银行从业经历,让阿钱顺利入职,转型为这家AI公司的B端销售,服务的客户依旧是金融行业。只是这一次,她不再推销理财产品,而是用AI赋能客户的业务场景,为一整套方案的制定、落地、调试和验收忙前忙后,有了更多作为空间。
那一年,撬动行业变革的ChatGPT还没问世,很多传统行业还未意识到这场正在酝酿的科技风暴。但像阿钱这样的人,已经看准机会,拿到了这辆时代高速列车的入场券。
只是,这才是第一步。挤上AI浪潮的“快车”后,旅程并不轻松。

跨界拥抱AI
“在地产公司里面跳来跳去,就像是在泰坦尼克号上选头等舱还是选三等舱。”晓明说道。
三年前,在地产行业待了一年半的晓明觉得,自己一个学建筑的怎么可能跳到AI这一行?2022年初,房地产行业寒潮持续,促使晓明做出了裸辞、转型的决定。
认为央企是“铁饭碗”的父母,很长时间不待见他。架不住“一个大男生,天天待在家里没事干”的唠叨,晓明逃到离家约两百公里的一座城市,到一家建筑学作品集机构做辅导老师,一边打工挣钱,一边伺机转行。
2023年初,有关ChatGPT的消息火爆全网,晓明看到了机会。他注意到一家AI数据服务商正在招产品经理,虽然暂时未能搞清数据标注等术语,但梳理完岗位职责后,他发现,这“门槛”或许没那么难跨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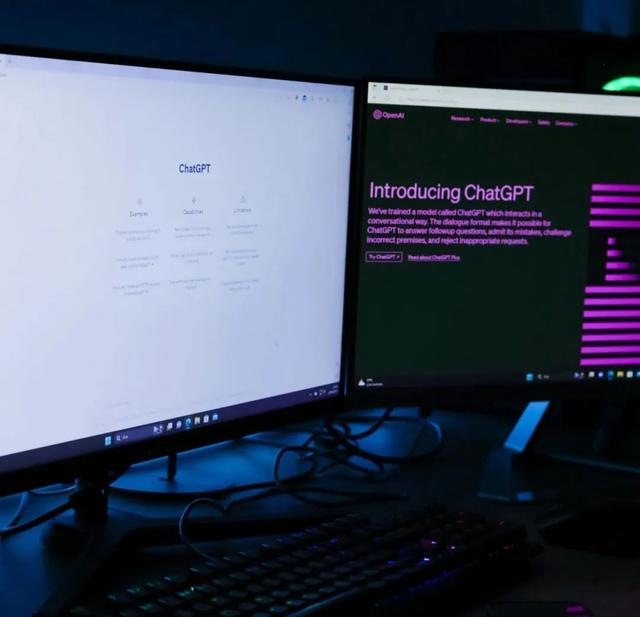
此前,晓明在地产行业做设计管理岗。拿到一块住宅用地后,他通常需要先分析其他“竞品”做了几房、几室、几卫,分析这样的空间结构有什么亮点,思考怎样才能在同类型中做出差异化,挖掘空白领域。完成前期的竞品调研后,则要和设计院讨论这块地的结构安排、施工排期等。推进到住宅的销售阶段时,他又要关注房子卖得怎么样,复盘整个工作环节与销量之间的关系。
类似的思维模式,让晓明对胜任AI产品经理这一岗位有了信心。他解释道,如果把数据比作矿产,这家为算法训练提供数据服务的公司既有储备的矿产,又有铲子的储备。“铲子”是指标注数据所需的工具。
而AI产品经理就是“设计铲子”的人。
在当时,业内几乎没有现成的“设计铲子”人才。即便高薪聘请大厂人员,公司也需要从头开始培训。“便宜”且学习能力强的他对于这家初创公司而言,性价比很高。

《胜券在握》剧照
在这个基础上,晓明面试中又着力“推销”自己的相关技能:他在学建筑时已经掌握3D建模和一些图像绘制软件,对于如何提升工具效率还算熟悉,能够应用在数据标注的工具上;留学的经历,则让他具有不错的英语能力,能够帮助公司顺利出海,拓展国际业务。
回忆起这段面试,晓明将其形容为“捡漏”。他总结自己的转行经验,“底层能力可迁移”。
AI行业并不神秘,需要的仍旧是在垂直领域积累的经验和能力,以及将这份底层能力迁移至AI赛道的眼光和胆魄,几位跨界AI行业的受访者都如此告诉南风窗。
导演专业出身的杜谦也是如此。他原本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创始人,但过去两年,行业状态让他感到失望,“最好的办法是早点去寻求新的出路。”
去年,杜谦关注到与其合作的互联网大厂推出的某AI硬件产品。作为潮玩行家,他察觉到,这款产品的功能仍局限在较为单一的听觉和视觉上,如果能与潮玩相结合,实现“玩具+AI智能硬件”的融合方向,产品应用空间更广,也更有生命力。

AI浪潮下,能与人互动的AI玩偶赢得市场关注
有人建议他可以做这一行,但强技术壁垒让他犹豫。一位经济学专业的朋友告诉他,做这个行业不一定要多了解AI技术、自己下场做开发,更应该做的,是“像产品经理一样,知道现有的技术基础上能做什么产品,同时被用户喜欢”。
他果断“all in”。没有相关技术背景的他选择“换个打法”,从产品端发力,把重心放在AI角色玩具的设计上,例如为其设定独立的声线特征和成长轨迹。他表示,过往在广告行业历练的经验,能够迁移到玩具的产品设计和创意构思上,形成一款有可能比智能音箱“更拟人化”的AI陪伴产品。用户在与其进行语言互动时,既能了解到角色的“人生”,还能通过接入的大模型解答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疑惑。
团队把原本的业务线向AI产品迁移,编导转向角色的故事线设计,制片转战销售渠道。在技术领域的空白,则有杜谦招引新团队入局。他带着新兵老将,把一个个构思逐渐落地。

学一门技术语言
在老本行里修炼的基本功,仅仅是进入AI行业的“敲门砖”。入门后,来自传统行业的跨界者还需要消融行业壁垒,这一历程,宛如非母语者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晓明向南风窗透露,传统的产品经理不太需要懂模型训练,也无需深究数据和模型之间的关系。但他作为AI产品经理,不光对技术和算法要有一定的了解,还要搞清模型表现优劣的原因。
模型表现出色,晓明就得进一步挖掘如何让模型发挥出更大的产品价值;模型表现欠佳,他还得思考如何避免用户产生负面感受,以及琢磨使用哪些提示词,才能让用户更轻松地上手产品,提升用户体验。

入职后,纯建筑出身的晓明开始自学AI专业知识。结合公司提供的学习资料,他优先了解与产品经理工作密切相关的内容,利用下班时间补齐行业知识。比起马上给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晓明选择循序渐进,先向做开发、测试的同事问出正确的问题。
不过,由于不是科班出身,晓明也难免碰壁。当对接的程序员告诉他“不能做”时,他无法判断是当前技术真的无法做到,还是对方嫌麻烦的托词。
被迫学习新知识的还有杜谦。真正涉水“攒局”后,他发现,自己也得产品、技术两手抓。他带上负责产品运营的同事,从成都飞到广东,拜访了玩具工业带的多家工厂,大到了解产品是如何从设计到投产,小到摸清玩具使用什么样的材质、选择什么样的供应商,逐渐建立起新的行业知识体系。
发现自己和技术人员在沟通上有障碍后,杜谦给自己报了个讲C语言代码逻辑的网课,试图理解AI的底层逻辑。
他直言,文科出身的自己学起来确实压力有点大。不过,他知道自己的重点:相比成为一个精通AI技术的专业人才,他更迫切需要的,是清晰掌握AI技术具体能在他的产品里发挥哪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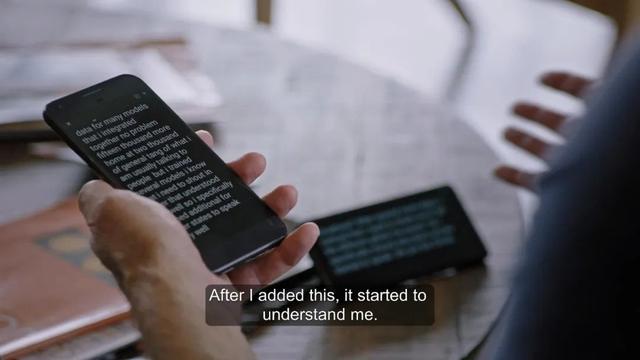
《AI时代》剧照
在销售一线的阿钱,则面对更复杂的认知错位。她要面向客户的具体金融应用场景,推广公司的AI产品。但是,大部分客户也面临来自AI行业的技术语言障碍,“既不是很能明确描绘出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模样,也不知道这样的东西在AI行业里叫作什么”。
DeepSeek爆火后,阿钱还需要面对越来越多超出理性的期待。“有时感觉客户在和我讲科幻电影,实际上我们只能完成他们想要的20%。”
她觉得这样的“客户教育”还“挺好玩”,但对于失望的客户,她得想办法让其愿意花100万买下公司的服务。毕竟,只给对方“构建专属的内部知识库”“让员工迅速查到想要的信息”“优化工作流程”的回答,很难应对 “这100万花得值吗”的思量。
因此,阿钱往往只能在愿意投资的大客户处拿下单子。

逃离“动物园”
阿钱形容,银行外的世界像丛林,想获取什么样的地位皆有可能。但是,没有人能给自己兜底,自己可能被饿死,甚至被咬死。
为什么还要往丛林猛扎呢?因为,她想要逃离一座安全的“动物园”。
“社会对于每个人的容错率非常低,恨不得你第一份工作就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而她不愿意给自己的人生设限,比起安稳,她更享受把一件件事谈成、做成,带给客户价值的同时,自己能力也得到认可的滋味。
往丛林去,义无反顾地离开父母眼中的“铁饭碗”,也是晓明的选择。在过去那家央企背景的地产公司,森严的等级结构,让晓明觉得压抑且心累,“要很小心翼翼去维护好同事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必要的时候,领导讲一个不好笑的笑话,你还得跟着笑一下。”

《前途无量》剧照
无效的加班也让晓明不解。即便手头的工作提前完成,他还是要继续待在工位。如果提前下班,领导会觉得他的工作量不够饱和,或者直接判定他最近不太积极。到了夜晚,“内卷”的同事还会发个诸如“星光不负赶路人”的图片。在晓明眼中,“这很恶心”。
上学时,晓明挺喜欢建筑学专业。在这门专业里,严谨逻辑搭建起的理性框架,交织着人们对空间的感性体验,让他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建筑这个行业糟糕透了。”来到职场,晓明发现,空间设计往往让步于资金的更大化流转。同时,他还要忍受学校外的职场规则。让他有落差感的是,面对初中肄业的工程部老板,科班出身的自己只能乖乖叫声“X总”,而对方往往趾高气扬。
“在这些人的手下工作,我不知道能学到什么。”
而现在,晓明不仅可以和同事、领导开开玩笑,休息时还能约着吃个饭、出去玩。他接触的工作也很新鲜,每天工作完成后,能带给他“明显比昨天有长进”的感觉。行业的反馈周期也大大缩短——此前在地产行业,他负责的项目往往要两三年才能建成,而AI项目每项功能的迭代,都要求两三天实现,这带给他满足感。

《平凡的荣耀》剧照
在上一份工作中理想被碾碎的,还有杜谦。去年许多甲方的预算收缩,再加上新人涌入、AI冲击,他们的营收比前年“至少缩水一半”。更“劝退”的是,做不了自己想要的作品,他们认为更好的表达、更艺术的表现,并不一定符合甲方的审美。妥协成为常态,“被消耗”的感受与日俱增。他告诉南风窗,“我不想做广告行业的守墓人。”
与其一辈子温水煮青蛙,逐渐走向平庸,杜谦更愿意去赌一把。对于这场all in AI的转型,他开玩笑说是在“赌命”。目前,团队已完成产品的技术链路部分,响应速度、角色故事等还在优化。“产品正式上线销售之前,所有的东西只能来自我们的揣测和预期。”
但杜谦确定的是,他久违的热情正在这条新赛道上燃烧。

登上诺亚方舟之后
2022年以来,ChatGPT等相继问世,“AI+”浪潮席卷至金融、医疗等多个行业,也催生了AI产品经理、AI训练师、数据标注员等新兴职业。
年轻的AI行业如同一艘诺亚方舟,打捞起迷茫的职场人。但旷野生机的另一面,是混沌生态里的不确定性。
在成功帮助几名建筑专业学生转行AI后,晓明发现,社交平台上询问自己跨行经验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想知道,AI产品经理能否成为一个好出口。但是,晓明忍不住吐槽,这更像是平台算法和卖课机构人为制造的焦虑。

《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剧照
“说白了就是贩卖焦虑,特别是针对建筑生的转行需求。最后搞得人会想,‘全世界都在转AI产品经理,为什么我还没转成?’本质上这是一种幸存者偏差。”
他说,自己经历了三个月的专业知识补课,才在新岗位上“不虚”。这时间并不算夸张,“如果你也在地产行业很痛苦,很焦虑,一年找不到工作,(转行AI后)你感觉你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求生的本能会激发出你的学习潜力。”
作为过来人,晓明想劝后来者理智决策,“想清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你不能因为说自己在这行干得不爽就想转,那你确定到另一个行业后,就能干得舒服吗?”
这两年,晓明手下的部门也陆陆续续招到一些来自各个专业的人。在确认新人基本的沟通、协调、表达、逻辑思维能力过关后,他最关心的,还是他们能否在三个月的培训和学习里迅速上手并有所产出。
“这个行业日新月异,如果只是守着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很容易被淘汰。”他说。

眼下,杜谦正处于“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状态。他原计划产品在元旦上线,但由于在技术路径走了弯路,进度条无奈拉长。AI行业诞生过许多一鸣惊人的神话,也并不缺少粉身碎骨的人。眼下最让他忐忑的,是产品上线后的反馈,毕竟这是全力倾注后,他们“进入这个行业的标志”。
不过即使失败,杜谦也不愿意重新回到自己的老本行。当下,他对AI硬件市场充满信心,并不缺少从头再来的勇气,“至少,我要做一只在风口里的猪。”。
他给南风窗发来一份标题为《32岁,我和理想签了一份生死状》的心路历程,告诉记者,“我的人生理想,就是想做一些了不起的大事情。过了30岁,发现,其实(人生)真的在不断地趋向于平凡普通,所以,转行对我来说,也算是一次冒险尝试。”
现在,AI,就是杜谦认为的实现理想最好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