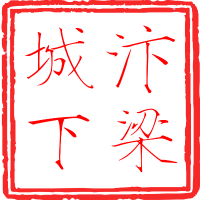天大亮的时候,红旗已经插在龙亭上空。
天也亮了,枪声也静了下来开门该干啥干啥,听父亲讲,救人不成,失了命,在我们家西边不远有一个小门楼有一个伤兵,浑身是血分辨不出是国军还是八路,看到我父亲指着自己的嘴水水要水喝,父亲飞快的跑到家里面给他端一大碗水,伤兵大口二口一气把水喝完,父親回到家里,爷爷问你干嘛去了?父亲讲有一伤兵要水喝,爷爷讲;你给他了吗?我给他送水去了,爷爷说坏了坏了,伤兵是不能喝水的,应该喝面汤,爷爷说人呢?父亲指了指在那,爷爷和父親再见到伤兵时,伤兵歪着头没气了,从那以后,父亲知道伤兵流血过多,要喝面汤不能喝水,有战争就会有牺牲,战争也不像电影里那样,双方开战,谁都不愿意伤害老百姓?因为他们要吃喝拉撒睡,依靠的还是老百姓,老百姓是他们的后勤保障,兵是打扫战场,老百姓是打扫卫生,二次解放开封,我们家的门板挂彩了,三八大盖枪眼一个,手榴弹皮有四公分左右长,这个我记忆最深,我们从宋门里搬家,搬到西门里南仁义胡同,我三哥是木工用门板做了一个方桌,要找现在还能找到历史的见证物。
开封第二次解放,从此没有发生过战争,开封回到了人民的手中,爷爷也老了,眼睛不好使,耳朵又聋,父亲是长子承担家里的一切, 听父亲讲他结过两次婚,是让媒婆骗婚了,相亲见面的女人和娶到家里的不是一个女人,最后他承认了,见面的是他姐姐,因为他有劳病结婚冲喜会好的,看病也没有少花钱,加上解放开封打仗,枪声炮声,农村的女孩子哪见过这阵势?连惊带吓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好歹没有留下孩子,不然的话,我们的家庭就会多一个父亲,不一个母亲同胞。
后来我的父亲又娶了我的母亲,听父亲讲,我前面有一个大姐,长的特别漂亮,非常的聪明,不到三岁,夭折了,用迷信来说,她不能成人。
淮海战役的胜利结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一个旧的世界即将过去,一个新的世界即将诞生,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军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宜江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那一年的春天来的特别早,朱家馍铺还像往常一样 , 开门营业,伙计们,忙忙碌碌,和面的和面,揉馍的揉馍,烧火的烧火,杠子压面,擀出来的大刀面就是好吃,这时候从远处传来了马蹄声,由远而近, 到了朱家镆铺停了下来,三个当兵的,一个军官两个警卫员挎着双枪,问;朱掌柜在吗,爷爷的年龄大了,耳朵又聋,眼又花,就问谁呀?当官的就说朱长贵,你不认识我了吗?爷爷手扶着门板看了半天,摇摇头说眼花了,不好使了,认不准,这时候军官就对爷爷说,你把身子转过去,就听到军官大声吆喝着,五香茶鸡蛋,这时候爷爷说听出来了,听出来了,你就是在桥头卖茶鸡蛋那个地下党,你主要负责的是日本鬼子进出的车辆和军用物资的情报,两人紧紧的搂着手拥抱在一起,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最后也不知道你到哪儿去了,军官说在当时那个情况是没有办法打招呼的,说走就走,任何人不能告诉要到哪去,全国很快都要解放了往后就是咱们穷苦老百姓的天下了,军官看了看我父亲,用手指着说这是你的大儿子,爷爷说是啊!然后说他都有孩子了吧?朱掌柜也有孙子了吧?有了,有了,那时我们走的时候他还没有三八大盖高,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几年就过去了,全国都要解放了,让他跟我们走吧,参加革命将来以后,像马道街,书店街的楼房将来以后都是我们的,我们都可以住的,听父亲讲,他想跟着解放军走,参加革命,全国都快解放了,打仗也少了,爷爷说不行,不行,我老了,眼睛耳朵不好使唤家里离不开她,要参加革命,上次在河南饭店解放军招兵,就让他参军走了,我听父亲讲过,当时在开封大金台宾馆,国军在招海军,在河南饭店解放军招步兵,国共两党互不干涉各招各的,这是真事儿,我见过大金台宾馆,国民党招海军广告黑白照片,有历史的见证。
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小的时候也算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没上过上几天私学老是和先生(现在的教师)吵架,先生批评他,他就让先生还欠我们家的镆头钱,先生劝学让我父亲回家帮爷爷干活,父亲的小名叫孬蛋,听名字都不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听父亲讲我的叔叔有文化他愿意去参加革命,跟着他们走了叔叔,中间回来过,听父亲讲他不打算再回开封了,家里的财产归父亲一个人,所有临走时,叔叔看家里情况怎么样?能不能给他点钱?家里所有的财产归父亲一个人所有,包括赡养爷爷奶奶,养老送终有父亲一个人承担,父亲在家务工,用他的臂膀支撑着一个朱氏家族,叔叔参加革命,我见过叔叔的黑白集体照片,我长大以后我知道叔叔参加工作,任郑州铁路总局人事处,处长,他的家我曾经去过,他管理人事的权利东到徐州车站,往西到山西太原,曾经,和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后任铁道部,部长他是叔叔的老首长,曾在文革期间有句口号万里不倒,火车不跑,叔叔任人事处处长,一直到退休,在当时的那样的老干部还是比较清正廉洁的,我们姊妹七个,叔叔没有给一个安排在铁路上工作,听我母亲讲,曾经去找过叔叔,我的婶婶说房子是国家的,家具是国家的,人是国家,意思就是叔叔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国家的,叔叔从小参加革命离家出走,从此以后,母亲再也没有去过叔叔的家,母亲没有文化和有文化的人在一起说话很难沟通。

解放后,父亲也曾经讲过他自己的故事,叔叔参加革命走了,姑姑也到出嫁的年龄了,听父亲讲,姑姑嫁给一个开布行老板的儿子,姑姑在结婚的时候,老朱家也不甘示弱,听母亲讲姑姑结婚出阁的那天,出嫁陪嫁的嫁妆摆了几十米的长,奶奶和爷爷年龄逐渐的大了,家里的重担全部由父亲一人承担,擀面条也引进了半自动化,最原始的手摇面条机两只胳膊不停地摇,带动压面滚子和切面条刀,解放了不能再用伙计干活了,当时听父亲讲政府说那叫剥削按朱家传统老规矩每人给他们另立一摊生意,各干自己的事业,
新中国的诞生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日子,听说国家有政策,不让个人做生意,那叫走资本主义路线,父亲也参加了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空降师,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帮助我们组建的,现在;在南郊还有历史的见证物,伞塔他专门训练伞兵跳伞用的,是苏联帮我国建造。
因为我家开的是镆铺,父亲到部队炊事班和苏联老大哥学烤面包,虽然全国解放了,还有国民党反动派土匪的残余势力妄想颠覆新中国,盼返国民党反攻大陆,父亲随部队开拔到湖北省薛家岛参加剿匪,听父亲讲新中国的刚刚成立政权正在巩固,土匪猖狂欲绝,刚到湖北,经常夜里解放军的岗哨被杀和失踪,最后他们想出了好办法,在军营里面养狗,狗是最灵敏的动物,效忠主人,养狗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炊事班父亲他们身上,父亲他们换防回来之后,不像现在有火车,有飞机,他们坐的全是军用卡车从湖北到河南,他们走了几天几夜,回到开封有一天早上,父亲看到在营区的门口有几条狗,父亲仔细一看,这是在湖北养的狗,浑身是泥,狗是跑不过汽车轮子,但是它对主人的忠诚,凭着他的嗅觉能坚持不懈,跑了几天几夜跑到开封,确实是让人感动,从此开封空降师大院儿里又多了几条狗,他们也曾经为剿匪立下过功劳,小时候听到老人说过这样的话,毛记千,狗记万,小鸡还记二里半,真的是这样。
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父亲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步兵学校工作,第八步兵学校的原址在开封河南省第一监狱,有两排灰砖灰瓦楼房,现在己经成为文物,那是历史的见证,现在还在己经维修整修过了。新的第八步兵学校在西郊油库那个地方。
父亲人生的转变,父亲在新的第八步兵学校开封西郊,在哪儿工作,因为一场痢疾改变了父亲的命运,
我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讲,自从嫁到了你们朱家没享过一天清福,母亲说的非常的对,我们姊妹七个挨得都比较近,父亲参加工作,经常不在家,家里还有生意,压面条,上面有爷爷奶奶,下面还有哥哥,压面条是很累很累的工作,全部都是靠体力劳动,虽然有一个压面条机是半机械化,全靠手摇,夏季穿的衣服四个角滴汗珠,母亲对我印象最深的,她穿的衣服都是老式大襟的衣服,现在的老太太穿的都不多见,确实母亲的命苦,自从嫁到朱家生儿育女,做家务,母亲去世的也早,我上初中的时候,母亲50多岁就走了,为我们朱家付出了卓越的贡献,我对母亲的感情还是比较深的,母亲病重,从医院接回家,就等我们家的老舅,能见上一面。老舅,上午来和母亲见了一面,下午老舅就回杞县老家,可能他不想亲眼看到自己的姐姐,就这样走了,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穿好衣服,要放在地下,我记得最清楚母亲一个人躺在地下,我就躺在母亲的身边,手拉着母亲的手,等到天亮的时候,我醒了,母亲的手冰凉冰凉,母亲真的走了走了,我坐在母亲的身边,只有看着母亲那苍白的脸,眼泪就流了出来当时年龄小,脑子想的简单,就这样送走母亲,我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把我们姊妹几个养大成人,大哥二哥成家立业,它就这样悄悄的走了,伟大的母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老舅就是老老实实勤奋能干的一个农民,用现在的话说非常实在,我小的时候记得老舅从杞县高阳拉着一辆两轮架子车,白菜,萝卜,红薯,南瓜,到开封送到我们家。当时兄妹子妹们多,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太好,在当时那个情况,全国各家庭都一样,没有什么贫富差距,国家主席最高生活标准才四菜一汤,等到老舅回杞县的时候,父亲从卧龙街有一个豆腐社,制作豆腐,剩下的那个渣叫豆腐渣,找关系托熟人,买一车让老舅拉回杞县老家,上笼蒸一蒸人也可以吃,剩下的喂牲畜,在当时那个社会基本上生活条件都一样,农村要比市里面条件更差一点,还是有城乡差别的,母亲去世后,老舅不断地往开封来,每次来捎农副产品,也就是农村那几样东西,红薯,白菜,萝卜,南瓜。
作者:朱学旗,开封市龙亭区人。供职于开封市曲剧院,开封市明史研究会秘书长。长期创作以纪实文学和研究明史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