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菲因·赛里格的纪录片《美丽噤声》里,多位女演员讲述她们对电影行业厌女传统的体会,例如,银幕对女性友谊的禁止。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演过让其他女性感到温暖的角色吗?”马洛里·米利特-琼斯(纪录片《三种生活》的女演员)说:“我演过一个让别的女人都感到可怕的女性。” 她们说:“在很多电影里,姐妹这个词相当于女性敌对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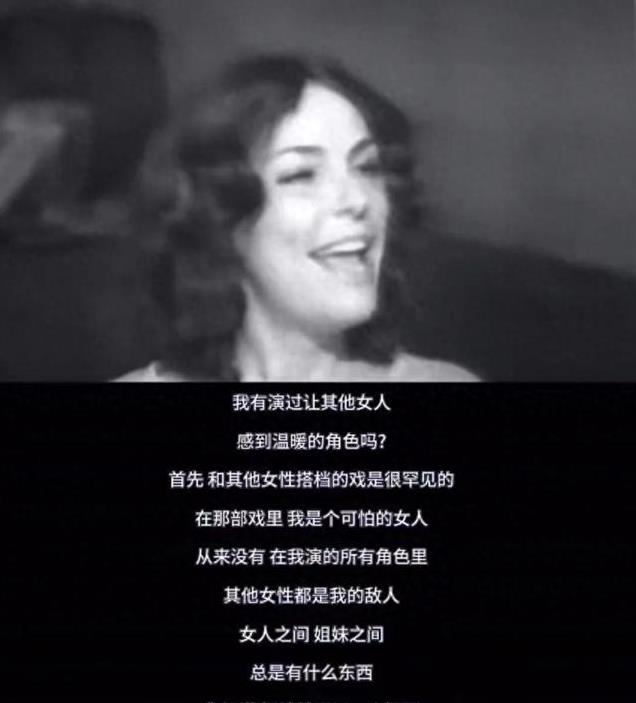
《美丽噤声》剧照
德菲因问朱丽叶·贝尔托:“除了《塞琳和朱莉出航记》,你还演过什么关于女性友谊的角色吗?”贝尔托说没有,她曾经参演《萨拉森》,希望电影能展现女作家萨拉森反叛的一面,以及她和别的女性的关系,遭到了片方的否决,“我想给萨拉森的死复仇,结果这部电影是她的第二次死亡。” 在影片的另一处采访中,简·方达提到一部她参演的女性友谊电影《朱莉亚》,女知识分子之间的友谊在当时很少见,而很多媒体所不能理解的是,这部电影无关女人和女人的爱情,而仅仅是女人和女人的相爱。

《美丽噤声》剧照
《美丽噤声》对女性的听和看既明确又不简单,我们一边听她们的声音,一边跟随镜头推拉来注视她们的肖像,在那些特写和中景里,她们以自身为自己和同胞画像。而因为熟知她们身负的电影史,所以你不只是在听玛丽亚·施耐德或路易斯·弗莱彻或的心声,你也在感知《巴黎最后的探戈》或《飞越疯人院》里的那个她的真实另一面。因此,德菲因在一片恐惧女性相互扶持的土壤之上,建立了女性电影人之间的共识,更多的人看见了友谊存在的事实。

《美丽噤声》剧照
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女性们在银幕上总是被成为“孤独的”或“可怕的”?或许基于艺术压缩时空的特质,如将漫长的生涯压缩为一本书的厚度,传统故事家考虑到情节性,经常选择将人生压缩给男女爱情。而此类关系通常排斥更多的友谊,如果有另外的男性女性,为了故事的密度,通常会成为男女主角的敌对者。以男性为主的传统艺术家群体也能创造浪漫的男性友谊,可他们似乎想不到两个女人做朋友的模样,他们认为女性朋友坐在一块经常什么都不干。
然而女性和女性的结盟往往呈现更生动的人物关系。甚至仅存在两个女人的画面,即使什么都不干,也是值得拍摄的,女性组合具有一些更生动的影像化力量。
我们会发现,很多更强调人物独立性的电影,经常在男女关系为核心的情节框架下,挖掘女性和女性的独立组合,因为女性影像本身的存在感总是能超过情节的限制:我们或许忘了《上海快车》的男主角是谁,就如我们不记得每一部黛德丽电影的男主角,但是谁能忘记她亲吻过哪些女孩,以及她和黄柳霜之间那侠情而旖旎的默契?而1925年刘别谦的默片《少奶奶的扇子》更是一部早期的双姝电影,而不是母女电影。因为王尔德的原著已经塑造了艾琳女士的形象,她是美丽的、神秘的“女士”,而不是苦情的“温夫人的妈妈”,两位女主角的仪表很相当,在一个画面里,她们各抄一条小路向对方走去,各有各的走路风姿,然后面对面站立,看不出年纪的差距。而刘别谦从一开始就透露了艾琳女士的真实身份,因此影片的主线始终是两个女性人物间的张力,男女感情反而是幽默的佐料。《少奶奶的扇子》产生了一个启迪,或许相互误会的女人本都是同根生?

《少奶奶的扇子》剧照
到了有声片诞生初期,刘别谦的歌舞片《驸马艳史》也是双姝,你以为克劳黛·考尔白是来找男主角“驸马”的,谁知她是来找玛利亚姆·霍普金斯的。她们都打了对方一下,霍普金斯拿出两块手帕,于是双女主竟分享起了对于男主的认知,考尔白浏览起霍普金斯的琴谱和服饰,她发觉这女孩根本还没发育,于是带她弹钢琴,弹着弹着教会了她爵士乐,理解了爵士乐的霍普金斯烧掉了原来老土的内裤,扔掉了那些小公主裙子,女孩的衣柜焕然,国家就走进了现代。

《驸马艳史》剧照
为什么刘别谦善于将情敌变成好友,乃是因为他的电影不忽略人物的个性,而非仅仅关注故事的模型。所有成功的好莱坞的类型片,从明星到配角都是独立的人物。霍克斯的《绅士爱美人》片场照,梦露在喝一瓶可口可乐,罗塞尔拿着镜子在补妆,好朋友就是坐在一起各干各的——霍克斯的电影几乎像一个豪华版的侯麦画面。

《绅士爱美人》片场照
在《绅士爱美人》里,玛丽莲·梦露与简·罗塞尔是一对追求截然相反的挚友。当梦露被诬告,罗塞尔直接顶替她去了法庭,顶着她的金发登场,也唱了那首《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一个人能自愿饰演另一个人,因为女孩从来不以自己的好友为耻,相对于现在市场对梦露的诸多同情式解读,这部梦露自己的作品却证明了她不需要被同情。

《绅士爱美人》剧照
梦露和罗塞尔在一块好开怀,在私家侦探的酒中偷下安眠药,梦露调酒的动作带着生动的节奏,歌舞片的乐感不仅来自于歌舞,而是日常动作的乐律。一个漂亮的动作能激活一样物品,一系列美丽动作能生成一个场景,如游轮宴会,双女主走下台阶来,罗塞尔笑笑、梦露微启唇,她们的神情与肢体、与衣服、与头发和鸣,大提琴手因此拉错了琴弦,而她们以自己的肢体协奏着更完美的乐章。霍克斯的景别多为中景,画面里有她也有她,这就是一种健朗的平衡,甚至群演们也在大明星旁边清晰可见,于是本片的结尾完成了真理的定音——镜头对准梦露和罗塞尔,全景推近到中景,原来男女婚礼乃是对女女友谊的嘉奖,影像说了算。

《绅士爱美人》剧照
影像到底有多说了算?日本电影里常有女孩子模仿梦露,甚至荒谬得像《晚菊》的望月优子。她和另一位女演员饰演两个年老的艺妓,站在天桥上,一个送别了儿子,一个送别了女儿。这时有个时髦女子经过,望月优子就说:“看,那是梦露走路的姿势对吗?”我们发现那位路人的姿态真的像《热情如火》里的梦露。她说:“我也可以”,就很滑稽地模仿起来,于是她们俩哈哈大笑,相携着出画。这是姐妹对时间的共同感怀,而望月优子将自己制造为好笑的影像,克制了悲哀,唤起友谊,在需要勇于生活的时刻,我们的女性友人激发了走而非停留的动力。

《晚菊》剧照
1966年的捷克电影《雏菊》,像是《绅士爱美人》的延伸,或许与之互为反面。《绅士爱美人》豪华而克制,玩转法庭也不拆人家的台,而维拉·希蒂洛娃镜头下的双女主则太混乱了,她们很穷,继而迅速想到社会的堕落,于是到处骗吃,敲那些有钱老男人的竹杠、再将他们送上火车,她们到处漂流,后来潜入了陌生豪宅。
《雏菊》是部形象化的电影,照理说一个故事有太多饮食,你就会记不清每一种具体的吃的,可是我们就是能记得这两个女孩玩过的每一样吃的喝的,啤酒泡泡、牛肉塔塔、奶油蛋糕,她们拿叉子叉着烤香肠、鸡蛋甚至对方的身体,还把杂志上的牛排剪下来吃掉。

《雏菊》剧照
玩乐不仅是贪婪的食欲,而是对餐桌礼仪的破坏欲,从喝牛奶、喝脏裙子开始。有时候屋子里满是食物狼藉,反而像当代摄影,因为当代摄影师经常将古典画作翻拍成更现代空虚的版本。更有一场时装秀,她们披着窗帘形若圣女地在餐桌上踩来踩去。《雏菊》是一部时尚盛典,她们为自己缝制的衣服都非常漂亮,只因为是女孩,所以袭击有俏皮的外表,只因为有两个女孩,所以画面不会过于个人中心。影片是有很多空虚时刻,然而与男性中心的空虚相比,两个女孩的空虚能打乱很多静态逻辑,或许空间仍是静止的,但她们怎么也停不下来。

《雏菊》剧照
六至七十年代的法国,电影和女性文学不断聚合,而与此同时,基于男女关系的创作走向了瓶颈,1973年,厄斯塔什的《母亲与娼妓》标志了旧新浪潮的终结。旧新浪潮的创造性组合是“三人行”,相比传统的一男一女,更喜欢搞一女两男、一男两女,直到1973年,大家终于搞不动了,《母亲与娼妓》描述的就是“无尽的无聊”。然而法国新浪潮没有什么既定的逻辑,转眼1974年,里维特的《塞琳和朱莉出航记》就作为“新”新浪潮而来。这一新新浪潮真可称为“女新浪潮”,因为取代“三人行”的是“双姝”,这种关系重新规定了女孩子在一块儿能做什么,因而带来了更活泼的想象力。

《塞琳和朱莉出航记》剧照
女新浪潮的法国是一个魔力地带,因此《塞琳和朱莉出航记》是一部童年电影,侯麦的《双姝奇缘》是一部童话。《塞琳和朱莉》开头的十多分钟没有一句台词:朱莉在椅子上看魔法书,抬头看见一只猫,接着塞琳就路过,边走边掉东西,于是她们展开了一番追逐;在《双姝奇缘》中,米拉贝和蕾妮特在郊区的小路上不期而遇,蕾妮特修补了米拉贝爆掉的自行车胎。

《双姝奇缘》剧照
塞琳和朱莉这对陌生人,就在相互追逐时成了认识已久的朋友,第一次有一部电影能随时改写自己的剧本,而她们的演员也成了好友。好朋友之间是有很多巧合,朱莉刚在厨房里调着血腥玛丽,塞琳就在客厅说:“我超级想喝血腥玛丽!” 画面迅速移去,朱莉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杯子啪地掉到地上,她们交换了一个奥秘般的对视。继而又恢复正常,塞琳喝到满满一杯的血腥玛丽。

《塞琳和朱莉出航记》剧照
里维特的电影产生丰富的蒙太奇,打碎的杯子像是个反应蒙太奇,魔法师应该维持对巧合的敏感,眼睛一闪,耳朵一动,一个灵性的时刻,联结着另一个神奇的经验。朱莉对于那神秘空间的想起,则受到了塞琳魔术表演的启发,她们决心将困在成人剧场里的小女孩救出来,她们的确用游戏——艺术的起源说之一——那“山猫的眼睛,木脑瓜”的咒语,吸引了另一个时间维度里的小女的注意,这就是本片的美丽之处。罗宾·伍德在他的影评指出,女性运动竟然可以是娱乐化、而非苦大仇深的,塞琳和朱莉的表演讲究自然的娱乐,反之,鬼屋中人物的表演则是调度的奴隶。在塞琳和朱莉的追剧方式里,有一代女观众对于雌性竞争式电影的反抗,而且这两位女观众更有主动去修改那部年代剧的冒险精神,她们轻盈的责任心不输给任何一场男性丛林竞赛。

《塞琳和朱莉出航记》
而《双姝奇缘》的虚构特征更加隐匿,因为侯麦的场景看上去无比写实,那些建立情谊的画面:新鲜的草莓、田野里的风、配着盐和芝士吃的小红萝卜、“蓝色时刻”,都是绝对真实的大自然,如同蕾妮特的画作。乡间有乡间的虚构,城市里也有,虚构可以令我们与矛盾和解,蕾妮特在抨击米拉贝帮助小偷以后,有一天在火车站给女骗子骗光了钱。那是很好笑的全景,蕾妮特在问陌生人有没有零钱,她身后来了个男子也在问别人讨钱,谁是真没钱、谁或许是来坑蒙的,反正看起来都一样,那男的还拿走了她仅有的一块钱!总算找到女骗子一番说教,可对方一哭,她也心软了,也许这正是来自米拉贝的惩罚。

《双姝奇缘》剧照
米拉贝和蕾妮特的矛盾与平衡里,有一份美妙的道德,当蕾妮特滔滔不绝地辩护自己的画作,然后打赌说“我明天一句话都不会说”,第二天米拉贝就在画廊用“艺术家应该沉默”的理论反击,但也帮蕾妮特卖出了自己的作品,赢得了继续住在巴黎的票券。那是影史上最像模像样的一场赌,不是煽情地赌性命和财产,而是赌“即便我明天要去谈生意,我都不说话”,自尊就这么简单。

《双姝奇缘》剧照
在这两部电影里,爱情都被边缘化了,因为女性电影可以没有爱情。朱莉那打着怀旧牌的表哥被塞琳吓跑了,鬼屋里面的“爱情”被双女主剥夺了版权,她们自己成为了新浪潮导演。里维特的确将演员朱丽叶·贝尔托和多米尼克·拉布里埃以及鬼屋女性们的名字也放在编剧一栏,在《美丽噤声》里,朱丽叶·贝尔托甚至谈到自己和多米尼克·拉布里埃对于《塞琳和朱莉出航记》的自由发挥创作,因此她们判断里维特其实是个女性而非男性创作者。
《双姝奇缘》更不需要男主角。浪漫的巴黎男都如此好笑,还不如乡下的农民伯伯能好好说话,不过好笑的影像都不令人厌烦,电影的结尾竟然是画廊老板的一句“五千法郎。” 这句话延续了生活的电影,影片放完了,美丽的塞纳河仍在继续流淌着。在侯麦的其它电影中,经常是两个女孩很浪漫地认识,再一块儿去玩玩男的,男性当然是可以被选来选去的。
侯麦和里维特均觉得自己的心里住着个少女,瓦尔达则是个真正的的女性,她的《一个唱,一个不唱》是场漫长的妇女运动。影片开头是单张单张的女性肖像,来自一家照相馆,继而女性时代到来,瓦尔达的社群组成了更坎坷却乐天的妇女报。

《一个唱,一个不唱》剧照
一篇纪实跟踪:1962年,两个女孩——玻木和续桑努。前者在逛照相馆时认出了后者的照片,在二人重逢后,玻木成了续桑努贫困生活的小救星。十年后她们因妇女运动再重逢,续桑努带着两个孩子,玻木带着伴侣,大家都成了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并肩走过一幅幅写着时代口号的海报。她们开始给对方写信,多么有斗志的六七十年代,人说起自己的成长,不是种停下来怀旧的幻觉,关于记忆的画面是切实生活的影像,一个女人怎么找到工作,一个女歌手在哪里创作,和她们对此的记述,都有最鲜活的同期声和独白。由于书写的习惯,她们即使在不书写的时候,也像是在一边复述着自己的此刻、此刻的自己,语言辅助着切实的行动,而行动的战斗力更胜于语言载体,每一封信都绝对简洁,因为她们能读出对方文字里的言语,影像之间有影像,声音内部有声音。

《一个唱,一个不唱》剧照
影片的每个场景,尤其是社会运动场面,都像照片一样朴素。一个世纪的女性在法庭外示威,为了一位女孩玛丽的堕胎权,那些手写的标语倒映在法庭门口的玻璃上,纷纷举在街头,每个字都好清晰。而口号声如清唱般清贫,她们喊着:“审判做过人流的我们吧!” 路边和楼上都有零星的围观者,瓦尔达像新闻般全面,没有自我夸大的时刻。蓝眼睛的民谣歌手玻木,穿着彩色衣服站到台阶上唱:“无论是处女还是卖淫女,我们欢迎更多的玛丽!”电影摄影机更成了现场的摄影机,这几台朴素的机器,以自己有限的推进能力看向此焦点。续桑努则和身边的人说这个歌手是她的老朋友,她们因此重逢。

《一个唱,一个不唱》剧照
没有瓦尔达,新浪潮会损失多少地气?我们能基于这样的场面想到五月风暴的真实场景,女人们在社会运动里的真模样,艺术是如此在复述历史。没有独裁叙事,谁都时髦而勇敢。
“确实她们迥然不同,但唱歌的人和不唱歌的人却很像,两人都为女人的幸福做了战斗,乐天的战斗真好。”这是放在结尾的话,镜头依次注目于这部电影里主要的人们,瓦尔达介绍着他们每一位的近况,连续的肖像组成一张合影,因为摄影是流动的照相。电影史又回到《绅士爱美人》的构架,在这合影里续桑努从丈夫身边走到玻木身边,友谊始终是电影的核心,接着镜头又被交给了下一代的女孩,而延续这一切的自然环境,是大家身后的小河。
随着女性运动,法国电影始终不绝地从双姝结构里发现生命,如2014年的《双塔》和17年的《七月物语》。《双塔》里的人际关系像色彩一样丰富,女人们穿着缤纷的衣服自由组合,两个女主角以及无论哪个年龄段的女性都有神秘感,一个黑人小姑娘被妈妈的朋友们打扮成性感女郎,几个黑人小姑娘成为跳舞女王。吉约姆·布哈克像是侯麦的继承者,《七月物语》第一部分是个度假故事,你以为女生在旅途中重色轻友,作为平衡,各自都获得了奇遇,可旅程的结尾仍是火车上的双姝。夏日电影能从小世界里发现乐趣,鲜红和明黄的色彩、水纹和树林、适合某个场景的音乐,这些事物决定了影片的简洁,就像女生之间的矛盾,总是能快来快去。

《双塔》剧照
别的地区如香港和日本也时不时成为双姝、三姝之都,阿根廷马里亚诺·利纳斯的《花》则是四姝,来自Piel de Lava剧团的四位女主演,演绎了涵盖各种类型片、神秘的无目的影像、乃至纪录片和实验影像在内的一本书,这是永无止境的独立创作。或者像洪尚秀的《克莱尔的相机》:人类能够以艺术的方式相处——如克莱尔的再一次观看理论——是生活死循环的解开,这个机会被交给了两位女演员。艺术的活力从困住它的“圈子”里挣脱,奔回它本身的纯粹,在克莱尔不分场合拍照片时、万熙哼起她的歌声时,电影不再被社群的信息挟持,女人也有更多的事可以做,就像散步总是能走向更有趣的地带。

《克莱尔的相机》剧照
这些年来,由于男性大量占据市场,以及商业模式对女观众的错误预估,那些人真的相信只要给一些能够代入负面情绪的雌性竞争的剧情就可以了,姐妹们的友谊总是少见,但我们始终更健康地存在。如瓦尔达所说:“战斗很不容易吧,那会是很单纯很明快的吧。”拍电影看电影,本身就是友谊的继续,而战斗如河流,每滴河水都有自己的运动不会呆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