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华,这颗黄泛平原上的明珠,自汉高祖二年(前205年)初露锋芒,便与沙颍河的波涛共生共荣。彼时,汉高祖刘邦于荥阳大破楚军,旋即分置长平、西华二县。想当年,此地春秋时期为宋华氏地,因其族甚大居住宽广,乃分东西,东称东华,西称西华。此地位于华氏住地的西部,故名西华。长平邑的阡陌间,应是炊烟袅袅、车马喧阗,而西华县治的青砖灰瓦下,或藏有贾鲁河畔的渔樵问答。隋唐之际,西华历经更名,从柳城、鸿沟到箕城,从基城、武城复归西华,恰似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在历史长河中洗尽铅华。贞观年间,太宗皇帝一纸诏书,竟将西华并入了宛丘县,令多少西华人扼腕叹息?然则,景云元年(710年)的复置,又似春风吹绿江南岸,重续了西华大地上的人文血脉。

宋元交替的乱世中,西华如一叶扁舟,随波逐流于梁、唐、晋、汉、周五代政权之间。金人南下时,这里或成烽火连天的边塞,而元末并入清水县,则是中原文明在战火中的又一次涅槃。明初移民迁徙的号角声中,西华的田野上又添了晋中、苏南、皖北的乡音,正如《文王》一篇所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陈州升为府治,西华自此隶属府城,恰似世家子弟入京赶考,虽离故土,却得风气之先。彼时,县衙前的石狮子尚在,而书院里的《四书集注》已翻出毛边,士子们或论朱陆异同,或谈农桑技艺,倒比京城的翰林院多了几分地气。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杜鸿宾、刘盼遂纂修的《西华县志》,恰似一面铜镜,映照出乱世中的文化坚守。书中详录逍遥镇、西夏亭、女娲城遗址的沧桑,字里行间既有“国破山河在”的悲怆,亦有“雾收日光新”的期许。

1938年黄河改道,“百里不见炊烟起,唯有飞沙扑空城”,西华由中原乐土变成了人间地狱。十年后,穆青经行此地,写到,“特别是在风沙弥漫的黄泛区,更是一幅人间惨相的图画。那里像塞外的沙漠一样,一片黄沙,几乎是寸草不生。过去被黄河水淹没的村镇,至今仍可以看到埋在黄沙中间的个别楼房的屋脊。许多无家可归的居民,如今以芦席帐篷为屋,聚集一起熬着痛苦的岁月。”这里一幅幅人间惨相,直到黄泛区农场成立。苏联援助的“东方红”拖拉机轰鸣着撕开荒沙的沉默,路岩岭、马伊林等第一代垦荒者用草绳捆着裤脚,在齐腰深的盐碱地里插下第一株麦苗。彼时,沙颍河畔的芦苇仍挂着日军轰炸的弹片,而拖拉机的履带声却让沉睡的土地苏醒。

1964年深秋,上甘岭战役英雄王近山中将悄然现身农场。这位身着褪色军装的副场长,白天与职工共扛锄头,晚上在煤油灯下研究土壤改良。1969年夏,中央党校千余名教职工迁至西华,将河南农大校舍改造成“五七干校”。朱镕基、李岚清等日后的国家栋梁,曾在此赤脚扶犁,却也在煤油灯下写就《论农业机械化》等论文。如今,当年用过的脱粒机,齿轮间仿佛还留着“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余温。

新世纪的风吹过农场,昔日的拖拉机群已换成无人驾驶的智能农机,种子公司的实验室里,基因编辑的玉米苗正破土而出。春日踏青,但见麦苗青青、菜花黄黄,三月底的颍河两岸,仿佛被谁以丹青泼染:红云般的桃花灼灼其华,金黄的油菜花如碎金洒落,青青麦苗在微风中摇曳生姿,恰似《桃花源记》中“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现代演绎。西华黄桥乡的万亩桃园,自2005年首届桃花节启幕,已化作豫东大地的春日盛宴。

若说桃花是西华的胭脂,逍遥镇的胡辣汤便是其骨子里的烈酒。这碗汤的传奇,可追溯至北宋末年的御膳房。徽宗朝的赵姓御厨,将少林“醒酒汤”与武当“消食茶”合二为一,赐名“延年益寿汤”,后随金兵南逃的难民流落逍遥镇,竟因一罐胡椒粉的意外“闯入”,成就了“胡辣汤”的惊艳转身。如今的逍遥镇,早已是胡辣汤江湖总坛。清晨五更,街巷间便飘起牛骨高汤的醇厚,槐山羊肉与黄花菜的鲜香,与30余味香辛料在砂锅中缠绵。食客们或配油条啜饮,或与豆腐脑“两掺”,辣中带麻,麻中藏香,正如西华老农所言:“喝罢这碗汤,干起活来有使不完的劲儿!”更妙的是,这碗汤竟撑起百亿产业:18万家门店遍布全国,带动20万人就业,连电商包装都成了香饽饽。桃花节与胡辣汤,在西华的土地上构成奇妙的互文。桃花节上,游人醉心于“红黄绿”的视觉盛宴;而胡辣汤铺前,食客们则在味蕾的激荡中,触摸着中原文明的体温。正如梁实秋笔下北平的豆汁儿,这碗汤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乡土记忆的载体。遥想当年漕运鼎盛时,逍遥镇的码头商贾云集,胡辣汤随着驼铃与帆影传遍九州。而今高铁呼啸而过,桃花节游客络绎不绝,传统与现代在此奇妙共生。有位老饕曾言:“一碗胡辣汤,半部中原史。”这话倒应了西华人的自况:“桃花是面子,胡辣汤是里子,缺一不可!”

而今漫步县城,郑合高铁与西华机场的现代化气息扑面而来,沙颍河航道上的货轮与岸边的百年民居,构成奇妙的时空对话。县城的街头巷尾,既有逍遥镇胡辣汤的浓香,亦有西华营镇的月季芬芳,传统与现代在此共生,恰似一壶老酒,愈陈愈香。西华的桃花节与胡辣汤,恰似一部缩微版的人类文明史。从御膳房的秘方到田间地头的桃林,从草根小摊到百亿产业,这些看似寻常的物事,无不镌刻着奋斗与传承的印记。西华地名历史沿革——西华小史政区地名沿革春秋为宋华氏地,因其族较大,且居住宽广,乃分东西,东称东华,西称西华。西汉时置县,因位于华氏地西部,故名。秦置长平属颖川郡,汉高帝时分置西华、长平二县,属汝南郡。王莽(新)更西华为华望县,更长平为长正县。东汉复改为西华、长平。三国魏时西华属汝南郡,长平属陈郡。晋永康元年(300年)西华、长平均属颍川郡。东晋改属陈郡,北魏太武帝时,并长平人扶沟,属北扬州陈郡。后复置。北齐省长平人西华,属信州。隋开皇元年(581年)改西华为柳城县,属陈郡。未几废,复为西华。十八年(598年)改西华为鸿沟县。大业元年(605年)复改为西华县,属淮阳郡。唐武德元年(618年)改西华为箕城县,武德八年(625年)又改箕城为基城县。贞观元年(627年)省基城入丘。长寿元年(692年)复置武城县。神龙元年(705年)改武城为箕城县。景云元年(710年)复改箕城为西华县,属陈州。宋宣和年间,西华属淮宁府。元至元二年(1265年)废清水县,并入西华,属陈州郡。明朝,西华属开封府。清雍正二年(1724年)改陈州为直隶州,西华从属。1914年属豫东道。1933年属河南省第七行政督察区。1947年1月建西华县民主政府。1949年属淮阳专区。逍遥、东夏亭两个区,划归西华。1953年西华县划入许昌地区。1965年西华划归周口专区。据了解,西华县志的历史版本数量可考者至少有四部:1.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宋恂版该版本为现存最早县志,共12册,采用刻本形式,内容涵盖西华县志乘沿革与风土民情。2.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续志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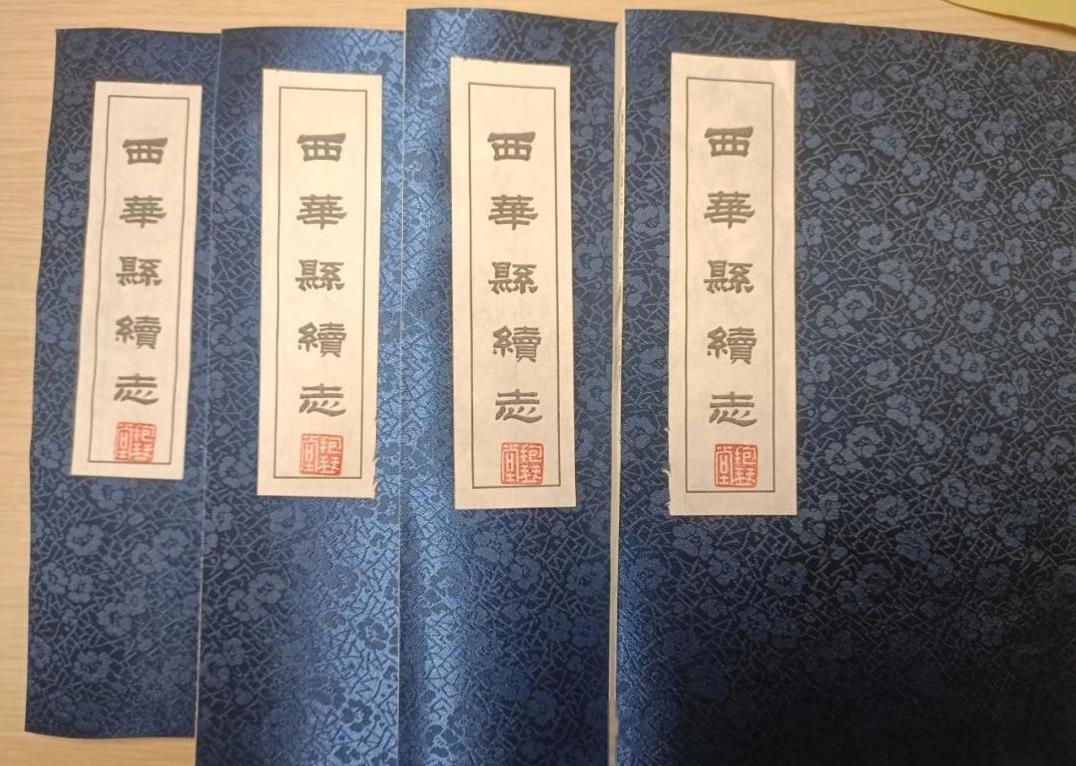
此版县志成书于抗战期间,虽时局动荡仍坚持付印,序言中特别强调"持久抗战"背景,现存版本为复刻本,是研究近代西华历史的重要文献。民国期间,河南号称有南陈、西张、北李三大儒,南是信阳的陈善同,西是南阳的张嘉谋,北是汲县(今卫辉市)的李敏修,三鼎立。民国27年(1938)修的《西华县续志》,即是由河南大儒之一张嘉谋编纂,该志受到方家的好评。3.1961年新编县志

新中国成立后首部系统志书,共4大本1000页,含4幅罕见地图(含3幅彩色地图),由西华县印刷厂承印,内容详实程度为地方志中之翘楚。推测西华县志可能另有其他版本散见于地方志汇编中。目前可确证者至少有上述三部独立编纂版本。4、1992年出版的《西华县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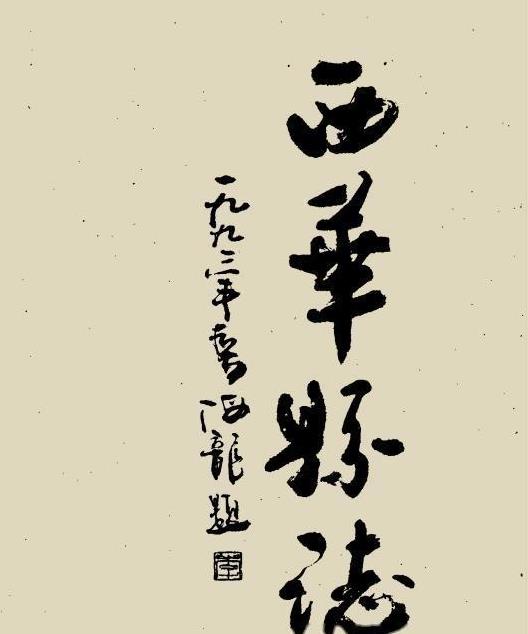
历经十年、数易志稿,反复琢磨,资料充实、体例完备,它记述了西华的巨变,西华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一大奇迹,这一奇迹是足以震惊世界的。即西华人民从毁灭性的黄泛灾害中,建设成了今天的林茂粮丰、工业新兴、文化昌盛,人民温饱的社会主义新西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