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跟大家聊点最近琢磨出来的东西。
起因很简单,就是在自己练拳时,
还有看师父练拳的时候,抓住了一点灵机。
这点灵机,是从感受自己身体内部那种“筋骨之力线”开始的。
就是内家拳里讲究的结构支撑之劲路,
只不过这种劲是动起来的,不是静止的。
现在运动学里讲究动力链,
也就是劲路的传导像一条无形的线,
贯穿全身。
它有方向,有韧性,有支撑,也有流动。
奇妙的是,当我把这种身体内部的“力线感”往外延伸,
去琢磨其他艺术形式时,发现都能说得通!
这种感觉特别有意思。

我们平时形容艺术,会用很多词:
看书法,会说“笔走龙蛇”,那是线条的飞动之美;
看舞蹈,会说“身姿婀娜”,那是身体勾勒的曲线之美;
看拳术,会说“劲力浑厚”,那是力量传递形成的势能线;
看绘画,会说“笔墨精妙”,那是线条勾勒出的气韵与骨架。
这些形容词背后,其实都藏着线条的韵律与节奏之美。
而这,恰恰触及了中国传统艺术一个非常核心的理念:
“取象”,也就是透过表象,
抓住事物的“骨”(结构、支撑)与“髓”(精神、气韵)。
为什么取象难,因为大家都被外面包裹着的肉迷惑了,
看不清里面的骨。
今天,就顺着这点刚悟出的“筋骨之力线”,
跟大家一起捋一捋,
线条是如何成为贯穿中国传统艺术的“筋骨”的。

我的灵感始于拳术,那就先从身体说起。
武术,尤其是内家拳,极其讲究“身法”。
站桩时,要求“虚领顶劲、含胸拔背、沉肩坠肘、松腰坐胯”,
这每一个要领,都是在调整身体的结构,
让内在的“力线”得以贯通、顺畅。
为什么猫科动物捕猎时的身姿那么矫健灵活,
就是因为贯穿整个身体的脊椎这条大龙带着四肢太活了。
学拳无非就是回归爬行时以脊椎带全身的身法。
以龙(脊椎)虎(胯)二劲为基准,
以阴面劲(体内侧)带动阳面劲(体外侧)收缩扩展为约束,
经过腿、腰、脊、肩、肘、手等的开发,
层层传递,让力在其中传递的过程低损耗,
也就是让一条充满弹性和力量的“筋骨线”充分的在体内运行、爆发,
这才是内家拳之所以称为内家的原因。

舞蹈也是如此。
我看抖音上专门有一个恢复古典中国舞的小伙子,
每个动作的造型摆出来都非常好看。
而这“身姿婀娜”的背后,
是舞者对身体线条极致的控制与运用。
古典舞中的“拧、倾、圆、曲”,
每一个动作都是身体在空间中画出优美的弧线。
水袖的挥洒,是手臂线条的无限延伸;
腰肢的款摆,也是躯干线条的柔韧表达。
这些线条,从塑造视觉上的美感,传递到了情绪与意境的渲染,
这是为什么称为“韵味”十足,
因为开发出了身体艺术的“髓”———线条的动态张力。
所以无论是拳术的刚猛或内敛,
还是舞蹈的飘逸或沉静,都是以身体为媒介,
通过对“筋骨之力线”的把握,
去“取”动静之“象”,
得其“骨”架,传其神“髓”。

那么从身体的律动回到纸上的乾坤。
书法,就更为直接了,它本身被誉为“线条的艺术”。
但是它的线条更加深刻的揭示了筋骨之劲。
唐朝楷书大家颜筋柳骨,也是用筋骨来形容他们的字。
而“笔走龙蛇”,
形容的正是书法筋骨线条的生命力与动感。
每一笔画,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气脉相连、顾盼生姿。
王羲之《兰亭序》的行气贯通,
颜真卿《祭侄文稿》的情感奔涌,
都是通过线条的粗细、疾徐、顿挫、转折来体现的。
书法讲究“用笔”,
这与拳术的“用劲”异曲同工。
提按顿挫,如同身体的发力与蓄势;
中锋行笔,如同拳架的中正与贯通。
好的书法,线条是有“筋骨”的——既有支撑结构的“骨”,
又有连接转承、富有弹性的“筋”。
这“筋骨”,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力感,
更是书家内在精神、学养、气息的凝聚。

所谓“力透纸背”,不仅是墨色,
更是那股无形的“气”与“劲”,
是线条所承载的生命“髓”。
通过对汉字线条的经营,
书法家“取”文字结体之“象”,塑其风“骨”,注其神“髓”。
所以,我以前不理解到这一层的时候,
曾经对一些说书法通拳法的言论嗤之以鼻,
因为书法就是书法,拳法就是拳法,
术业有专攻,这些恐怕都是为了宣传的噱头。
但直到真悟透了这一层关系,
以前那么不直观的气势、雄浑、工整、险绝等等词语,
突然冲破了两种学问的壁垒,
找出了它们直观的表述,
那就是筋骨线条在不同载体上分化了的表达方式。
实际上是非常直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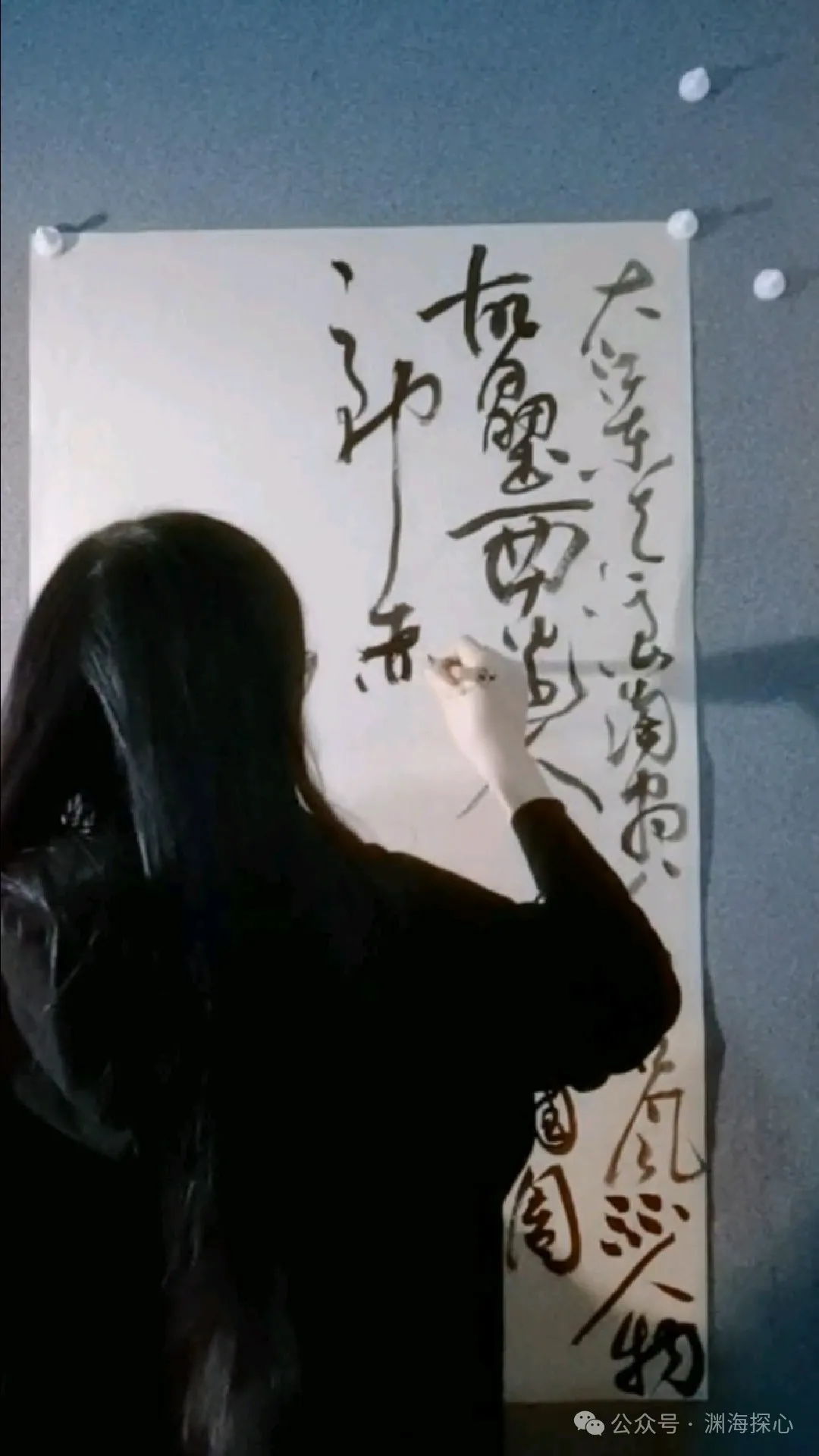
而到了这里,
我联想起了明末著名画家石涛的画论,
以为我特地看完了他的《苦瓜和尚语录》
苦瓜和尚石涛在他的画论中提出“一画论”,
认为“一画”是万物之本源。
这“一画”,落实到画面上,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线条。
中国画讲究“骨法用笔”,
这直接点明了线条在造型中的核心地位——如同骨骼支撑起血肉。
无论是山水画中勾勒山石的皴法线条,
还是人物画中描绘衣褶的铁线描、兰叶描,
线条不仅界定形状,
更重要的是传达质感、体积感和内在的精神气度。
你看八大山人的画,寥寥数笔,鸟儿的孤傲,鱼儿的倔强,跃然纸上。
这绝非简单的外形模仿,而是画家通过对物象精神的深刻洞察,
以最精炼、最具表现力的线条,
“取”其神“象”,抓住那内在的“风骨”与不屈的“精髓”。

山水画中的线条,更是承载着宇宙的节奏与气脉。
一条线,可以是山脊的挺拔(骨),
也可以是云气的流动(髓);
可以是树木的苍劲(骨),
也可以是流水的绵延(髓)。
这“笔墨精妙”的背后,
正是画家运用线条“取象”,
提炼事物“筋骨”,
并赋予其生命神韵的高超能力。
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画,
即是是西方绘画的速写,
也是线条的艺术,
只不过铅笔和碳笔这些硬笔少了毛笔的一些弹性律动。

从拳术舞蹈的身体筋骨力线,到书法绘画的笔墨线条,
我们看到,“线条”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且共通的角色。
它不仅仅是形式的构成要素,
更是承载“气”、“劲”、“神”、“韵”的媒介,
是艺术家“取象”的关键手段,
因为,这是直接把握事物本质(骨)与精神(髓)的必经途径。
而“筋骨之力线”的顿悟,
也让我直接打开了具象与抽象之间表达的桥梁。
从一画论来理解,
它简单,却又蕴含无穷;
它基础,却又直抵核心。
或许,下一次我们再欣赏书法、观看舞蹈、品味画作,
甚至是在运动伸展时,
都可以试着去感受那流淌其中的“线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