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王头衔有多重要?对当时的人来讲,答案是“非常重要”。那时,在那个权力的象征不是外壳而是核心的时代,王权便是实力。国王拥有最高统治权,这一地位表现为他有权册封和废黜贵族。对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诸侯而言,这也是走向完全独立的一步。神圣罗马帝国的结构通常看似很神秘,特别是对英国或美国的读者而言,他们各自的国家很久以前就已经是统一的状态,故而在此有必要解释一下帝国的结构。最好将其看作一个“复合式的国家”,下辖大约300个领地,这些领地的统治者享有一般君主拥有的绝大部分权力,但不是全部权力。这些领地通过以下几条途径密切结合在一起:对皇帝的效忠义务、受由2个帝国法院执行的帝国法律的制约以及它们在雷根斯堡的帝国议会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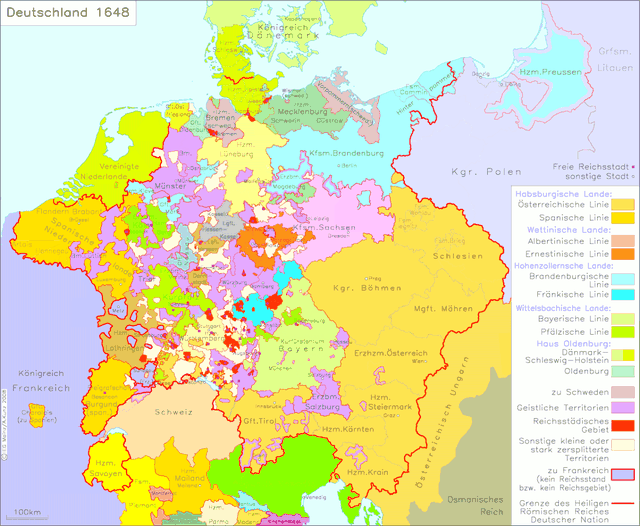
帝国议会分为3个议事团,第一议事团由九大选帝侯组成(美因茨、特里尔、科隆、波希米亚、萨克森、普法尔茨、勃兰登堡、巴伐利亚,以及1692年以后的汉诺威)。第二议事团也是人数最多的议事团为诸侯院,包括34个教会诸侯,以及约40个修道院共享的2张集体选票,还有60个世俗诸侯,再加上100余名帝国伯爵共享的4张集体选票。第三议事团包括51个“帝国自由城市”,这些自治的共和政权,只服从皇帝的权威。这种体制结构在1500年左右固定下来,但世界在继续发展,实际的权力与表象在此过程中分离了。
在17世纪的后半叶,最为活跃的是地位更重要的世俗诸侯们,正如他们纷纷获得国王的头衔展现的那样。只原地踏步就意味着落后于人。如果勃兰登堡选帝侯只是无所事事地干坐着,看着他的汉诺威和萨克森邻居们从大厅阴冷的角落移到主桌贵宾席上,他将很快发现自己被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挤开了。众所周知,其他的诸侯,特别是巴伐利亚选帝侯和普法尔茨选帝侯,都在谋求国王甚至是皇帝的头衔。为了避免被赶超,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在17世纪90年代开始了自己的活动。在1697年的赖斯韦克和平谈判上,勃兰登堡的特使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对弗里德里希三世来说,这是对他附属地位的一次刺眼的提醒。

和之前的例子一样,皇帝对人员和财物的迫切需兰登堡的特使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对弗里德里希三世来说,这是对他附属地位的一次刺眼的提醒。和之前的例子一样,皇帝对人员和财物的迫切需要给了他机会。1700年11月,弗里德里希三世承诺,在即将开始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勃兰登堡会为皇帝提供8000名士兵,还承诺支持帝国的政策,由此获得了称王所必需的认可。1701年1月18日,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宣布,从今以后,他将是“在普鲁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之所以是“在普鲁士的国王”而非“普鲁士国王”(of Prussia),是因为西普鲁士仍处于宗主国波兰统治之下。而舍弃“勃兰登堡”选择“普鲁士”作为国王的名号则是因为普鲁士不在神圣罗马帝国疆界之内,他毋庸置疑对其拥有最高统治权。
加冕典礼在东普鲁士的首都柯尼斯堡举行。为使众人更加信服,弗里德里希使出了浑身解数,确保加冕典礼的庆祝活动配得上最伟大的君主。由3万匹马拉着的1800辆马车,将王宫人员从柏林送到了加冕礼现场。弗里德里希猩红色的加冕长袍上镶嵌着钻石纽扣,每颗价值3000杜卡特。而且,仅是为他自己和王后制造王冠的花费,就已经超过庆典的全部预算。弗里德里希亲手为自己戴上王冠,比拿破仑还早了一个多世纪。实际上,在柯尼斯堡城堡的一个房间里举行完加冕典礼后,国王夫妇才前往大教堂,接受两名专门为此场合选定的主教(一个来自加尔文宗,一个来自路德宗)为他们举行涂油仪式。在加冕日当天,新国王设立了黑鹰勋章,以此象征霍亨索伦家族所有领地的统一。

甲冕典礼的肆意挥霍以及典礼前后奢侈的炫耀,充分显示了普鲁士王室的暴发户性质。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弗里德里希一世将柏林从一个穷乡僻壤建设成为一座合乎国王身份的首都。他父亲的文化喜好一直是简朴无华的,偏向荷兰共和国的实用主义,他父亲年轻时曾在那里度过好几年时光。而新的风格看起来更南方化一些,倾向于以凡尔赛为代表的那种宫廷文化。两座宏伟的新宫殿拔地而起,一座是位于柏林市中心庞大的冬季居所;另一座是矗立在柏林西北部一片绿地上的夏季行宫,名为夏洛滕堡。另一项深受路易十四影响的举措是对文化事业的促进,最引人瞩目的成就包括:在哈勒建立的一所新大学;1697年成立的一所艺术学院,它将成为 “像罗马和巴黎的学院那样的高等艺术学校或艺术大学”;还有1700年成立的科学院,其第一任院长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莱布尼茨。
弗里德里希三世受到了历史学家的粗暴对待,这尤其是因为他的孙子在《勃兰登堡家族回忆录》中对他的严厉谴责。这本书中对他的控诉可以概括如下:这位新国王以头衔的膨胀来弥补他在邻国面前坚持自身主张时的无能。个子矮小、身有残疾的他贪慕豪华排场,把王权的虚饰误认为实质。他任性的奢侈挥霍并无有用的目的,仅仅是出于虚荣心和愚蠢的浪费行为。他让自己的士兵为其盟友白白牺牲,还剥削穷人以使富人获利。他对自己王国东部省份的饥荒和瘟疫坐视不理。他的宫廷榨取民脂民膏,成了一个腐败朝臣沆瀣一气的大污水坑。他意志软弱又迷信,醉心于他的加尔文教信仰到了疯狂的程度,以至于只要神职人员为迫害行为设计了一个适宜又华丽的仪式,他就会诉诸迫害的手段。他唯一能被称赞之处就是获得了国王头衔,这至少让勃兰登堡从奥地利君主国的枷锁中挣脱出来。但这也只是一个给子孙传递了如下信息的空壳:“我为你们挣得了一顶王冠,现在赋予它一些实质性内容吧,以证明你们配得上它。”
弗里德里希二世应该承认,建造一个华丽的宫廷被视作是任何有自尊心的诸侯必备的条件,更别说国王了。弗里德里希三世认为他的宫殿建筑是“一项必需品”。

在德意志的其他地方,从1700年左右开始就遍布着宏伟的宫殿——巴伐利亚有宁芬堡宫和施莱斯海姆宫,萨克森有德累斯顿王宫和莫里茨堡,汉诺威有海恩豪森王宫,普法尔茨有曼海姆宫,黑森-卡塞尔有威廉高地宫,符腾堡有路德维希堡,还有布吕尔(科隆)、布鲁赫萨尔(施派尔)、美因茨、班贝格和维尔茨堡等地也有宫殿,以上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逆此潮流而动的国王并非弗里德里希三世,而是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后者于1713年登基,他对文化的冲击可谓惊人至极。曾拥有神圣罗马帝国最迷人的宫廷之一的普鲁士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弗里德里希·威廉认为,戏剧、歌剧、音乐会、舞会和所有其他宫廷活动都是“撒旦的工作”。
宫廷预算被大幅削减;宫廷画家安托万·佩恩的薪水被砍掉了一半;管弦乐队被解散。王家图书馆的置书费被削减到侮辱性的每年4塔勒,图书馆员的职位变成了名誉称号。供人娱乐的花园被夷为平地并改建成了练兵场。从各处宫殿和狩猎别墅里收集来的大量银器,不论多么精美,都被集中熔化成银条,打上军队的烙印,并存放到波茨坦宫酒窖的木桶里。这些银条将是弗里德里希·威廉最实际的遗产:到1740年,这笔巨额财富的价值膨胀到了870万塔勒,他的儿子对此感激不尽。要不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在其统治后期增加了宫廷和宫殿的经费开支,这笔钱的数额会更大。

一支规模庞大、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一个习惯于服从的忠诚的贵族阶级;一个高效的行政机构;一笔数额巨大的战争基金,足以在不额外征税或是贷款的情况下发动战争:这些就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父王于1740年5月31日死去时留给他的遗产。有过其他的王储在如此有利的形势下继承王位吗?
当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查理六世在同一年稍晚时候(10月20日)去世时,他给女儿玛丽娅·特蕾莎留下的是空空如也的国库,堆积如山的债务,一个充斥老朽之辈、派系丛生的内阁和一支战斗力不足其名义上一半的军队,这支军队还在舔舐着与土耳其人的灾难性战争后留下的伤口。哈布斯堡君主国只在传统方面维持着优势。就像弗里德里希二世尖刻的评论那样,“它的骄傲弥补了它力量的缺乏,它过去的辉煌遮盖住了它现在的耻辱”。不幸的是,弗里德里希·威廉给他儿子留下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厚物质遗产也相应伴随着巨大的心理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