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3月20日,
一向忙碌到晚10点的外卖骑手田某
一反常态——
当天下午2点半后,
他没有再接过单,
手机上也没有任何主叫或被叫记录。
两天之后,
他才被发现
猝死在独自居住的出租屋内。

在京务工多年,
田某干过装修、家政、送快递等各种体力活。
某外卖平台的众包骑手,
是他从事的最后一项工作。

与专职骑手不同,
田某这样的众包骑手属于“兼职”。
他们的工作时间和地点自由,
个人注册参与平台配送,
按单赚钱,
自配保险。
每天开工接单前,
众包骑手必须先在平台上购买
价值3元钱的一日意外险。
田某和其他骑手从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直到出险理赔。

田某意外猝死后,
家人欲索赔,
却遭保险公司拒绝。
保险公司给出的理由是:
01
田某死亡时间超过合同规定的
“身体急性症状发生后即刻
或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02
田某猝死时不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而是在出租屋内;
03
骑手通过合作商在平台投保,
保险公司已向合作商进行了提示说明,
免责条款无需再向每一名骑手释明。
法庭上,
围绕田某猝死是否发生于保险期间、
保险公司限定的
“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是否合理、
实际投保人是谁等焦点问题,
双方当事人进行了激烈交锋。
我国有多少新业态劳动者?
全国总工会第九次
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
这个数字高达8400万!

然而近年来,
骑手发生意外事故,
保险公司拒赔现象多发。
如何保障新形态从业人员保险权益?

作为本案二审审判长,
北京金融法院法官王思思
看到了本案可能带来的社会意义
穿透本案交易架构,
洞悉保险产品本质,
拨开商业嵌套下的迷雾。
针对三个争议焦点,
合议庭抽丝剥茧完成最终认定:
一、就田某死亡时间是否在保险期间问题

法院认为,
田某3月20日购买的保险
有效时间截至3月21日1时30分0秒。
但公安机关根据现有证据,
也难以认定田某死亡是否超过上述时间。
此时,
不应苛责猝死者及其家属有能力证明。

且田某在3月20日下午2点30分后,
没有任何生活、工作活动迹象,
这与常理严重不符。
因此,
结合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
可以认定田某的猝死事件
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存在高度盖然性 。
二、就田某死亡是否符合处于工作岗位问题

法院认为,
外卖骑手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
在认定骑手是否处于
工作岗位、工作时间时,
不应仅参照平台记录的接送单时段,
还应考虑骑手等待接送单、
接单间隔或者为接送单进行准备的过程。

根据田某日常接单习惯,
其在下午2点-5点间往往选择休息,
为晚高峰时段继续接单补充体力。
故不能因田某系在出租屋内猝死,
即认定该事故发生在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岗位。
三、就意外险的实际投保人及保险免责条款释明问题

法院认为,
案涉保险的性质系人身保险、商业保险,
目的是保障骑手的人身安全。
无论表面形式如何,
实际上的投保人及被保险人,
均应是客观上有投保需求和保险利益
且实际支付了保费的骑手。
也正因此,
保险公司提示说明义务的履行对象,
应当是实际投保人即骑手。
因保险公司未能充分举证其就免责条款
向实际投保人进行了提示告知,
故该免责条款对骑手不发生法律效力。
2024年4月,
本案二审判决作出后,
田某的妻子及一儿一女
很快收到了60万元保险赔偿款。

提到田某一家的情况,
本案一审法官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法官邵一峰
印象也很深刻:
“骑手是新时代的劳动者
也是值得尊敬的奋斗者。
我们在一审期间,
考虑到当事人的经济条件,
为减轻其诉讼成本,
最终赴田某山东老家开展巡回审判。”

当被问到本案后续效果时,
王思思告诉记者,
案子判了之后,
保险公司就众包骑手意外险引发的批量性纠纷
自发地与骑手们进行和解,
并调整了保险产品的入市模式和条款。
同时,
法院以本案为契机,
针对保障外卖骑手
这一新业态劳动者保险权益问题,
向监管部门发送司法建议并得到回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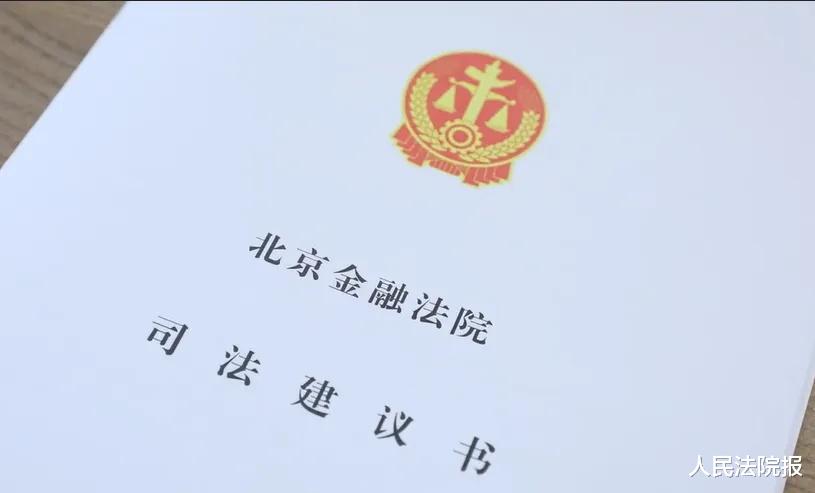
据悉,
本案也成功获评
“2024年度北京法院贯彻落实
习近平法治思想优秀实践案例”。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
“新业态虽是后来者,
但依法规范不要姗姗来迟,
要及时跟上研究,
把法律短板及时补齐,
在变化中不断完善。”

在全国人大代表安康看来,
外卖骑手猝死保险理赔案的
依法公正妥善审理,
正是人民法院真正践行
“如我在诉”,
积极保障新业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有力例证。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记者:杨梦娇
图片/视频:北京金融法院、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