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时期,一种突然出现的黑色怪物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官修正史将这种怪物称为“黑眚(shěng)”。此前,偶有黑眚现身的记载,但基本都在夜里出现,而且它每次现身,必有大凶之事发生。最近的两次现身,一次紧接着宋神宗驾崩,另一次则是宋哲宗驾崩。
到了宋徽宗大观(1107—1110)年间,黑眚不仅频繁现身,更诡异的是,白天也能看见它。政和元年(1111)以后,黑眚愈加肆无忌惮,一听到宫殿内有人说话的声音就现身吓人。
《宋史》细致地描述了黑眚现身的过程及其样貌:
“先若列屋摧倒之声,其形廑丈余,仿佛如龟,金眼,行动硁硁有声。黑气蒙之,不大了了,气之所及,腥雨四洒,兵刃皆不能施。又或变人形,亦或为驴。自春历夏,昼夜出无时,遇冬则罕见。”
动静很大,外形多变,伴有黑雾笼罩;刀枪不入,连禁军都拿它没办法;唯一的软肋可能是怕冷,所以冬天极少现身。
它出来吓人的次数多了,宫中之人反而习以为常,不觉得恐怖了。
等到宣和(1119—1125)末年,黑眚现身逐渐减少,而北宋也离亡国越来越近了。
对于这种怪异之事,史学家吕思勉认为,虽然难以解释,但历时甚久,见者甚多,“不能尽指为虚诬”。
如果一定要寻找一个解释,在古人的观念世界里,这就是所谓的“亡国之象”。

宋徽宗画像

除了带有玄幻性质的“黑眚”,在古代,天象异常或自然灾害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王朝衰亡征兆。比如,我们读史书会看到陨石坠落、彗星出现、久旱不雨、洪水暴发等等记载,这些在特殊时期都被朝廷官员解读为上天启示,并以此劝谏或警告君王。
最典型的例子来自明朝末年。
当时,陕北与关中地区北部连年干旱,草木枯焦,赤地千里。在天启帝去世、崇祯帝继位的天启七年(1627),陕北地区“草木尽,人相食”,农民“皮骨已尽,救死不赡”。据不完全统计,崇祯在位的17年中,全国各地竟发生了14次特大干旱,各地“饿殍遍野”“人相食”的记载十分常见。
干旱不是孤身而来,它还伴随着蝗灾、瘟疫等灾情。在明末的大瘟疫中,鼠疫的危害程度尤其大。明清之际华北三省的死亡人口中,至少有500万以上的人口死于鼠疫。
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灾害是极端气候造成的,是“明清小冰期”威力发作的后果。
但当时人更愿相信,这就是亡国之兆。特别是经历过明清易代的幸存者,更容易产生“国之将亡,必有异象”的联想。

从科学的角度分析,不管是当时人的认知还是后来修纂的史书,对于天象、灾异的描述和解读其实大多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和事后诸葛亮式的附会。一个朝代的衰亡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经济衰退、外患入侵等,所谓的“亡国之象”更多的是当时人们对社会动荡不安情绪的一种反映。

问题是,古人对于天象、灾异的认识,到底是怎样的?
宋神宗即位后,天下出现了一些自然灾害。这时,有人就对神宗说,这些灾害都是天帝预先安排好的,跟国家治理的好坏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富弼听说后,叹息道,天子所敬畏的只有天帝,如不敬畏天帝,什么事干不出来?这就离亡国不远了。
于是,富弼上书数千言,洋洋洒洒引用经典、史籍,只为证明一件事情:自然灾害与人事作为、国家治理是息息相关的。
在关于天象、天灾的认知上,朝堂上关注的重点从来不是科学/迷信之分,而是忠臣/奸人之别。听到有人劝说皇帝摆脱天灾束缚的阴影,作为忠臣的富弼立马就想到,这是奸人企图用歪理邪说来误导天子,一旦天子无所敬畏,负责谏诤的大臣便无法用力劝阻,这个国家就糟了。
所以古代士大夫是真心拥护天人感应这一整套学说的,将天象、天灾与国家治理深度绑定,说白了也是皇权制约的一种手段。就此而言,对于“亡国之象”的阐释,就是那个时代的“科学”。

富弼画像

但我们今天写历史和读历史,显然不能仅满足于古人的“天人感应说”,还应该着力于揭示古人认识不到或认识到了却不敢说出来的深层原因。
开头讲到的“黑眚”现身于北宋禁中,用现在的话语是可以解释的——它本质上是北宋末年的“都市传说”,极大概率是口口相传渲染出来的恐怖故事,唯有背后反映的人心异动以及对于宋徽宗执政的王朝危机的不安是真实的。人心不安借诡异的“都市传说”进行表达。
而明末的天灾也不必然导致明亡,明亡的祸首应该是天灾之后的国家应对。如果是汉代文景时期的治理模式,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天灾,朝廷的第一姿态一定是减免赋税,休养生息。但在崇祯时期,明朝官方不仅没有减免税赋、赈济灾民,反而增派“新饷”“均输”等赋役,并严令官吏督责催收。这一系列操作,相当于给明朝贴上了一张催命符。
走投无路的底层开始搏命寻求自救,农民王二在陕西澄城率众杀死了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翌年,即崇祯元年(1628),因为年荒乏食,曾经作为边兵的王嘉胤也组织灾民揭竿而起,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随之先后参与农民起义,一时陕西遍地烽火,并蔓延到山西、宁夏、甘肃三地,明末农民起义由此逐渐成势。
所以,关于明亡,天谴之外,人事又占了几分?作为一个视野内缩的农业帝国,明朝的财政体制从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缺陷,在危机来袭时根本无法灵活拆招;庞大的官僚体系则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大多数官员都默默等着跳槽换公司、换老板;海量的宗室人员,从一开始就是啃蚀大明根基的寄生虫。一个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的王朝,面对天灾频仍的状况,人事应对的蛮横草率才是真正的“亡国之象”。

类似的:
李斯被杀后,秦二世任命赵高为丞相。赵高做了一个忠诚度测试,命人牵来一头鹿献给秦二世,并说这是一匹马。秦二世说,丞相是在开玩笑吧,怎么把鹿说成马?于是,秦二世问左右大臣,这到底是鹿是马?有人默不作声;有人为迎合赵高,跟着指鹿为马;当然也有人直言是鹿——这些人恰好成了赵高收拾的对象。
这个成语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但以常理度之,如此赤裸裸地愚弄皇帝与众大臣,现实中发生的几率几乎为零。所以我一直认为史家是把这一事件当成寓言在写的——它不一定是史实,但一定是秦朝亡国的政治隐喻。
当朝堂上只剩下指鹿为马之人时,离亡国就不远了。

故事还有很多,艾公子的新书《王朝的崩溃》对此有深刻而全景式的描述分析:
当汉献帝与公卿大臣会见时,却能看到驻守在外的士兵脸上挂着嘲弄的笑意,听到他们不加掩饰的喧闹声;当权相贾似道以“打算法”之名对一代名将刘整进行整肃时,刘整惊恐不安,向朝廷上诉,但又投诉无门;当洪承畴向皇太极俯首称臣时,紫禁城内的崇祯皇帝还以为他已经“殉国”,为他设祭坛……
古人认为不可揣摩或玄之又玄的“亡国之象”,在这本书中化成了一个个具体可感、可追溯、可分析的历史时刻,这些时刻积聚于历史的台面上,直至王朝无法承压而轰然倒塌。

所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么,国之将亡呢?自古至今,从人到组织,都逃不过生死存亡、兴衰成败的生命周期。纵观中国自秦朝大一统以来两千多年的帝制文明,尤其可引为殷鉴的,莫过于王朝崩溃、毁灭的最后时刻。
《王朝的崩溃》聚焦中国历史上17个大一统或局部统一的王朝的最后几年,通过透视它们衰亡背后的政治、军事、经济、财政、人事、气候等各种问题和境况,从而提供一种思考:假如历史的盛衰周期无法改变,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又能为应对下一次危机准备些什么?
传统史书中的“亡国之象”,几乎都是一些散乱而独立的表述,每一处都看似隐含微言大义,实际上却颇多后见之明,依然无法突破“当局者迷”的思想困境。既然如此,何不引入现代史学的方法与观念,对这些王朝的覆灭时刻做全景式的分析与描述,以构建“旁观者清”的历史认知呢?
每一个王朝的崩溃千差万别,但背后的深层原因却有相当的一致性。
从思想上说,立国的理论资源是可以转化的。你的亡国之象,恰是我的祥瑞。比如西汉哀帝时期,无论皇帝本人还是帝国都有衰微之象,于是上演了一出“再受命”闹剧,希望以此延续国祚。但闹剧过后,汉朝天命将近的说法反而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各种祥瑞之象纷纷上报给了野心勃勃的王莽。
从统治阶层上看,君主与士大夫的分裂也可以导致王朝崩溃。东汉的党锢之祸,表面是宦官迫害忠臣的运动,但宦官从来无法形成统一的阶层,他们背后一定是皇帝。所以,士人对宦官专权的指责,其实隐隐指向的是宦官背后想要集权的皇帝。皇帝如果懂得体恤儒士,便是理想的共治模式,值得拥戴称颂;皇帝如果不懂,那么一定是受到身边人——外戚或宦官的蒙蔽。
从阶级角度分析,底层的地位坠落亦值得反思。西晋立国以后,世家大族获得无限特权,不仅自身免除各种负担,还可以荫庇亲族、依附民。依附民虽然地位比奴隶高一些,但并没有人身自由,平时要为地主耕作,战时要为地主战斗。从自耕农到依附民,人的地位无疑下降了,但很多自耕农认为这种变化是一种“高攀”,为什么?因为成为朝廷的编户齐民,就要接受官府永无休止的劳役和名目繁多的赋税,这是比丧失人格更恐怖的事。
……
身处某个历史周期之中,人很难看清自己所处的时代,这种现实困境使人更加向往拥有全知视角。当下信息纷繁,未来难以预测,所幸我们可以看见过去,总结过去。《王朝的崩溃》这本书犹如一面镜子,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封建王朝兴衰的历史轨迹和内在逻辑,或可助力我们穿透时代的迷雾,谨慎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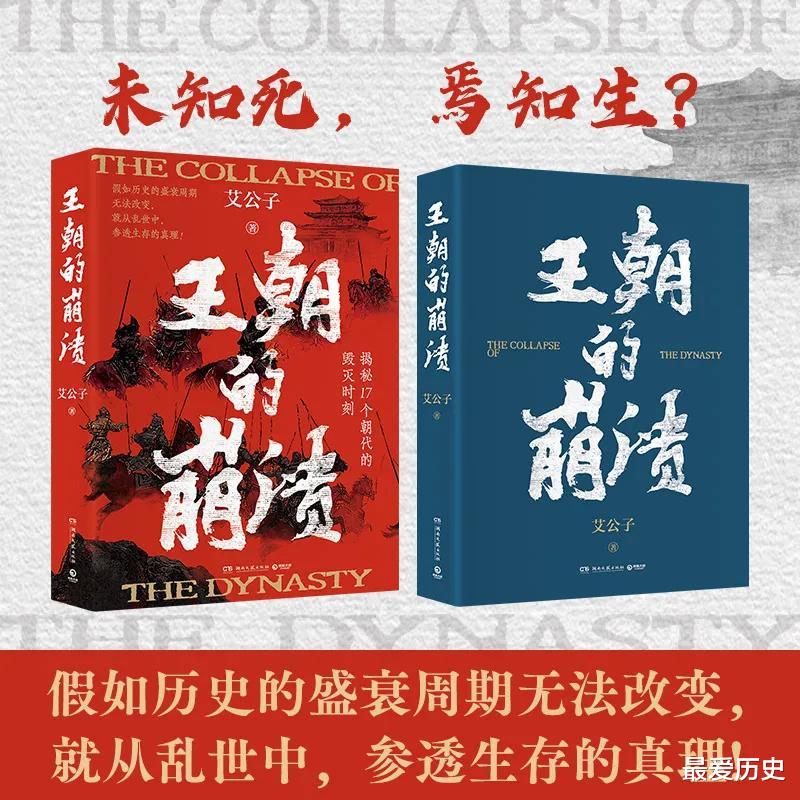

满遗们真有钱,变着花样买文狗一边抹黑大明,一边给鞑清涂脂抹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