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由于湖州知州苏轼在《湖州谢上表》当中写有敏感词汇,被监察御史上奏弹劾,宋神宗派人要将他抓捕进京。
在宋神宗的授意之下,御史台马上派出以太常博士皇甫遵为首的人马,马不停蹄地前往湖州抓捕苏轼,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根据当时的朝廷制度,官员被调往新的地方做官的时候,都要给皇帝写一封感谢信,因此,苏轼来到湖州担任知州仅仅三个月,就写下了献给皇帝的一篇《湖州谢上表》。
然而,《湖州谢上表》只是苏轼写给宋神宗的一篇感谢信,内容并没有涉及朝廷的任何信息,为什么还会发生“乌台诗案”呢?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监察御史何正臣仔细观看了苏轼送来的这篇《湖州谢上表》,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
“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察事,或能牧养小民。”
从苏轼的话语当中可以看出,苏轼是在《湖州谢上表》里面发泄了对宋神宗的不满情绪,他无法跟“王安石变法”的变法派一起共事,所以只能来到湖州管理一下地方事务了。
从宋太祖建立宋朝之后,宋朝一直都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而苏轼当时已经当了八年的地方官,竟然还没有被调往朝廷,所以他对宋神宗产生意见也在情理之中。
虽然苏轼当时的文采已经名誉天下,但始终就是得不到宋神宗的重用,这或许跟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

苏轼
在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实施“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苏轼和司马光等人一样,选择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
不仅如此,苏轼还经常给宋神宗呈上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奏折,其中表示“王安石不应该这么改革”、“科举考试改得不对”等等。
这样一来,在宋神宗的心里,苏轼就成为了他最为讨厌的大臣,自然不会对苏轼加以重用。
在写给宋神宗的那篇《湖州谢上表》里面,苏轼只是写了几句发牢骚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过激性的词汇。但是,当苏轼的这几句“牢骚话”,到了那帮居心叵测的御史台手里面,意义和性质就完全改变了。
监察御史何正臣、李定、舒亶正是抓住了《湖州谢上表》当中的那几句话,在中间大做文章,并且还给苏轼安上了一个“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传中外,孰不叹惊”的罪名。

对于宋神宗来说,他为了推行“王安石变法”,不顾曹太后以及众多大臣的反对,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谁想要阻挡新法的推进,就会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须要清除,更何况一个小小的湖州知州呢!
于是,身为湖州知州的苏轼,尽管在湖州当地深受百姓的拥护和爱戴,还是被御史台的几道弹劾奏折逼上了绝境,从而被皇甫遵率领的人马逮捕进京。
在宋神宗的心里,他也希望苏轼能够帮助自己推行变法,但因为政治理念不同,根本无法重用苏轼。
宋神宗深知,苏轼的高调行事作风也确实影响了新法的推进,已经到了自己出面调解平衡的时候了,索性就借着逮捕苏轼的机会,打压一下保守一派。
从苏轼被调往湖州担任湖州知州,到莫名其妙地被捕入狱,期间仅仅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而这一年,苏轼已经四十三岁了......
从表面上来看,苏轼的被捕是因为监察御史上书弹劾的结果,然而实际上,却是宋神宗为了推行变法,而故意趁机调整新旧势力所下的一步棋。
可惜的是,此时的苏轼却对此一无所知,他还在各种猜测自己被捕的原因。
就这样,在一头雾水的情况之下,苏轼被皇甫遵率领的人马绑了起来,并且准备押解到北宋的国都汴京(如今的河南开封),他也不知道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根据北宋学者孔平仲在《孔氏谈苑》当中的记载,苏轼被押上一艘船准备走水路前往汴京,当他们走到太湖的时候,由于船桨损坏,不得不停下来进行维修。

于是,在士兵的看守之下,苏轼坐在太湖旁边的芦香亭休息。
然而,当苏轼望着太湖之上美景的时候,他的内心百感交集。
此时的苏轼已经隐约意识到,自己的遭遇必定跟创作的诗文有关,而是自己的朋友实在太多,跟许多朋友之间都有过诗文创作和书信往来。
苏轼心里明白,在当时那个文字狱盛行的时代,一旦自己的罪名成立,势必就会牵扯进来众多的朋友,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苏轼认为,与其连累朋友,不如一死了之,他竟然萌生了跳湖自尽的念头。

可是,即便苏轼投湖自尽,这件事情就可以就此了结吗。
苏轼坐在湖边前思后想,他担心自己投湖自尽之后,留下一个手足情深的弟弟苏辙该怎么办呢?自己的朋友依然会受到牵连又该怎么办呢?
想到这里,苏轼决定重新振作起来,不管前面即将面临怎样的风险,也要勇敢去面对。
苏轼看着同样坐在湖边休息的太常博士皇甫遵,他非常想要询问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终究还是没有开口询问,他只是在心里联想出了无数种可能面临的后果。
为了折磨苏轼,皇甫遵可谓是煞费苦心......

皇甫遵内心深知,苏轼利用自身的文采结交了许多朋友,这次被捕入京,肯定会有许多朋友前来探望他,那就阻止他们见面,彻底让他变成一个孤家寡人,从心灵上折磨他。
可是,当大家知道苏轼出事之后,由于担心会惹火上身,纷纷选择远离他。
常言道“患难见真情”,并不是所有朋友都对苏轼避之远离,而且敢于跟他站在一起,其中就包括扬州知州鲜于侁(shen)。
就在皇甫遵押着苏轼途经扬州的时候,鲜于侁主动提出要见苏轼一面。
然而,皇甫遵断然拒绝了鲜于侁的请求,并且威胁他说:“我知道你是扬州知州,你跟苏轼之间的关系很好,你们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比较频繁,你赶快回去把那些书信全部烧了,否则会把你牵连进来的!”

面对皇甫遵说出的略带威胁的话语,鲜于侁并没有被吓到,而是义正词严地说道:“欺君负友,吾不忍为,以忠义分遣,是吾所愿。”
因此,就在大家纷纷对苏轼避而远之的时候,鲜于侁甘愿冒险来探望他,可见他们两人之间的情意之深。
经过了二十多天的一路跋涉,皇甫遵顺利将苏轼押解到了汴京,并将他关进了刑部监狱。
虽然此时的苏轼身心疲惫,但御史台的那些人一心想要把他置于死地,不让他拥有任何喘息的机会,没过几天就开始对他进行一场残酷的审讯。

负责审讯苏轼的主要官员是监察御史李定和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张璪,他们两人都是属于“王安石变法”当中的变法派,与苏轼正是政治上的对头。
关于张璪的品德,《宋史》当中评价他为“德之贼”,几乎是没有什么道德可言,还经常编造一些谣言陷害他人。
审讯刚一开始,李定和张璪就问苏轼一个十分奇怪的问题:“在五代之内,你们家族有没有皇上赐予的誓书铁券?”
誓书铁券通常是由皇帝赏赐给那些立下赫赫战功的大臣的,如果他们本人或者他们的后代犯了重罪,可以拿出来免除罪行,相当于“免罪金牌”。
然而,御史台的那帮人早就提前把苏轼的家庭背景调查的一清二楚。

李定和张璪明明知道苏轼没有誓书铁券,仍然故意问出这句话,其实是在告诉苏轼:你这次犯得可是重罪,谁都营救不了你,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问你什么问题,老老实实回答就行了。
那么,李定和张璪采取的这个计策,能否攻破苏轼的心理防线呢?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李定和张璪想要尽快拿到苏轼交待的口供,这样就可以把苏轼的罪名坐实,从而把他置于死地。
可是,审问刚刚开始之后不久,面对李定和张璪提问的第一个问题,苏轼不愿意回答,他看不惯自己受到这样的折磨和羞辱,竟然再一次想到了自尽。

而这一次,苏轼想到的自尽方式是绝食,他拒绝接受食用狱卒送来的食物。
苏轼在监狱之中绝食了两天,就传到了宋神宗的耳朵里,宋神宗马上派人来到监狱询问情况,但苏轼什么话也没说。
眼看宋神宗派人来到监狱进行稳询问,苏轼意识到,此时的宋神宗还没有忘记自己,说明自己犯下的罪名罪不至死。
想到这里,苏轼给自己的心灵带来了很大的安慰,他决定继续坚持下去,于是放弃了“绝食自尽”的念头。
对于这起“乌台诗案”,御史台的那帮人早就想好了对策,他们想要从苏轼身上获取两个目的:一是通过苏轼招供的许多诗词歌赋上面,来证明他对皇上和朝政的诽谤,从而将他置于死地;二是利用苏轼跟他的朋友之间的书信往来,将朝廷当中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牵扯进来,从而将保守派一网打尽。

苏轼被囚禁的监狱,环境是极其恶劣,面积非常狭小,双手伸开甚至就能碰到两遍的墙壁。
长时间被关押在这种狭窄的监狱当中,不仅给苏轼的心灵上带来了压抑的感觉,而且还要在这里日夜不停地接受审讯。
值得庆幸的是,自从宋太祖建立宋朝以来,就立下了一个祖训,那就是“不得对士大夫动用刑罚”,因此苏轼可以免去许多身体上的严刑拷打。
虽然宋朝规定不能对苏轼采取刑罚,但御史台的那帮人是何等的精明,他们知道,折磨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心灵上的折磨远远要胜于身体上的折磨。
于是,李定和张璪想出了一个办法,轮流派人看着苏轼,不让他睡觉。

苏轼旁边的一间牢房里面,关押的正是在“铁钉杀母案”当中被御史台诬陷入狱的开封府知府苏颂。
苏颂在监狱关押的时候,每天都能听到苏轼在隔壁的牢房里面接受审讯,而且经常是日夜受审,还能听到狱卒对苏轼的各种难听的指责和辱骂。
尽管苏颂十分同情苏轼的遭遇,但他也是被人诬陷身陷囹圄,除了怀有一颗深深的怜悯之心以外,再也无能为力。
关于这起震惊朝野的“铁钉杀母案”,监察御史何正臣对于苏颂的审讯,主要依据就是来自大理寺丞贾种民提供的供词。后来宋神宗下令深入调查下去,何正臣却意外查到,贾种民竟然私自篡改了李氏的口供,从而酿成了一起冤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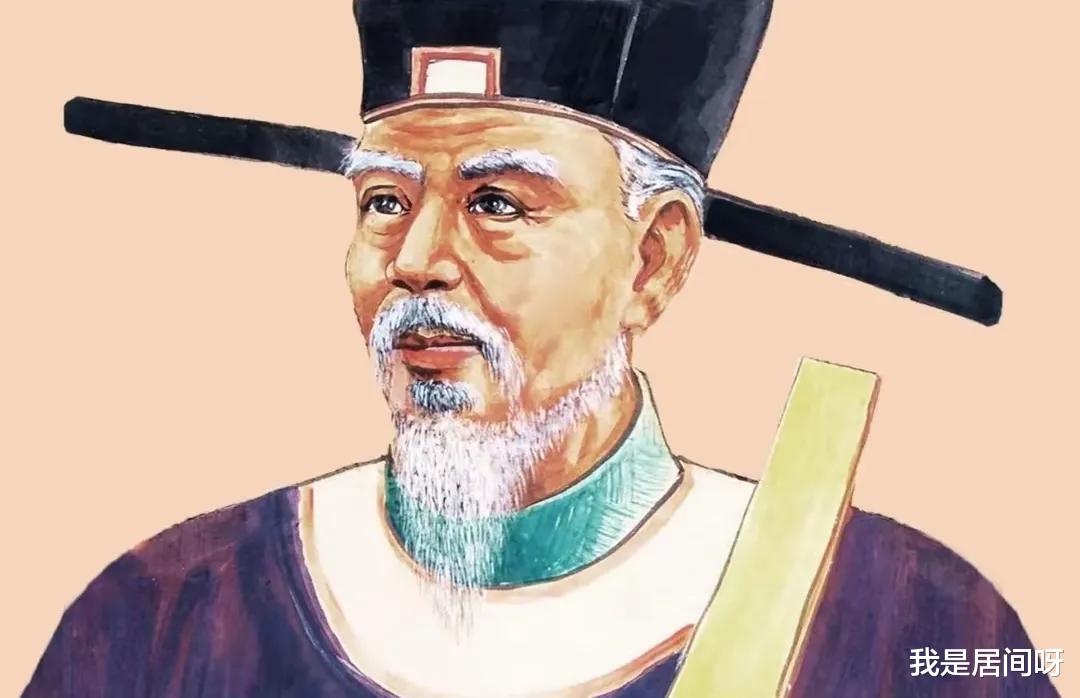
苏颂
直到这个时候,宋神宗终于明白,苏颂和吕公著是被冤枉的,他们两人都是值得信赖的大臣,当即下令释放所有的关押人员。
苏颂被释放出狱之后,对于在狱中亲耳听到的苏轼的悲惨遭遇,不禁感慨写下了一首诗《元丰己未三院东阁作十四首(其五)》,诗中还为苏轼鸣不平:
“飞语初腾触细文,庭中交构更纷纭。网条既甚秋荼密,枉直何由束矢分。御史皆称素长者,府徒半识故将军。却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自从苏轼被押解到汴京之后,御史台的那帮人始终摆出的都是一副欲除之而后快的架势。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身在监狱之外的苏轼的亲朋好友,此刻正在为了营救苏轼而绞尽脑汁,四处奔波。

但是,想要把苏轼安全解救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毕竟苏轼被捕入狱,大家都还不知道他被捕的真正原因,即使想要救他出狱,也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经过多方打听,去世的亲朋好友几乎动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渠道,终于得知这件事情的背后竟然是宋神宗在暗中操纵,以此来打压朝廷当中的保守派。
这样一来,想要营救苏轼出狱,就必须劝说宋神宗改变主意。
那么,谁会甘愿冒险站出来与宋神宗和御史台为敌呢?

第一个站出来替苏轼说情的是已经辞官在家的翰林学士范镇,他向宋神宗呈上奏折,极力阐述苏轼是朝廷当中难得一遇的人才,请求宋神宗放过苏轼一马。
范镇在担任翰林学士的时候,就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而且两人的政治观念十分相似,对于王安石实施的“王安石变法”,他也持有非常大的反对意见,但并没有得到宋神宗的采纳,于是一怒之下就辞去官职。
范镇辞官回家之后,由于自身直言敢谏的性格,从而引来许多朋友的称赞。
有一次,苏轼来到范镇的家里拜访,刚一进门就说道:“恭喜你啊,虽然你现在已经退休在家了,但是你现在名声反而越来越大了!”

范镇回答说:“我希望看到的是天下太平,可是如今朝廷因为推行新法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而我独享其名,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由此可见,范镇是一个好官,他敢于在这个时候第一个站出来替苏轼求情,可见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
然而,范镇知道,仅仅依靠自己的薄弱力量,根本无法说服宋神宗改变主意。
就在范镇忙着向宋神宗上书求情的同时,苏轼的弟弟苏轼却迟迟没有采取营救行动。他不是不着急营救苏轼,而是一直在思考应该怎样打动宋神宗,从而让宋神宗改变主意。

王安石
经过再三思索,苏辙提笔写下了一封奏章,他通过打感情牌,在奏折当中更多体现的是人性的正义和善良,这让宋神宗感触颇深。
随后,又有三位大臣相继站出来替苏轼求情,第一位是王安石的亲家、宰相吴充,第二位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第三位则是身在南京赋闲的王安石本人。
尽管苏轼曾经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但王安石的脑海里只想实现富国强兵,并不想通过变法打压政敌和排除异己。
虽然王安石此时已经不在朝中主持变法,但他的话在宋神宗心目当中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可是,就在宋神宗准备放过苏轼一马的时候,御史台的那帮人又想出了一个新招,他们通过刑讯逼供逼迫苏轼认下了所有口供。

王安石
其中包括,苏轼被迫承认在《山村五绝·其三》和《山村五绝·其四》里面讽刺“王安石变法”推行的盐法、青苗法和助役法。
随着苏轼的“被迫”认罪,御史台的那帮人也终于达到了自身的目的,等待苏轼的似乎就只有死路一条。
庆幸的是,由于曹太后的出面说情,以及宋神宗为了祖母而大赦天下,苏轼才得以逃脱一死,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他最终被贬到了偏远的黄州充当团练副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