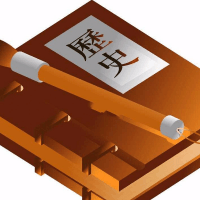作者:刘宏宇
还有人记得“刀子”吗?
退一步——还有人记得几年前颇有争议的电影《八佰》吗?
为什么“争议”,不说了——没得说。有的说也不敢说。只讲电影本身——

(一)情节与人物追忆及疑惑
电影《八佰》故事提要:全面抗战爆发之初的1937年11月,史称“八一三抗战”(标记其始于同年8月13日)或“第二次淞沪抗战”(相对1932年“一二八“事件引发的局部抗战而命名)败局已定,日寇全面占领上海“华界”,唯有相邻“租界”的“界河”苏州河的“四行仓库”,仍被一支仅数百人的“国·军”(国民革命军)坚守着。
该部本有人员和败逃的散兵游勇,总计起来,对外宣称有八百之众,以仅有的微薄武备和更微薄的生活补给,明知必败而戮力死战,不退不降,以决死意志苦战,为抗战重书壮烈篇章……
那是一场消磨、对峙、围攻与被围攻、只有“道义”的意义而完全不存在胜负悬念的坚守战,一场所有中国军人都抱定以身殉国决心的决死战;我方军队据守的四行仓库背临苏州河,对岸的租界,尚不在日军武力覆盖范围之内,就出现了一河之隔一边是炼狱一边还是和平状态的特殊状况。
身处“安全”的租界中的国人,大批临河持续观战,声援中国军队的同时,也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其中有一个关键动作,就是向对岸四行仓库中国守军投递通讯线缆。
影片中,未具名甚至连正脸都没有的“大佬”,就地摆开“生死局”,重赏招募勇士徒步奔跑向对岸递送线缆。
为阻止中国守军得到线缆,日军以强火力覆盖“边缘地带”,在由租界方向奔来试图递送线缆的人员堪堪“越界”时即将其射杀;很多人奋勇尝试,都功败垂成、喋血“边界”,给守军送去线缆,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万难之际,绰号“刀子”、影片中操川贵口音的“上江帮小子”,自告奋勇,发挥跑得快的特长,踏着诸多前行者的血泊,逞博命大勇,拼死尝试,虽被日军射伤,仍披血前行,最后奋力一抛,瞬间中弹殒命,抛出的线缆却终于落到中国守军可及位置,完成了递送使命……
影片感人之初颇多,“刀子”舍命抛送通讯线缆一节,实在只堪为“插曲”,还是短短一闪即逝的那种,却在笔者的感观中留下很值得思考的浓重一笔,理由很简单——在那实在可谓“壮举”的行动之前,“刀子”这个人物的“定位”,是个流氓;而从影片的展现来看,刀子,也的的确确,是个旧上海挺典型的流氓。
一个流氓、混混,怎么忽而就成了忘死无畏的“英雄”?耍短刀(匕首)流里流气与人“论江湖”的他,真的能算是“英雄”吗?

(二)乱世中的上海滩“流氓”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季云天、虞洽卿……如果对旧中国的上海多少有些“间接知晓”,就不难从认知中搜罗出这些人名,还有“次一级”的王亚樵、马永贞等等,在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如果提到(大概率不会提到),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称谓——流氓。当然,“顶级”和一些“出挑”的“次一级”,也就是上面不完全列出姓名的那些,“流氓”之前,会冠个“大”字,称“大流氓”(早前也这么介绍“投机革命”之前的“蒋某人”)。
之所以“流氓”、“大流氓”,当然,也是很有事实依据的;但之外,还有个重要标志,就是“在帮”,即:他们都是帮会分子、帮会头子、大头子;而帮会,则被“定义”为“流氓组织”,时兴点儿,也可以叫“黑社会”。
旧时代的“黑社会”或说“帮会”,客观点儿说,算是一种亦正亦邪的存在,不完全是“恶”的,当然,肯定也称不上“善”。由于其形成与发展的形式、途径、历程,多样且复杂,到一定规模时,就势必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具体到“十里洋场”的旧上海,多重复杂缘由作用下,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交迭之际,帮会,既是社会毒瘤,也多少承载着某种“秩序”的“维持使命”,构成政治颓败的乱世中一种畸形社会现象。
有关帮会和旧上海帮会,实在是庞杂话题,并非本文的关注,只简单说两点——
帮会的“恶”或说“危害”,绝对是“行为主流”;但在特定历史时期,其“恶”或说“危害”,也有参差;很大程度上,这样的参差,更是首领的个性及其对帮众乃至所控制区域、领域的影响所致。比如:被称“老板”的“先驱大佬”黄金荣(黄老板),吃软饭起家,贪财好色、欺男霸女、买权谋私、黄赌毒俱全,可谓罪大恶极;但好面子、重虚荣,且说不上“智勇”,充其量不过“简单”的“社会毒瘤”而已。
行伍出身的“后起”张啸林(张大帅)则乖张狠戾、好斗嗜杀、侵财掠色毫无底线,骨子里恶性昭昭,终成汉奸。相对“口碑”稍好的杜月笙,起于微末、擅长结交、权谋深湛,且注重维持、资助为数众多的底层帮众(劳工),化解诸多矛盾,对抗战做出过一些积极贡献,以至于在某些“圈子”里被“称“先生”(旧时代“先生”之称有表达尊重甚至敬仰的意味,而并非笼统的指代称谓)。
随着包括“北伐”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大事件以及日寇始于1931年的武装入侵(九一八)和随即由局部到全面的抗战,东方最重要的工商城市上海,先于大多数国内其他地方,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旧有的“帮会秩序”,逐步消解、淡化;帮会,作为特殊离乱时代的畸形存在,也相应退缩到了愈加边缘的境地;随着抗战胜利,撤销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相当程度依附老牌帝国主义的旧上海帮会“主流”,基本“下台”,至新中国成立,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了永远的过往。

(三)“刀子”从流氓到英雄的心路历程
旧上海的帮会“世界”,“暴胀”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交迭时期,在二三十年间,形成庞大复杂的松散体系同时,也呈现出“鄙视链”——以宁波及周边地区旧“漕帮”为“主流”的“甬帮”(宁波简称“甬”),彻底取代洋务运动前后先期“登陆”上海的“潮帮”(潮汕商帮),以“青帮”(可理解为旧漕帮的社会性扩展)为基础,占据“顶端”。
随即兴起的“本帮”(上海本地及相邻苏杭地区)则以杜月笙(上海郊区人)为典型代表,与“甬帮”积极融和,有的跻身“顶端”,有的则成为发端于长江下游其他地区被称“下江帮”的“次级”帮会群体的“头部”;而由于战乱等原因,从长江中上游地区“辐射”到上海“捞世界”的众多大小帮会,被称“上江帮”,虽带个“上”字,却处在“鄙视链”底层。
前述电影《八佰》中的小人物“刀子”,从口音判断,该是川贵人士,其老板(女老板)或称“龙头”,大概率就属于“上江帮”。

注意,真正“论得上”的,是他那个女老板(刘晓庆扮演),他本人,充其量也就是个在桥头靠无赖手段盘剥路人的混子,纵然匕首耍得翻飞,也完全不入流。女老板对他有恩,所以他还能随侍左右,但不等于内心没有“攀升”之欲。
混世界的主儿,眼界主要还是围着帮会,同样适用“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通则”;骨子里,他是想“向上”的;但作为“上江帮”的“小子”,实在缺乏攀升阶梯,所以也就只好跟着大概率也就是“挂名在帮”的女老板混,把“冲天”的“抱负”和不得伸展的怨怼,发泄给还能欺负一下的陌生人。
河对岸“华界”四行仓库国·军螳臂当车般与“大势已成”的日寇殊死周·旋的壮举,无疑刺激了他作为青年男子的“血气”。看着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却都没成功、血洒魂断,庸人的怯懦和男儿血性焦灼着没什么见识也不怎么聪明的他。彷徨之际,旨在招募勇者向中国守军投递通讯线缆的“生死局”,让他看到“进身”契机。主持生死局的大佬,有人猜原型就是杜月笙,可能性不大——作为当时上海滩帮会最有势力的人物,杜月笙本人,不大可能亲自出面那样的场合;但因为事关重大,主持生死局的那位,也应该是颇有地位的“爷叔”。
如果看过电影,并且注意了“刀子”的行动线,就不难记得,“刀子”拜别于之有恩的女老板后,奔到生死局前,匕首戳上桌面,对那位大佬口称的是“师父”——青帮讲辈分、论师徒,“师父”不是随便叫的,真正“入局”,得递有人担保的“门生帖”。很可能,激战当时,特事特办;至少“刀子”是这样希望甚至是这样理解的;配合着跪拜的一声“师父”,等于表明了冒死的“条件”——不要赏钱,事成也好,没成死了也罢,都请收我为徒……从他的角度讲,这也不能算是纯粹的投机,毕竟,他是在拿性命“奔向理想”!
这样的话,“刀子”舍身投递的壮举,好像还是带着明显的功利心——鄙视链底层的野路子流氓的想当成“正牌儿流氓”;但是,莫说大几十年后的现在,就是在人命如浮萍草芥的当时,即便在“亡命徒”居多的流氓堆儿里,又有几人能把命赌在助战抗敌的事情上!
年轻、不懂事、没见识、冥顽流气的“刀子”,在“获准”参加行动的那一刻,或许还想着以性命博“前程”;但敢不敢说,背负上要投递的线缆,向着战场或说“死亡”飞奔的那一刻起,他年轻不经事很可能相当简单的头脑里,就只剩下了一件事——把东西送到!
奔到半途开始“领略”侵略者凶器射来的阴风时,“中国人不受欺”的念头,会不会占据主流?终于中弹喋血那刻,“狗日的日本鬼子,老子跟你拼了”,会不会成了唯一信念?会的话,就可以说,那一刻起,小流氓的“刀子”,几乎就成了“大英雄”!

躲在今天的和平安全中日日喊打喊杀的那些“侠”,互联网牵头打旗声讨这个控诉那个的“人杰”们,换到大几十年前“刀子”的位置,敢不敢赌命?肯不肯舍命?有没有勇气迎向侵略者的子弹,而有机会为国喋血?有没有明知下一秒铁定是死还拼尽最后力气不要命地把线缆抛向目的地的意志力??
以上诸问,只要有一个含糊,就真还不如旧上海的小流氓“刀子”!
“刀子”或许算不上英雄,但骨子里存着男儿真性情。
“刀子”或许终究也还是个流氓,可躲在和平的安全中喊打喊杀的ta们,却连那样的流氓也都还不那么配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