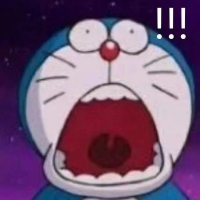高一那年,家里突然多了个弟弟。
才刚踏进家门,我妈一脸神秘指了指我的卧室,「走路小声点,你床上躺着个崽子。」
「什么崽子?」我撒腿想推门去查看究竟。
直觉人生马上就要变天了。
1
老旧的木架床上果然有张红毯子,里头包着个婴儿,眼皮还没睁开。
他似乎被我吓着,开始啼哭不止。
我情绪激动,「是你们从人贩子那买来的,还是偷来的?不赶紧送他走,等着我报警?」
我爸暴怒的声音随即传来,「花钱养大你,敢恐吓起老子来了?」
他抬手就给了我一耳刮子。
此前他常年在外修路,掌劲大得很。
眼泪瞬间模糊眼眶,我忍住不哭:「没错,我是吃家里饭长大。可你别忘了,都是我妈一把屎一把尿带大我。你邀什么功?」
我爸常睡在工地,每年在家的时间从不超过半个月。
我都长到十五岁了,跟他还异常不亲。
我妈语气强硬,更像是在通知:「以后他就是你弟,你不认也得认。」
我还没说什么,只见我爸气到脸色黑红,抡起墙角的扁担朝我砸来。
「狼心狗肺。不是我在外边没日没夜干活,你能有机会念高中?」
「书别念了,过完年就跟你姐进厂打工。」
我没来得及躲,肩胛骨狠狠挨了一棍,浑身疼得快散开。
我妈见我迟迟没反应,吓出尖叫,「下手可别太狠,伤了骨头可得花钱。」
眼见扁担又要落下,我打了个激灵迅速闪到门外。
身心的重创,让我失去理智愤怒嘶吼:「要留下他,我就跟你们断绝关系!」
大不了,我真不念了。
我爸瞪着的眼露着凶光,吼得比我还大声,「断就断,你以为我会在乎?」
我的人生果然毫无预兆的要变天了。
2
我出生在南方一个极度闭塞落后的村子。
上边有个姐姐,大我十二岁。
那会计划生育抓得严,讲究工人一胎,农民两胎。
我爸恰巧是有正式单位的修路工人。
为了生二胎,我妈跟着他躲躲藏藏好些年,中途还不幸流过产。
三十六岁那年,好不容易再度怀上。
跛子奶奶跟我爸都对她寄以厚望,想一举得男。
我妈想吃酸,我爸就常拉回几箱酸梨跟酸枣。
奶奶不顾左腿不方便,还专程花钱去离家远的山村问神婆。
确定我妈能往家里添个孙子,养好了一大竹笼母鸡。
孕末期我妈体重超标,得了妊娠期糖尿病。
费了快八小时还没生下我,很是危险,医生只能用剖的。
听说我一出生便啼哭声洪亮,产房护士笑着跟我爸报喜。
「王师傅,是个千金,六斤八两。」
我爸当即沉下脸说不出话,缩着手迟迟不肯来抱我。
奶奶如遭雷劈,在走廊捶胸顿足:「来福,瞧你娶的瘟神。折腾了十几年,半个带把的都生不出来。」
「这是要我们王家绝后!吃的那些鸡,还不如喂狗了。」
我爸铁青着脸抱我进了病房。
我妈刚缝好针,面色苍白如纸,看了看我的身体差点晕过去。
等她回家坐月子,奶奶干脆敷衍,只煮些蛋花汤给她喝。
还泄愤般把剩下的几只鸡宰了自个吃,吃不完硬塞给我爸。
轮到给我妈端饭,就没少冷嘲热讽。
「生不出儿子,又一身病,招呼你饭菜都便宜你。]
「亏我到处请神,生出这么个赔钱货。」
奶奶连生两个儿子,却都没留下孙子。
骂完我妈,又骂我爸:「我就是死,也闭不上眼。外地婆死不中用。」
我爸气得摔了碗。
我妈小学毕业,二十出头从邻省嫁到我们村。
她在这没别的依靠,这更加造成她的盲从与懦弱。
月子坐到一半,家里又出了事。
我妈被妇女主任带的几个人架上车前往卫生所,当天就做了结扎手术。
从此,奶奶跟我爸更看我妈不顺眼。
我妈更是一肚子怨气。
生下我家里便断了根,我成了全家的出气筒。
饿到啼哭不止,我妈没什么奶水喂我。
我爸听着烦,买回几包劣质奶粉,一天就只冲泡几勺。
稀释的奶粉几乎成透明色,奶奶还在往我嘴里塞。
后来,村里薛支书来催着上户口。
他们随便看了看,便给我取名「王梅娣」。
薛支书眉头紧皱,「这名字,听着别扭。」
我爸狠狠剜我一眼,「谁让她命薄?身上不多长点。」
到我两个月大,跛脚奶奶抱我时没坐稳,双双从门前的石墩狠狠摔在地上。
我惊吓到大哭,奶奶也突发中风没能救回来。
她死后,我爸更认定我是个扫把星,是来家里讨债的。
3
打小我就体弱多病,上学后成了班里最瘦的孩子。
家里泥墙砌的老瓦房,特意留出个能供狗进出的洞。
有时我妈干农活忘带钥匙,就推我进洞帮她开门。
大伯经常比划着食指中指笑我,「梅娣,手腕还没我两手指头粗。」
一次我发烧到半夜,烧到双眼通红。
我妈骂骂咧咧起身:「讨债鬼,生你那会差点害我丢命,被婆婆老公骂,上辈子我欠你的。」
我难受到哭。
骂归骂,她还是到屋后找了大伯,连夜带我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
医生帮我量了体温,让我张嘴。
看完,他眉头一皱:「老毛病,扁桃体肿大。经常注射青霉素对身体不好,不如带去县医院割了?」
我都记不清因为这问题发烧几次了。
针扎进屁股,我疼到直叫,是大伯抱住了我。
「手术一定很贵,她爸又很少寄钱回来,我哪来的钱?」我妈甚至没做了解,直接下了定论。
医生也不勉强。
回去的路很黑,我趴在大伯背上。
我妈在后边拿着手电照明,又一路抱怨没儿子多命苦。
在爸妈眼里,我跟我姐似乎都毫无价值。
为了让我妈看见我,从小我就静得下心念书,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
除了前桌男同学总拿班级第一,第二名基本是我。
为此,我在村里有着不错的名声。
同学大浪他妈,曾在我妈面前夸我。
「梅娣虽然是女娃,脑子可真好使。不像大浪,门门考个二三十,鼻涕泡都收拾不利索。」
我妈难得挣了面子,笑着回:「可你家大浪,能给你养老。」
见夸我的人多,她才对我稍微客气些,偶尔愿意拿几毛钱给我零花。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能花一毛钱买包酸梅粉,我都能开心老半天。
七岁那年的冬天。
我爸回家过年,跟大伯聚在桌上喝酒。
黑白电视机里正在播放春运的画面,火车站很多人赶着回家团圆。
大伯喝了半杯聊起我。
「梅娣是块读书的料。将来考了大学,也能带你们坐火车。」
村里人大多没去过外边,觉得坐火车就很高级。
我爸放下酒杯,语气怀疑,「读得再好,长大了也得嫁人。谁知道她有没有良心?」
我妈坐在附近的矮凳上瞪我,「她敢?真那样就送她去山里。」
大人都说,送进山的孩子要么给人当童养媳,要么被弃养生死未卜。
我的头皮一阵发麻,表现得异常乖巧,「妈,我才不要去山里,长大我一定有良心。」
4
被我爸打后,我拎起书包往外跑。
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原来他们一直在谋划养个儿子。
那是一天夜里,遇到村里白事做道场。
刚失去亲人的村民一阵阵哭丧,道士手里的铙钹彻夜吹打。
我单独睡实在害怕,只能去敲爸妈的门。
我在旁边小床睡得迷糊,隐隐听到我爸在说:「大荣那对双胞胎不错,他答应过继大的给我们。」
我妈立刻反对:「不成,勇子只比梅娣小一岁,认得清亲生爸妈。养了也是白养。」
我爸不耐烦,「能怎么办?躲了那么多年,还不是生出个讨债鬼?」
又受了气,我妈立马跟他闹。
「谁让你常年不着家?见我被抓去结扎,屁都不敢放一个。」
面对没有儿子的现实,爸妈的心从来就没死过。
正当往外走,我妈追上来扯住我,「你倔什么劲?最好接受你弟,闹下去对你没好处。」
我完全听不进去。
我爸无情的训斥,在身后回荡。
「我看她能去哪?离了这个家,她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我跑到离家很远的田埂,早已饥肠辘辘,脚步却停不下来。
回头看向那幢养了我十几年的瓦房,那一刻好像没有家了。
我亲生父母,尤其是我爸,因为一个来历不明的「儿子」跟我开战。
在快出村的桥头,我遇到了兰婶。
兰婶见我双眼通红,笑得不怀好意。
「梅娣怎么哭了?听说你爸妈前天领回个儿子?」
「知道不知道,你弟怎么来的?」
「你爸今年五十五了吧?没生出儿子总是不认命,一把年纪瞎折腾什么劲。」
我妈从后边追上来,气到开骂:「消息都挺灵的?我儿子怎么来的,有义务告诉你们?」
兰婶跟我妈年纪相仿,「好命」地生了三个儿子。
各个都在广东打工。
她看向我妈一脸挖苦,「心还挺宽。老公从外头带回个野种,当了现成的妈。」
「小心哪天他再领回个小老婆,把你家给占了。」
我妈气到脸色发青,硬生生说不出话。
谁让她没生出儿子受尽委屈,腰杆直不起来。
我极度难堪气愤,「不准说我妈,说我家。你有三个儿子也没什么了不起。」
兰婶气急败坏,干脆冲我诅咒。
「死丫头,接下来有你受的。」
「家里多出个野种,爸妈就更不稀罕你了。」
5
遭遇羞辱我还要回嘴,我妈拉扯我到了旁边,「翅膀还没硬呢,想跑哪去?」
我们坐在田埂附近的竹林,母女头一次严肃地交谈。
身上的疼一阵阵的,我说话不太利索:「回学校,继续读书……」
女娃考上高中本来就不容易,何况我考的是重点。
那会我心思单纯。
想着靠读书出人头地,就不用跟其他女娃那样早早进厂跟嫁人。
我妈脸色透着往常的淡漠,从兜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先拿去用着,买点跌打药。你弟的事,不要管。」
「村里人笑话你们,笑话我。也不让我管?」
毕竟我爸已经五十多,靠修路拿份苦力钱,不是什么有钱人。
顿了顿,我追问:「我总该知道孩子哪来的?」
我妈的答案,却让我无言以对。
「你管他哪来的,没偷没抢。那么多人都能养儿子,我跟你爸为什么不能?」
「要不是因为生你结扎,我能没机会自己生?」
爸妈老来得子,对两个亲生女儿没多少感情,心自然偏到了太平洋。
两人特地挑了个喜庆的日子,在家门口席开三桌给我弟办百日宴。
席间。
常年不修边幅的爸爸换了新衣,紧搂儿子招呼客人,像到达人生巅峰般神采奕奕。
我弟从毯子里露出个头,笑得天真无邪。
「来福还真是福气来得晚,这崽子连笑都像你。」
「赶紧联系王家主事让娃进族谱啊,取个响亮的名字。」
空气中,到处飘着彩虹屁。
我爸看向我弟,越发乐得合不拢嘴。
他本来不抽烟,硬是给客人安排了好几条红塔山。
偏桌的一群女亲戚,则连看都不带不多看一眼的。
外省来的姨婆跟城里的表嫂坐一起,悄悄聊起我弟。
我瑟缩在椅子上听。
姨婆思想古板,跟我爸妈一样陈腔滥调。
「他们苦了大半辈子,将来终于有儿子送终了。」
表嫂的眼神飘向我,「我看是嫌苦日子不够长,梅娣都念高一了还养儿子。」
姨婆立马不赞同:「女娃大了要嫁人,总归得靠儿子。」
我刚想说话,表嫂抢先一步。
「他们要无灾无难,养大好儿子都七老八十了。儿子娶老婆还得出彩礼,能不能靠上不好说。」
「梅娣可就不一样。等考上大学能挣钱,没准还跟着享福。」
她心疼我,劝我多吃饭长结实,别怪爸妈。
寥寥几句,让我越发不是滋味。
自从有了弟弟,身边所有人都在围着他转。
不久我妈走过来,姨婆又开始八卦我弟的来历。
我妈上桌音量极低,「山里一个没结婚的女人生下来不要的,给点钱打发了。」
姨婆好像在听家常便饭,「估计是怕带着个拖油瓶,往后不好嫁人。」
那会村里很多夫妻超生躲计划生育,女多男少,弃养女婴的事经常发生。
弃养男婴,我也是头一次听说。
可能这就是我弟的命,生下来就被亲妈丢弃。
他跟我一样没得选。
6
不知道我爸得罪了谁,很快就有人把他养儿子的事捅到了单位。
麻烦跟着上门。
单位派人到家里来核实后,我爸被开除了。
原本他还想再撑几年,靠退休金养老,养儿子。
这下直接没了盼头。
短短几天,他急到头发花白一片,面容比常年饱受风吹日晒还要沧桑。
可到底有了儿子,苍老的眼底始终有光。
单位那份工资没保住,只能再谋生路。
他拿出大部分积蓄在村口租了个店面开了家小卖部,一大早便踩着二八自行车到城里进货。
为了卖更多货,他一天能在村里跟城里来回两三趟。
我妈也不闲着,背着我弟在家养猪种菜种田,继续包揽所有农活。
而我为了保住上学的机会,尽量避免跟他们争吵。
只要在家就去店里帮着卖货,分担家务。
可家里到处堆满婴儿的衣服和烂布条,上边沾满屎尿。
空气里弥漫着浓厚的尿骚和屎臭味。
我收拾着烂摊子,渐渐被磨得没了脾气。
好不容易闲下来,屋外的阵阵啼哭哄笑让我根本静不下心看书。
后来我一咬牙,干脆每月回家一次。
一中人才济济,数千号人都是从县里十八个乡镇选出来的尖子生。
除掉部分自费生,我的成绩成功垫底了。
期中考后,我拿着不及格的试卷回去签字,顺便通知下周末开家长会。
我爸在厅里给我弟喂奶,一见我回家视线直接避开。
餐桌上摆着几罐当时很贵的完达山奶粉,是我永远都喝不上的。
一个月,我弟就要喝掉好几罐。
看到试卷我爸脸色一黑,丢下奶瓶劈头盖脸骂我。
「越大越蠢,数学五十八?天天在学校梦游?浪费家里血汗钱。」
「要是考个三本大专,一分钱都别想我出。」
乡下人都说起码得考个二本,才算得上正儿八经的本科。
三本是花钱买来读的野鸡大学。
至于大专,读了三年没工作分配,钱跟打水漂没什么两样,不如提前进厂。
从小我就活在他的语言暴力下。
对上他看仇人般的眼神,比我妈暴脾气时拿鞭子绕着屋子追着我打更恐怖。
那晚,我赌气没吃饭,躺在床上发呆。
还是我妈推开门,悄悄给我捎了两个鸡蛋。
她虽然恨我,却又一手带大我。
「你爸嫌丢脸,家长会让我去。加上他人木讷也没兴趣。」
我多少懂他们,不客气冷笑,「对,他的兴趣都在带儿子身上。」
「爱吃不吃。」我妈气得脸涨红,丢下鸡蛋走了。
7
过去我除了守着书桌拼尽所能证明自己有用考上一中,似乎从来都忍气吞声。
有很长那么一段时间,我变得迷茫。
那会县里刚开起一家网吧,一块五一小时。
我不敢在晚自习期间翘课,保守选在周末上网。
用的是省出来的饭钱。
网吧内乌烟瘴气,很多杀马特男女,热火朝天在玩最新款的游戏。
我这乡下人见了世面,只敢申请个QQ聊天,听听歌什么的。
估计一中的校服显眼,有人跟班主任廖老师打了小报告说我在网吧逗留。
他很快联系到我家。
爸妈由表嫂带着,在网吧内成功找到了我。
我爸背着我弟进门就招呼我耳光,连拖带拽扯的。
「死丫头,考倒数还出来上什么网,染上病毒怎么办?老脸都被你丢光了。」
那些杀马特男女,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们。
一个男生吹起口哨,「乡巴佬,上网还能得病。带个崽子哇哇哭,吵死人。」
出了门,我的脸都被打肿了。
在一家超市入口,我见到迟些赶来的廖老师。
爸妈一个劲跟他道歉,说没教育好我这类的。
廖老师很和善,带我们在附近找了椅子坐下。
还花了几块钱,给每人买了碗凉粉解暑。
我妈不满地瞅我,「家里给你钱吃饭,都花去上网了?面黄肌瘦的该不会真染上什么病了?」
「信不信你在外边饿死,我都不管了?」我爸也怒冲脑门。
我垂着头,不看他们。
廖老师了解到大概,倒是没责备我。
只说我成绩不好可平时还算安静,胆太小特别不爱说话这类。
「孩子青春期容易走错路,当父母的父母尤其要注意。」
我爸嗦完凉粉,不忘哄身后乱蹦乱跳的弟弟。
「她不争气,关做父母的什么事?」
廖老师欲言又止。
我妈继续训我:「不抓住高中三年,除了打工你只能嫁人。」
我长久紧绷的神经终于崩溃。
「你们从来这样,说什么做什么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们真把我当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