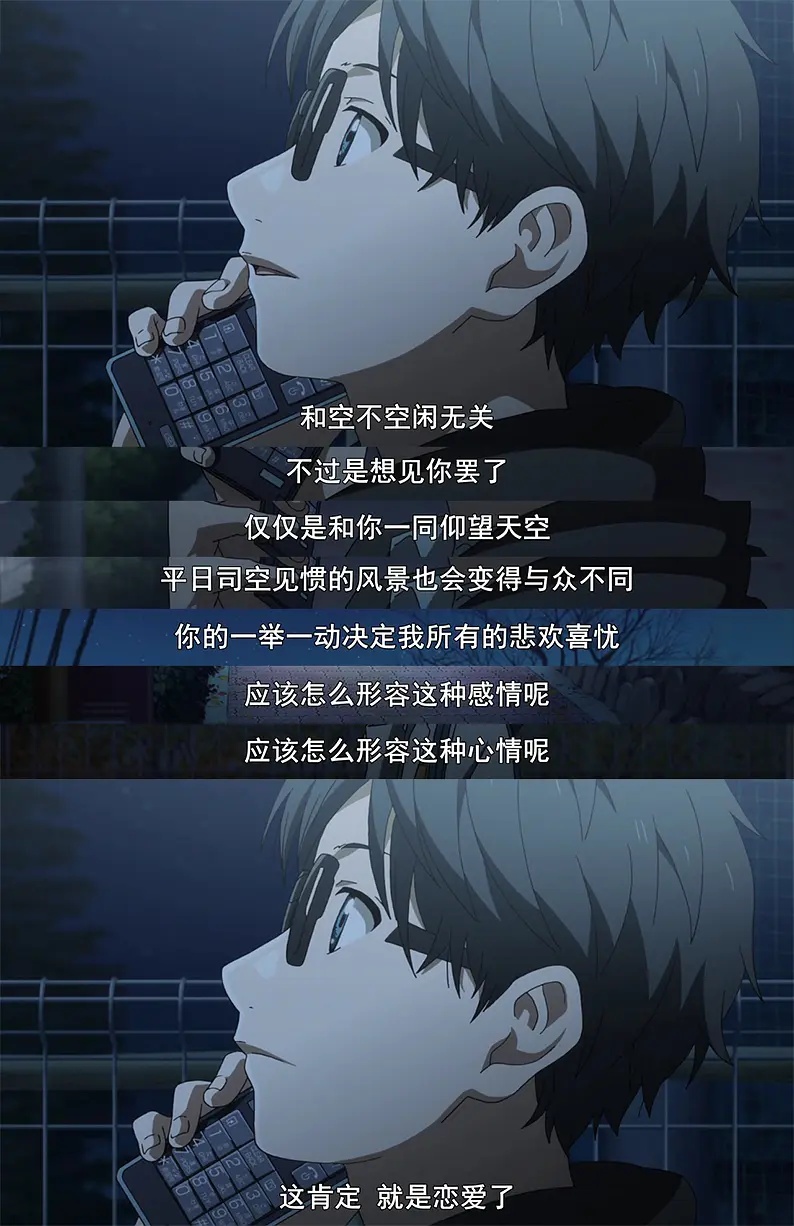暮色中的樱花开始凋落时,我忽然明白有些相遇注定是命运写错的诗行。
宫园薰躺在病床上数点滴的声响,像极了那年我们在废弃琴房里,用铅笔敲击节拍器的节奏——清脆,单调,却能让人在寂静中听见彼此心跳的轰鸣。
她总说自己是"为守护某人而生的恶魔",却在东京塔的玻璃幕墙前露出少女最本真的笑靥。
当我说出"你弹琴的样子像在焚烧日记",她突然把发热的额头抵在我肩上,发梢残留着消毒水的气味。
那些被谎言包裹的午后,我们其实都在用音乐修补残缺的魂魄,她用肖邦的夜曲覆盖化疗时的耳鸣,我用巴赫的平均律对抗记忆的撕裂。
最痛的不是告别时刻的樱花雨,而是某个寻常周三午后。
薰把改编的乐谱塞进我琴盒时,指尖划过泛黄的纸页,像抚摸新生儿般轻柔。
她永远不会知道,那个在站台追着列车挥舞乐谱的少年,口袋里还揣着她偷偷塞进的止痛药说明书。谎言编织的羽翼有多轻盈,真相降临时就有多沉重。
如今每当我翻开那本被泪水晕染的乐谱,总能看见四月末的黄昏在她瞳孔里凝固。她说谎时睫毛颤动的弧度,比任何肖邦夜曲都更接近永恒。
或许有些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场盛大的即兴演出,当帷幕落下时,留在空中的余韵比完整的剧目更令人心碎。
暮春的樱花又开始纷飞,我站在新宿车站的背阴处,看着穿校服的少男少女们嬉笑着穿越轨道。
突然想起薰曾说:"真正重要的旋律,往往藏在休止符里。"此刻春风卷起满地落英,恍惚间又听见那架老钢琴在雨中独自吟唱,每个走调的音符都是未及诉说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