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愿远在天堂的母亲能永远面对我微笑 ——这场展览献给您

妈妈,时间过的真快,您离开我已经四年了。但在我的觉知里您始终像神祇一样在护我周全,同样也始终未觉得您已离开。直到这场展览开始的前夕,您切切实实的走进我的梦里,嘱咐我要更加爱惜自己,珍爱生命中的人,要勇敢前行……我在大梦初醒之际才真正体会到了天人两隔。我才彻底明白您真的不会再回到这个世界了,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在爱护着我,凝望着你的儿子。但是您知道吗?这种诀别真的是一种无边无际的痛楚啊!
妈妈,我想告诉您我现在很好!依旧努力,依旧热爱生活,依旧是那个您眼中的儿子,依旧以您为傲!只是会时常想起您伴我走过的人生路,点点滴滴的温暖填满了我记忆。挺好!这种思念,这种回忆真的挺好,让我感到生命的富足和爱。我是在“母爱”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这对我很重要!那些“爱”片段始终会在我的脑海中闪回,正是这些,让我懂得了如何去拥抱生命,如何去关爱生命中的人。
我对艺术的热爱,源自您对我的一贯鼓励与支持。我从小便不是那种天资过人的孩子,是您教会了我“勤能补拙”,教会了我“笨鸟先飞”,告诉我“坚持与认真”的力量。这份“笨拙”在您的引领下逐渐让我获得了许多踏实的本领,让我渐渐自信,不彷徨……
妈妈,谢谢您!
前几日,我读到了袁枚的《苔》:
白日不到处,
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
我想说:妈妈,这就是我眼中的您!
我很想念您,我的妈妈!

与策展人在展览布展现场

开幕式当天观众等待入场







艺术家访谈录
策展人:Claudio Rocca

于:1977年我出生在中国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由于父母都是军人,我们后来又随部队搬到了辽宁省的本溪市。本溪是一座被美丽的山脉、小溪和河流环绕的城市。也许正是这种经历激发了我对风景画的兴趣。后来,我随父母搬到了老家山东省淄博市。在那里,我住在齐鲁石化这样一家大型化工企业的生活区中。
记得在小学三年级的暑假期间,父母把我送到中国画班,在那里我遇到了潘思剑的老师,他在齐鲁石化公司的工会工作。潘老师是我的第一位中国水墨画老师,也是我在美术方面的启蒙老师。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对绘画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以至于课后为了画画常常忘记午休。父母还为我购买了中国画用的毛笔、“一得阁”墨和宣纸。就这样,我算是初步了解了中国画的特点,并背熟了谢赫的《六法》。当时我的年龄还很小,未能完全理解这些法则;直到后来我开始正规的艺术学习,才真正明白它们的重要性。
改变人生的“转折点”与一封信有关。那时父母为我剪下了许多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其中许多还只是黑白图片。由此,知道了些著名的中国画家,如齐白石、李可染、李苦禅、潘天寿... ...其中我对李苦禅特别喜欢,并且知道他曾是齐白石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记得是在1988年,我让母亲给李苦禅写了一封信,恳求他收我为徒。 信发出去了,但我们从未收到回音,仿佛石沉大海。于是,我请求母亲带我去北京亲自寻找李苦禅先生,请他收我为徒。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母亲同意了我的请求。在北京我们找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并向学校的老门卫打听李苦禅。老人惊讶地告诉我们,大师早已去世多年,并问我们找他的缘由。我回答说“我想成为他的学生。”老人建议说,以我这么小的年纪,去找一位大画家做徒弟是不现实的,不如先报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系统学习绘画。就这样,我在几年后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没想到从此我的人生便与中央美术学院结缘。现在想想正是那封没有回音的信指引着我走上了绘画艺术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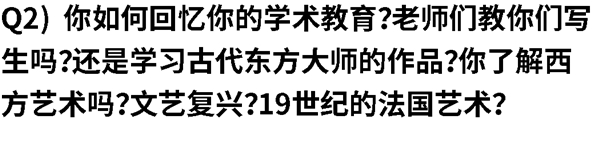
于:我于1993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CAFA),在完成了学院附属中学的学业后,于1998年,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油画系,并于2002年毕业。在中央美术学院期间,我开始了系统的油画艺术学习。早在中学阶段,我就已经坚定了学习油画的决心,尽管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记得在附中第一年,我的素描成绩还算优秀,但在理解和处理色彩关系方面遇到了困难。当时的授课老师认为我的色彩感觉不好,不适合报考油画系。然而,另一位老师却给了我一个宝贵的建议,他说:热爱绘画是最基本的前提,“感觉”是可以通过训练来提升的。这种关于绘画实践的观念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它让我想起了母亲在我童年时期关于日常生活的教导:那就是,缺陷可以通过意志力和训练来克服。于是,我投入了极大的努力开始了密集的训练。剪下小块硬纸板并涂上乳胶水,然后每天坚持画小尺寸的风景油画。这个训练一直延续到今天。老师要求我密切关注色调关系以及一天中不同时间的光线变化。一年多后,我的作品终于得到了最初对我有疑虑的教授的认可,他认为我已经达到了可以进入油画系的水平。这一认可给了我极大的勇气,也让我更加坚信:通过艰苦的努力、奉献精神和系统的训练,艺术的敏感性是可以被培养出来的。
在附中学习期间,我还经历了多种艺术学科的训练,包括人物写生、色彩静物练习、石膏像写生等;此外,还学习了雕塑、中国画经典作品的临摹以及版画课程。后来,本科阶段的课程内容与附中相似,但难度显著增加,教学范围更广,教授们的教学方法也有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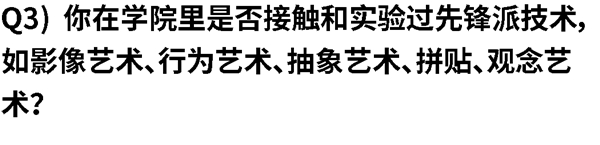
于:在我就读美术学院期间,教育内容丰富多样。学科涵盖了油画、壁画、版画、雕塑、中国画,那时还有连环画、中国年画专业,同时新兴的艺术设计专业也成立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学生们的思想非常活跃,使我们愿意去探索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学院内,有些学生开始私下从事观念艺术和装置艺术的实践,尽管这些不属于正式课程的内容。当时学生们与教授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新的艺术概念,彼此间营造出了一个活跃而富有生气的学术环境。总体而言,学院支持学生追求他们的学习抱负,鼓励进行艺术实践。像徐冰和吕胜中这样的艺术家在当时名噪一时,在学生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90年代,美术学院的学生充满了新思想,但同时也有很多困惑。很多人在思考艺术是否还应该遵循传统模式,是否应该演变。那段时期被记忆为一个充满激情和思考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疑虑和矛盾的时代。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学习,现在我有一种感慨:如果时光能让我回到大学时代,我会更加专注研究绘画的本体问题,对自己的选择不再犹豫。


于:为了深入理解19世纪的法国艺术,我于2006年在上海开始跟随徐芒耀教授学习油画技法并 从2010年起攻读博士学位。这里我特别指的是19世纪中后期法国沙龙(Salon)艺术,即那些所谓的学院派艺术家。在此之前,我们对安格尔等艺术家以及后来的印象派和后印象派有了一定的了解。然而,像梅索尼埃、杰罗姆、布格罗、卡巴内尔等法国沙龙艺术家我们却知之甚少。他们尽管在当时的法国乃至欧洲享有盛名,但后来却几乎从艺术史中消失了。这种遗忘的原因有很多。但近些年,他们的艺术光辉重新被挖掘出来。
自2006年以来,徐芒耀教授开始向我介绍那个艺术时期的相关信息。那时,我对梅索尼埃特别感兴趣,甚至可以说是着迷。于是在2010年,在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以沙龙艺术为研究重点,并把梅索尼埃作为个案。2013年,中国美术家协会派我去法国研修,我有幸结识了彭昌明教授,她是研究19世纪艺术的专家,特别是对高蒙和达仰有深入的研究,她也成为了我在国外研究博士论文时的导师。在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彭教授给了我许多指导,建议 我去参观法国各地的博物馆,去观察研究那个时期的艺术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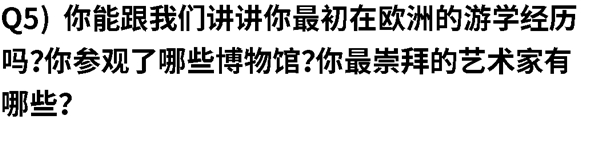
于:我第一次到国外参观博物馆是在2009年,当时去了俄罗斯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此后,我几乎每年都出国旅行,参观欧洲各地的博物馆。2013年,中国美术家协会派我前往法国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学习。在学习期间,我继续沉浸在博物馆中,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到卡拉瓦乔,然后是委拉斯凯兹、伦勃朗、维米尔、夏尔丹,再到19世纪的法国艺术家,如安格尔、德拉克洛瓦、莫奈、梵高、高更、纳比派、塞尚等都是我研究的对象。2017年,我首次前往美国,因为我的画作《在布拉格》在“美国肖像画协会国际肖像比赛”中获得的第一名。这是中国画家首次在国际重要比赛中获得比较高的奖项。2018年,我又在ARC国际艺术大赛中获得了金奖和其他多个国际奖项。此后,我连续几年参加了美国的一些比赛。在第一次美国之行中,我参观了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和弗里克收藏馆。随后,我还参观了波士顿、费城和洛杉矶的博物馆。
我也特别喜欢美国艺术家,如爱德华·霍普和安德鲁·怀斯。我对霍普非常敬佩,因为我认为他的绘画非常有力量,展现了典型的美国生活。这也是我的目标:在绘画中找到典型性和永恒性而不是猎奇性。基于此,上面提到的这些艺术家在我眼中是无与伦比的巨匠。在抽象艺术家中,我欣赏罗斯科、蒙德里安和波洛克。我钦佩他们作品中高超的艺术品质。我的艺术风格可能看起来是理性并且抒情的,类似于安格尔,但我对各种风格持开放态度,并愿意从各类绘画中汲取灵感,我认为任何形式的绘画,在审美的追求上都是一致的。








于:除了在西方的旅行经历之外,还有很多旅行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从1995年开始,我几乎每年都会前往中国的藏区旅行写生。我的博士毕业创作《捡牛粪》便是描绘了藏区草原上的牧民生活。这些生活在雪域高原极端环境下的人们自由且积极的生活方式深深吸引了我。藏区的地理环境和人物特点非常适合用油画表现。这些旅行经历 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
在欧美的旅行中,我也非常关注当地的文化特色和自然景观。我特别喜爱那些历史悠久的城市,那些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找到过去痕迹的小城市。幸运的是,我从小便养成了随时画画的习惯,从而绘制了很多视觉笔记。即使没有时间作画,我也会用眼睛“绘画”,观察光线,还有人物的面孔以及他们与环境的关系。2019年,在北京靳尚谊艺术基金会组织的一次游学中,我再次造访意大利。在佛罗伦萨、阿西西和罗马进行了一个月的研究和学习,这一次我有幸见到了许多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教堂里的重要壁画。马萨乔、波提切利和乔托等艺术家的作品为我带来了丰富的营养。在那次旅行中,我画了很多速写,我认为随时将所学付诸实践是非常重要的。



于:油画是通过造型和色彩的美感来表达的。这是一种基于对“真实性”追求而发展起来的艺术形式。与东方文化不同,西方文化强调真实性,我指的是相对于描绘对象的真实性,它成为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真实”再现。而东方绘画则基于抽象的图像和艺术家从自然观察中发展出的各种风格化和概念的范式。在印象派艺术家中,我认为莫奈是非凡的。莫奈在户外绘画方面尤为出色。有些人认为他过于草率和流畅,不如毕沙罗那样真诚,也不像西斯莱那样富有诗意。然而,当从远处观察画作时,莫奈的作品所产生的视觉冲击力是最强的。他在画面内部关系的安排上具有超群的能力。他通过观察创造出了一种抽象的美,在这种美中,人们可以欣赏到丰富的变化。这种抽象关系正是美的所在。我钦佩莫奈在提炼和综合视觉感受方面的能力。我喜欢描绘黎明和黄昏,也喜欢在自然光下作画,因为外部光线比室内光线更复杂多变。当我绘制《黄昏的塞纳河》时,我选择在外部光线下表现作品,因为我认为黄昏的色调深沉而丰富。色调是色彩的灵魂,反映了作品想要传达的情感。在创作这幅作品时,我并没有刻意模仿莫奈的风格,而是专注于他观察事物的方法。



于:我喜欢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场景,因为这些场景对我来说有着强烈的冲击力。我无法描绘我从未见过的东西。我之所以喜爱上了库尔贝,是因为他不带有猎奇的眼光,而是能非常深入的去描绘普通人的生活、工作场景和肖像,还有他目之所及的风景,这些作品极具感染力。库尔贝的作品有着鲜明的特点:色彩深沉,造型坚实,绘画技法既大胆又细腻。他的作品在近看时显得粗糙,充满了原始的质朴感,但从远处看,整体效果却深刻而有力。这说明他驾驭抽象美的能力非常强。因此库尔贝的作品经常给我带来灵感。
在我的博士毕业项目中,我还受到了乌克兰画家雅布隆斯卡娅(TeEana Nylivna Yablonska)的启发,她以作品《粮食》而闻名。我借鉴了她的构图形式和表现外光时所展现出来的水平。我不认为模仿就意味着失去自我,相反,这种站在大师肩膀上远眺的方式倒更能让自己认清自我。通过吸收经典作品的精华来完善自己是终其一生都要做的事。 19世纪的俄罗斯有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苏里科夫、列宾和列维坦的作品。苏里科夫的绘画创造了一种类似库尔贝的“脏”色调交响曲。这些表现抽象美的画作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于:在研究梅索尼埃的过程中,我开始对创作小尺寸作品产生了兴趣。许多19世纪的学院派画家也喜欢采用这种类似于“弗拉芒小画派”的风格。这种风格的顶峰可以在17世纪维米尔的作品中找到。维米尔的造型硬朗、简洁且具概括性。相比他而言,其同时代的其他一些艺术家虽然在细节上表现出色,有时甚至优于维米尔,但从远处看时作品往往缺乏视觉冲击力,缺乏抽象的美感。
19世纪的学院派画家的作品大多通常缺乏抽象性,他们的作品受当时刚刚兴起的摄影术的影响很大。像梅索尼埃和杰罗姆这样的画家都热衷于根据照片作画,认为这些照片提供了更为真实的信息。当时,艺术评论家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Eer)强调对对象、环境和人物的生动细致描述,注重呈现“近距离观看”的美学特质。这一理论主导了当时的美学潮流,导致学院派画家过分关注细节而忽视了整体的抽象性。
对于中国人来说,学习油画非常困难,因为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观察方式与西方人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发现这种艺术的魅力,必须先从改变思维方式和观察方式开始。改变习惯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此我认为学习油画的最大困难不在于掌握技法,而在于如何能建立一种适合这一画种的科学的观看和思考方式。
基于这些思考,我致力于无偏见地研究欧洲不同时代的不同画家的优秀作品。因此,我自然而然地将莫奈、库尔贝、维米尔、伦勃朗,甚至毕加索等艺术家联系在一起,因为我能够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的共同点,我想这应该是我必须要学习的东西。


于:我最初开始绘制自画像是出于必要,因为当时没有可用的模特。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仔细观察镜中反射的自己,我逐渐在这种形象中识别出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熟悉感来自于我的外在形象,而陌生感则源于情绪状态和周围的环境及光线的变化。我的状态在不断变化,在不同的环境中和光线下都会形成一种全新的关系——这使得创作自画像充满了挑战。我可以通过耐心地观察自己,捕 捉特定情绪下的自我形象。此外,画自己让我感到舒适从容。因为我可以耐心地、稳定地观察。
自画像自古以来一直是油画艺术家们所钟爱的主题。像伦勃朗、弗洛伊德、毕沙罗、塞尚这样的艺术家在绘制自画像时,也应该有过与我类似的感受。我对面部表情、姿态,光线甚至衣着都非常感兴趣。一个面孔就足以让我产生情感的振动。一幅作品是否有力量,并不取决于题材的宏大,最为重要的是:你是否真的有话要说。尽管自画像这一主题看似有限,但对我来说却充满了激情。一方面,我通过它提高了自己的技巧,另一方面,我通过它也能够自由地表达我的视觉和内心情感。


于:在创作肖像时,必须捕捉人物的典型特征。我喜欢画熟悉的人,因为我了解他们的典型性。即便是光线的设计也要更好地突出对象的特点,从而能够令人信服地表现出人物。例如,我在几幅作品中都画了一个叫杨音的朋友。最初的几幅画虽然形似,但总觉得缺少点什么。最终我意识到,他最典型的情绪是乐观,是面带笑容的表情。所以我让他保持微笑给我做模特。虽然很辛苦,但结果是创作出了一幅特别像他的肖像。简单来说,肖像画必须“像”其描绘的对象。在中国,人们欣赏东晋时期大画家顾恺之的理论,他是中国“传神论”的奠基人,强调捕捉人物的神韵。这是表现的核心目标。在中国绘画中,一棵树、一座山、一个人物之所以吸引人,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形象本身,还因为其抽象元素。因此,传统中国绘画的方法,其实都是抽象元素的集合。
当我创作肖像画时,不仅要关注对象的典型特征,还要关注其抽象美的表现。许多作品在细节上非常写实,但整体上却显得“虚假”。例如,法国画家大卫的某些作品在造型上缺乏力度,过于圆滑,导致所有人物看起来都很相似。美国画家萨金特的肖像虽然看起来真实,但有时也显得单调甚至不真实。相比之下,像委拉斯开兹、安格尔、惠斯勒在表现视觉现实时更会发现抽象的美感,比如会将一些区域画得模糊,而其他部分则保持清晰,这就是一种主次秩序上的抽象美。因此我认为肖像艺术是一种很有难度的创作形式,它不仅要酷似你所描绘的对象,还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要寻找并构建出整体的“抽象美”。


于:在我看来,我并不认为艺术家或艺术作品应该被划分为古代、当代或未来。我认为艺术作品可以被分为两类:好的和不好的,艺术家也可以被视为优秀或不那么优秀的。作为一名艺术家,我们的任务是创作出具有高审美标准的艺术作品,感动人的艺术品。对我个人而言,我一直专注于架上绘画,因为这是我最热爱的表达形式:它带给我无尽的愉悦也带给我无尽的挑战。


于:当前的艺术理念和艺术实践充满活力且多样化,但手段上的多样是不能与“进步”划等号的。只是多了几种说话的方式而已,其中有说的好的也有说的不好的。一位艺术家短期内获得成功并不代表他能真正的被历史铭记。当我们回顾过去的优秀艺术作品时,并不会因为它们的技法与当下不同而觉得它们单调乏味,因为那些作品蕴藏的情感是充盈的。
我认为白南准的影像作品非常出色。还有克里斯托的大地艺术,对我来说非常引人入胜,令人印象深刻。他选择对象时是有审美思考的,包裹的过程突出了造型的基本形态,与环境(包括色彩)进行对话配合的很协调,巨大的雕塑效果非常震撼。
因此,我认为技法只是一种外在形式。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地处理主题,因为只有通过视觉上的吸引力才能引发情感反应。许多杰出艺术家的作品主题简单,但展现了卓越的审美能力,因此成为经典。相反,许多看似深刻复杂的作品,如果没有达到必要的美学高度,往往显得乏味平淡。




于:我希望我的绘画首先能够传达油画的魅力,比如造型、色彩和构图的美感。只有这样,才能与观众建立沟通。我喜欢描绘能引发情感共鸣的主题,无论是人物还是风景。至于我的作品会给观众带来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过程。我能够做到的是尽量表达出自身的感受,我相信观众自然会找到与之共鸣的部分。
主题只是一个工具。无论是历史题材、日常生活场景,还是梦境描绘,都同样有价值。只有感动自己的题材才是重大题材,就像塞尚画的“苹果”作为“主题”,它便是塞尚的全部。你说重不重要?我认为,艺术作品的真正灵魂在于向观众传达一种抽象的美感,用这种美感来传递某种情感。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是相通的。


于:在2024年,我计划创作一幅大型作品。这将是继大型西藏题材作品《捡牛粪》之后的又一重要作品。我想选择煤矿工人作为主题,并亲自前往矿井,深入体验和发现他们的典型特征。我被煤矿工人从矿井出来时的色彩魅力和形象特征所吸引,那些黑色调中存在的各种层次很有力量,我想要探索这些黑色的表达。 目前,当得知佛罗伦萨学院美术馆将举办这场展览时,我充满了热情,原本打算运用尽可能多的表达形式来呈现这次展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到需要一个更精简的展览,就像一颗钻石一样,让观众能够在安静的氛围中欣赏这些作品,体会我多年来对油画语言的研究。我希望作品本身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并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这是我所追求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