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四年(1657)十二月,在云贵地区坚持抗清的永历朝廷发生内讧,叛降清廷的永历朝权臣孙可望为了得到清廷的信任,“上方略,言滇、黔可取状”,清廷立即组织大军以贝子洛托、吴三桂、赵布泰统率约15万余人分三路进取云、贵。由于清军兵力有压倒性的优势,以李定国为首的南明军连战失败,经过一年的抵抗,终于在顺治十五年(1658)十二月崩盘,清军即将直逼云南省城昆明,永历朝廷的转移已经成为了必然局面,当永历朝廷踏出昆明的那一刻,就已然成为了流亡政府,下面本文就来说说永历朝廷悲壮而屈辱的最后时刻。

永历帝流亡图
清军直逼省城,永历朝廷踏上流亡之路。顺治十五年十二月(1658)初八日,晋王李定国在安龙战败的消息传到了昆明。初九日,晋王李定国的特使急至昆明,上奏前线形势不利,奉劝永历帝尽快放弃省城转移,“上当移跸以避清人之锋”,昆明城人心惶惶,乱作一团,秩序已经出现崩溃征兆,“乱兵有行劫于市者”,幸好广昌侯高文贵将乱兵斩杀,才暂时稳住了局面。

《狩缅纪事》
眼瞅着清军日益逼近,转移已经成了必然局面。十二月十四日,永历帝召开在昆明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应该往哪个方向撤离。以刘茞为首的四川籍官员主张入蜀求生,投附当地的抗清势力。而身为永安侯、内阁参政的马吉翔(此人乃永历朝之权奸)担心在四川的抗清将领夺其权柄,遂“力沮之”。身为世镇云南的黔国公沐天波主张逃往云南西部,如果清军追急,便逃往缅甸,如果局势稍缓,可据守大理,“犹不失为蒙、段也”(历史上在我国云南地区的割据政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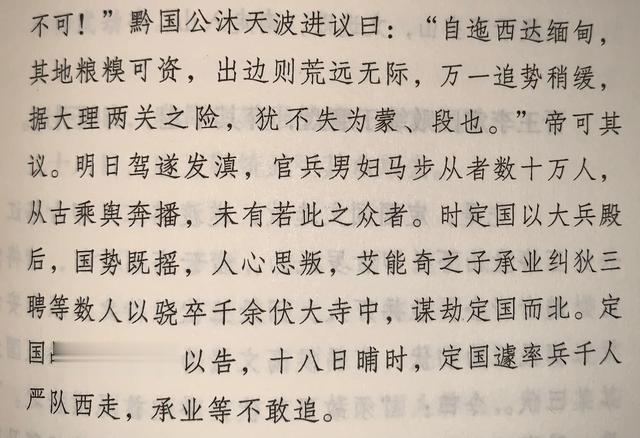
《求野录》
最后,永历帝同意了沐天波的意见。于十二月十五日,永历帝一行“官兵男妇马步从者数十万人”从云南省城出发,经过楚雄、大理两地等地,在顺治十六年正月初四,永历帝一行到达云南永昌,暂时安定了下来。
但这安定日子也没多久。清军在正月初三占领昆明之后。在休整后,遂于闰正月初二向永昌继续追击永历帝。十五日至大理玉龙关。永历朝廷眼见清军急追,再次匆忙踏上了流亡之路,于二十五日到达盏达土司,二十六日到达布岭,此地已与缅甸相近。
执掌内阁的马吉翔和他的弟弟、女婿商议认为,只要到达缅甸就可以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就想方设法勾连扈从护卫的将领孙崇雅谎报清军在后急追的军情,迫使永历帝退往缅甸。为了牢牢控制永历帝,还不忘排斥异己,并授意孙崇雅大肆杀戮抢劫永历帝的从官,而这个孙崇雅本就感觉前途黯淡,在马吉翔的怂恿下,欣然应允。
《狩缅纪事》:我等百千谋议,方得车驾幸缅。今从官相随又已至此,万一得有宁宇,上意必悔不早入蜀,在廷又欲持文墨以议我弟兄。今护卫平阳侯右协孙崇雅,与我极为同心。莫若先示以意,使之妄传追逼,则乘舆今夜必兼程入关。伺夜半昏黑,车驾一过关,便将从官尽劫,则东奔西窜,流离万状,必无有随驾者矣。

《狩缅纪事》
于是这天晚上一场巨大的悲剧发生了,孙崇雅大肆纵兵劫掠,在夜色笼罩下,连永历皇帝都不能幸免,“上跣足不能登山”,随行文武官员被抢劫的更是狼狈,不少官员将士也在混乱中作鸟兽散。二十六日白天,到达曩本河,距离缅关10里,黔国公沐天波先派人晓谕,由于历史原因,沐家在缅甸享有极大的威望,缅军纷纷下马礼待。
此时,由于一路流离,加上孙崇雅的叛乱,到达中缅边境的文武官员和随从只有2000多人。缅人要求明军放下武器才能放他们进入境内避难,“必尽释甲仗,始许入关”,永历帝只能命军士抛弃武器“一时卫士中官尽解弓刀盔甲,器械山积关前,皆赤手随驾去”。黔国公沐天波、华亭侯王惟恭、太监李崇贵认为不应该把命运完全交给缅甸,应该以“文武将士分一半随大驾入缅”,另外一半随太子在云南境内“调度各营”,以为外援。但中宫王氏舍不得与爱子分离,只能作罢。
朱由榔唯恐清军跟踪而来,命令土司官思线砍倒数木,阻塞道路。思线在得到永历帝谕旨后,等永历帝一行启行,立刻搜山三天,对仓皇追驾的明朝官员一律逮捕,抄没财物,身强力壮者直接杀死,扔于各寨沟下,老弱者发往各寨做奴隶,折磨而死,投入江中,销尸灭迹。

《狩缅纪事》
三十日,行至伊洛瓦底江。二月初二,缅甸国王平达格力派大船4艘,小船若干前来接应永历帝。但由于船只不够,永历帝只能挑选其中的646人乘船南下;剩下900多人等在总兵潘世荣的率领下骑马走陆路与永历帝会合。十八日,永历帝一行才乘船至井梗(曼得勒),在沐天波等人接洽下,缅甸国王在用印信核对身份无误后,才允许永历帝和其随行人员留驻境内。
而潘世荣陆路一行则遭遇了灭顶之灾,他们在三月十七日就到达了缅甸首都阿瓦城的对岸,由于人马纷杂,引起了缅甸国王的怀疑,缅甸国王说道:“此等非避乱,乃是阴图我国耳。”,遂派出兵丁将他们包围,强行把这批南明人员分散安插,带到村落中看管,一户一人,禁止往来。这批南明人士立刻妻离子散,潘世荣受到了如此羞辱“仰天锥心而死”,内使江国泰、总兵姜承德“自经树间”。这一行只有大约90人逃出,为暹罗(泰国)所收留。

《狩缅纪事》
在缅受辱,丧失气节,文恬武嬉。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五月初七,缅甸当局才把永历帝及其随从搬移到阿瓦城河对岸,用竹子造了一座承,以草屋十间为永历帝居所,其他官员随从自行盖房,“盖茅屋十间为上行宫,以竹编围,四面如城”。
在永历一行到达缅甸之后,这些人对光复大明的前途早就不报希望,已经失去了失国忧君的观念,竟然过起了苟延残喘、苦中作乐的生活。很多官员和缅甸当地居民进行贸易,这倒也无可厚非,但那些官员们竟然不顾体面,“短衣跣足混入缅妇女,席地坐笑”。八月间,永历帝左腿患病,昼夜呻吟,“而诸臣结舍酣歌,毫无顾忌”,马吉翔在皇亲王维恭那还接着奏乐,接着舞,共庆中秋到来。气的永历帝下发诏书:皇亲即目中无朕,当念母死新葬,不宜闻乐。才有所收敛。
此外,绥宁伯蒲缨、太监杨国明等大开赌场,永历帝非常愤怒,命锦衣卫捣毁,但诸臣赌兴正浓,哪管得了这些,换个地方继续赌博。尤其混账的是马吉翔,到了这个时候都没有忘记拉帮结派,九月间缅甸人向永历帝分发稻谷,他居然“据为己物,分散私人亲厚”,侍卫总兵邓凯阻止,差点被他派人打死。

《狩缅纪事》
这个流亡朝廷的所作所为被缅甸人看在眼里,更加鄙视永历一行,私下说道:“天朝大臣如此嬉戏无度,天下安得不亡!”,连当时的通事(相当于翻译)都看不下去,说:“我看这几多老爷越发不像个兴亡图霸的人,就有晋王(李定国)也是一木难支大厦也。”
八月十三日,缅甸国王派人来请黔国公沐天波参加十五日的缅历年节,在沐天波过江后,缅甸仁不准他穿戴明朝衣冠,强迫其穿上缅甸的民族服装与其他小国朝见缅甸国王,想以此“夸示外夷”,沐氏世镇云南,一直代表明朝管辖云南土司并处理周边国家的事务,以往边外国家只有跪见沐氏的份,现在身份翻转,反而要他向缅王称臣,心中苦闷可想而知,但寄人篱下,为了永历帝安全,不得不如此,“我若不屈,则车驾已在虎穴”。
随着坐吃山空,永历朝廷的“财政”愈发紧张,有些大臣已经没粮下锅,马吉翔要永历帝发点内帑。可永历帝此事哪有什么钱,只好把黄金制作的国玺扔在地上,让他们凿碎分给群臣,马吉翔等竟然毫无廉耻的将印砸碎。气的永历帝大骂:“马吉翔、李国泰二奴沽名钓誉,将朕作人情送人。赌博饮酒,挥金如土。今乃碎朕国宝,分较锱铢,良心何在?”

马吉翔、李国泰碎玺
李定国、白文选竭力救驾在永历帝入缅后,李定国也南下并在顺治十六年(1659)二月与白文选会师于木邦,二人认为云南内地虽然被清军占领,散处在云、贵、川的拥明势力仍然不少。当务之急是把永历帝从缅甸接回来。
两人在商议后,决定先由白文选率师深入缅甸寻找永历帝,并派出两名使者说明接永历帝的来意,但中途为缅人杀害,其又派10名骑兵说明情况,但依旧被缅人所杀。而当时的缅甸官员认为,永历皇帝既然是来缅避难,想必他的手下一定也是一些乌合之众,不足为惧,不仅杀使,还抢白文选军队的马匹,白文选勃然大怒,下令出兵反击。
缅军主力在江对岸列阵,准备迎战。白文选命令部下士卒砍伐树木,制作竹筏,准备渡江。据《狩缅纪事》记载,缅军主力有数十万之多(可能夸张很多),自恃人多势众,根本对白文选兵看不上眼,信心满满的想要等南明军渡河全歼,“汉人无状,然亦不多,须俟其尽渡,然后扼而尽歼诸江中可也”,白文选刚渡过100名骑兵,见缅军松懈,急急吹号,“一鼓而前”,缅兵望风披靡。南明军主力陆续过江后,再次发动冲锋,缅军大败,“积尸横野”,缅军这才知道厉害,收兵入城自保。但白文选怕把缅人逼急了伤害永历帝,遂不敢继续进攻。
而缅甸一方则质问永历帝:“尔到我家避难,云何杀我地方?”,永历帝在缅甸研究陷入了信息茧房,根本不知道白文选前来接驾的情形,立即下谕让明将退兵,白文选只得叩头退兵。

《狩缅纪事》
顺治十七年(1660)九月,白文选再次出兵攻打阿瓦新城,打的阿瓦城防摇摇欲坠,缅人遂使诈,欺骗白文选说:“三天后,交还永历帝。”(三日后,出此让王),白文选误信诈言,退兵十里,缅人得以重新整顿城防,等白文选反应过来就已经晚了,二次攻城失败退走。

《南疆逸史》
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二十八日,李定国和白文选至缅甸,白文选密疏永历,言:臣所以不敢速破缅者,恐缅未破,而害及于皇上尔。为今之计,令多方委婉,使缅送驾出来为稳著。他们搭建浮桥试图营救永历帝,但浮桥被缅人砍断,最后一次营救永历帝的计划失败。
白文选和李定国对于永历的解救真是不遗余力,由于水土不服,后勤困难等因素,成功概率本身并不大,再加上永历一方毫无配合,且有马吉翔等奸佞作祟,终告失败,如李定国所言:“诸公只顾在内安乐,全不关切出险一事,奈何!奈何!”
缅方决定投靠清廷,引发咒水之难。而此时的永历一行的做法简直是荒唐,马吉翔着实是个奸人,都到了这个份上,还忙着结党、固宠、专权,至于复国大业完全不在其考虑范围内,为了讨好缅甸,不惜阻止李定国、白文选的援兵,以永历帝的名义对缅甸官兵说:“朕已航闽,后有各营官兵来,可奋力剿歼。”
不仅如此,还刀口内向,铲除异己,全力阻止内部救亡图存的义举。总兵王启隆与其家丁何爱、沐天波麾下家丁李成私藏兵器打算保护太子突破缅甸人的囚禁投奔李定国、白文选。这一密谋被马吉翔、李国泰察觉,他们反诬沐天波、王启龙勾结缅甸谋害皇室,最后两位家丁被处死,他们为了挽救明王室的行动化为泡影。永历一行继续过着“实则无异囚犯”的生活。

《狩缅纪事》
永历一行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浑浑噩噩,但外面的局势却在发生剧烈变化。顺治十八年(1661)五月二十三日,原来的缅甸国王平格达力被其弟莽白篡位夺权。这位新国王对李定国、白文选的救驾举动非常憎恨。而缅甸人之所以坚决不交出永历帝给李定国、白文选,也必然考虑了当时我国境内的局势。这位新国王眼瞅着清朝统治已经稳固,势必长期盘踞在中缅边境,如果把永历帝交给清廷,对遏制南明论会起到一定作用,局面显然对自己更加有利。
缅甸一方态度的变化,很快就被清廷所察觉,确切的说是被吴三桂所察觉。吴三桂早在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就上表清廷入缅擒拿永历帝,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三患二难疏》,就是这份奏疏,让清廷下了擒拿永历帝的决心。
在出兵缅甸前,吴三桂一面恐吓缅甸国王,“急缚伪王来,否者我且屠阿瓦”,一面又让麾下将领马宝和缅甸国王交涉,许诺只要交出永历帝,富贵立至,“苟能送帝出,则富贵可立至也”。缅甸国王在威逼利诱之下最终服软。

《行在阳秋》
为了清除献出永历帝的障碍,缅甸国王在顺治十八年(1661)七月十六日要求永历帝麾下大臣前去议事,“众人皆疑惧不肯行”。十八日,缅甸使者前来催促,威胁如果不去,则断绝物资供给,“不然断绝往来,并日用亦艰矣”。十九日黎明,马吉翔矫诏让文武官员同去。一到地点就被3000缅兵包围,不分好坏,全被杀戮,马吉翔、沐天波等大臣42人被杀,沐天波在临死前,“自袖中取出流星槌,击死缅兵九人”,至为壮烈。接着缅兵又来永历营地抢劫,宫女、诸臣纷纷自缢。永历帝也差点自杀,被都督同知邓凯所阻止。这就是史学界有名的“咒水之难”。经过此次劫难,永历一行只剩下了300多人。
《狩缅纪事》:上大骇,欲与中宫自缢。惟邓凯在宫,劝上云:“太后年老,飘落异域。皇上失社稷已不忠,今弃太后又不孝,何以见高皇帝于地下?”,乃止。

咒水之难
吴三桂进兵俘杀永历帝。顺治十八年(1661)十一月,吴三桂、爱星阿等率八旗军、绿营军、土司兵、降兵75000人,“并炊汲余丁”,共100000人向缅甸境内,施压缅甸交出永历帝。永历帝得知吴三桂入缅的消息后,向吴三桂写了一封信,祈求吴三桂放自己一马,但感觉永历已经觉察到了吴三桂不会答应,此信虽然词气绵软,如秋虫鸣泣,但每一个字都直戳这位卖主求荣的平西王的肺管子。信如下图。
幸李定国迎仆于贵州,接仆于南安,自谓与人无患,与世无争矣。而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督师入滇,覆我巢穴。(就连曾经做过“流贼”的李定国都能不忘君父,你吴三桂家族承受大明恩厚矣,反对旧主下手,不觉得羞愧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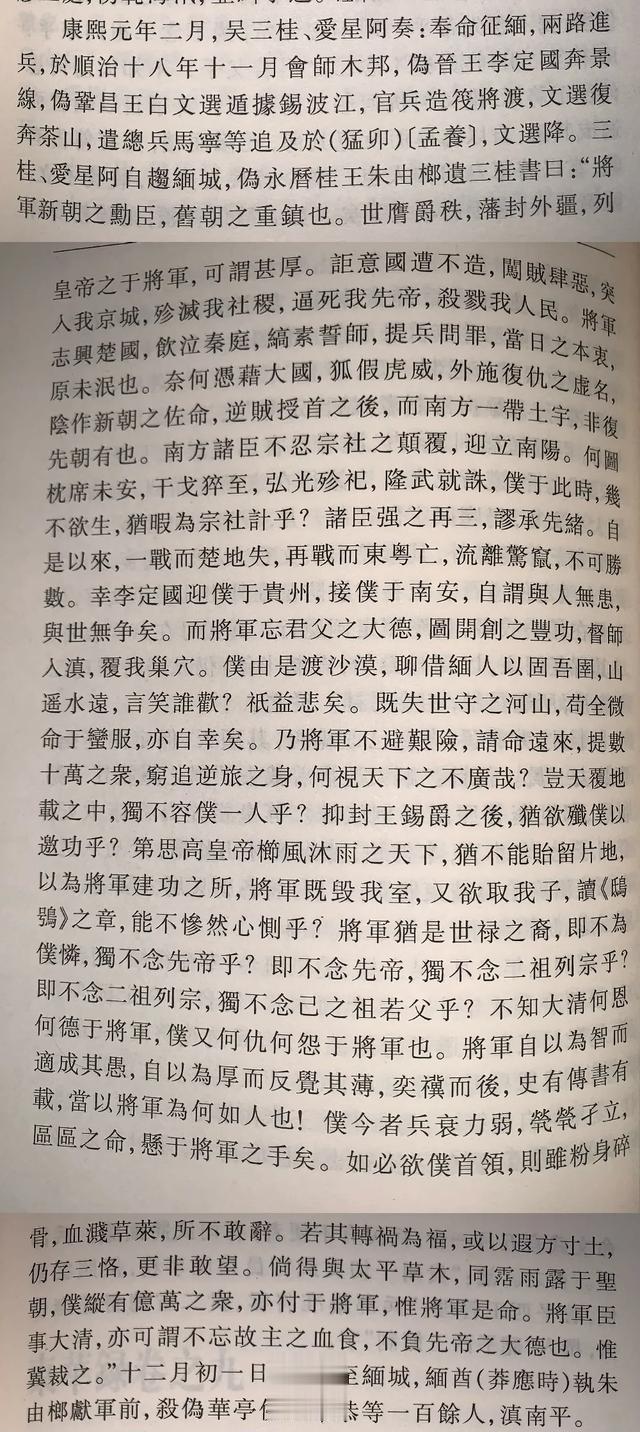
《东华录》
十二月初一日,清军大队已到阿瓦城,缅甸国王大惊,决定送出永历帝朱由榔父子。据《庭闻录》记载,缅甸宰相锡真持贝叶缅文来旧晚坡见吴三桂,书上有“愿送永历出城,但求退兵扎锡坡等语”。初二日,数十名缅军来到永历驻地,谎称:“中国有兵来近城,我国发兵由此抵敌,宜速移去”,不由分说的将永历帝抬起就走,另外备轿给太后、皇后乘用。
一行人步行五里渡河,清军前锋噶喇昂邦担心永历帝投水自尽,事先安排了不久前降清的铁骑前营武功伯王会(又有史书称是吴三桂麾下将领高得捷)到河边等候,假称晋王李定国来迎,直到进入清军营地中,永历帝才知道被出卖,永历帝至此被清军俘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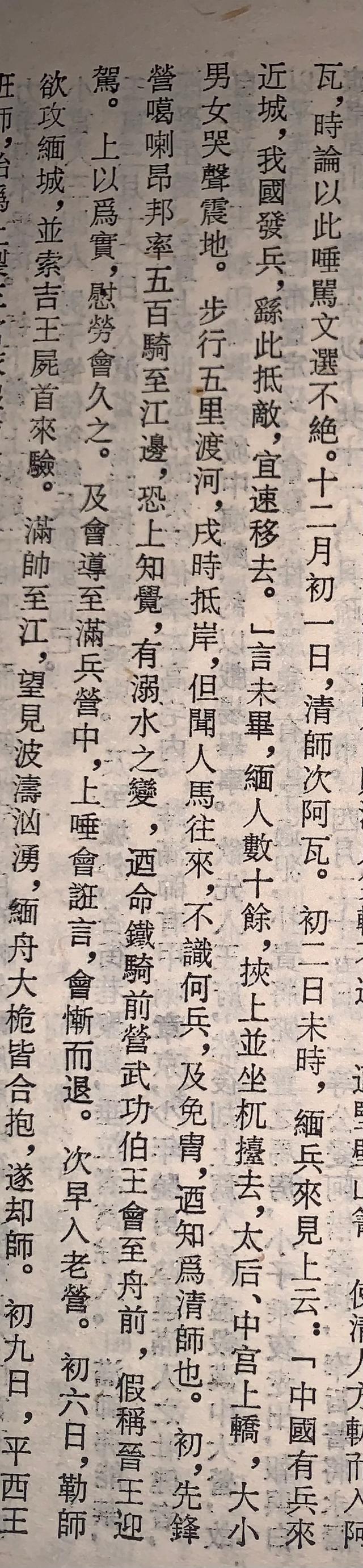
永历帝被清军俘获
十二月初三,永历帝被送入吴三桂营中。见到永历帝的吴三桂显得十分难堪,竟然忘记自己是清朝臣子,不由自主的向永历帝跪拜,“王问为谁,三桂噤不能对。再问之,不觉得膝之屈也”。永历帝连问4次,吴三桂才说出自己的名字。
永历帝责备吴三桂很久,吴三桂都不敢说话,最后永历帝说:“今亦已矣,朕本北人,欲还见十二陵而死,尔能任之乎?”,面对永历帝谒拜先祖陵墓的要求,吴三桂只胡乱说了一句一个字“能”,便狼狈离开,“三桂伏地不能起,左右挽之出,面如死灰,汗浃背,自是不复见”。那封信和永历的斥责翻起了吴三桂心中余烬未熄的负罪感,让吴三桂过于难受。至此,他再也没有见永历帝一面。

《小腆纪年附考》
康熙元年(1662)三月十三日,永历帝被押解至昆明。清将爱星阿本打算把朱由榔和他的家眷都送往北京。但吴三桂认为如果押解北京献俘,路途过于遥远,变数太大,建议就地处决。得到清廷核准后执行。
吴三桂主张斩首。但清军将领爱星阿、卓罗等人不同意,爱星阿认为:“永历尝为中国之君,今若斩首,未免太惨,仍当赐以自尽,始为得体。”,卓罗认为:“一死而已,彼亦曾为君,全其首领可也。”,四月二十五日,朱由榔、朱慈烜、国戚王维恭的儿子被缢死。

《庭闻录》
至此,南明最后一帝烟消云散,历时16年的永历政权也最后灭亡。
引用文献:《东华录》、《狩缅纪事》、《求野录》、《庭闻录》、《南疆逸史》、《行在阳秋》、《缅甸史》、《鹿樵纪闻》、《小腆纪年附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