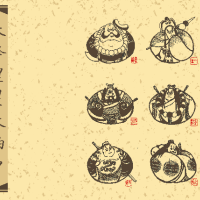日本人曾经在潍坊犯下的罪行不亚于南京大屠杀和东北“731”。
1938年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潍县城,广文中学和小学被迫停课,部分师生流亡到内地。日本人大肆吞并潍县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欲将潍县建成“支那的名古屋”。1940年后,日寇将美籍校董芮道明、医院院长梅仁德和外籍教师、医生、护士及家眷全部驱逐回国。
1941年底,驻潍县地区的日本宪兵队长汤本宣典,指挥一中队伪军将乐道院包围,命令伪军中队长刘锡赞把守北大门,汤本亲自率领一小队日本宪兵进驻乐道院。进院后,他与迟走一步的女护士魏希芳相遇,把她堵在梅仁德院长的厨师李长安家里,于光天化日下剥光她的衣裤,强行奸污,并长期占有了她(日寇投降后,汤本宣典转任王耀武部下教官,在一次讲解手榴弹时不慎爆炸身亡)。
在华北众多城市中,日本侵略者选择潍县乐道院作为盟国侨民集中营,这是颇费了一番心机的。一则这里远离大都市和港口,相对安全;二则潍县的经济和治安状况使他们放心;三则这里铁路、公路、机场畅通,押送侨民比较方便;四则这里有一个适于欧美侨民居住的密封环境。因此,他们把整个华北地区的盟国侨民都集中到这里关押。

日本宪兵和伪军进驻乐道院后,把医院和学校的所有人员全部赶走,将各部门的小套院的院墙全部拆除,利用拆墙所得的砖石和砍伐的木料修筑起许多碉堡,只留下西南角的一个小院给日本看守居住。另外,在大院墙外的东北角和西北角各建一座高大碉堡,配备探照灯和机枪小炮等武器,四面的高围墙顶上都架设电网,墙外还架设了铁丝网和电网,避免外人靠近围墙。院墙内侧修成环墙马路,路里面也架设了铁丝网,防止外国侨民逃走,同时便于看守巡查。
日军将原来学生宿舍的铺地砖扒去,换成木板,成为日本住宅式样的塌塌米,让外国侨民睡在上面,房间里都用放置物品的木架代替家具;并将所有房间和街道都编号,就这样,一所教学育人,环境优美的学校变成了阴森恐怖的集中营。但这些变化从外面却不容易看出来,四面墙头上的电网很像原来的铁丝网,并不显眼,碉堡在围墙里面只露顶部也像原来的天文台,大门并未改动,门楣上依旧是原来的乐道院巨匾,从外面很难看出是一座大型集中营。集中营建成后,日本宪兵撤走,改由高等警署日本警官担任看守。
当时集中营的日本官员有:日本驻青岛领事馆副领事古贺(KOGA)、日本军方代表神保中佐、集中营主管伊佐、日本警官小谷野等人,分别负责外交、军事、行政和安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地区盟国侨民开办的企业、学校、医院被查封,成为日军财产。最初,日军将侨民就地关押在各个城市,如青岛的侨民被关押在江苏路、湖南路口外国教会的房子里;烟台的侨民被关押在原益文商专北面的长老会住宅里。他们还被游街示众,有的被日军杀害。半年后,潍县乐道院集中营建成,他们才从各地陆陆续续押往这里集中关押。被捕的盟国侨民最多时曾经达2000多名,再加上看守集中营的日本军警,拥挤不堪,人满为患。
1943年8月16日,日本看守将440名天主教僧侣和修女转移到北京一处天主教堂关押(留下潍县当地的10名天主教僧侣和5名修女),使集中营减少了人口过多的压力。9月,日本侵华军从这里抽出330名盟国在押侨民交换战俘,又走了不少人。但是,原来关押在烟台庙宇山的370多名芝罘学校外籍师生,很快又全部转到这里关押。通过上述调动,设在潍坊乐道院集中营的盟国侨民,由2000余人变为1500余人。

集中营的生活像监狱一样,不仅看管严厉,作息时间也严格。早上敲钟起床,紧张地梳洗后,分别到3处食堂去吃早餐,饭后收拾房间洗地板,然后教徒做早祷,学生自习。点名的钟声一响,所有囚徒都必须停止一切活动快步到操场集合,按住区分6队在固定的地方排好队,各队的值日看守到队前点名,囚徒用日语依次报自己的号码,经看守核对名册看是否有误,有时看守还要训话或宣布事情,点名时间便拖得很长,盛夏热不可耐,隆冬严寒难忍,等到钟声再敲响才得以散去。这是集中营里的头等大事,不论刮风还是下雨雪,每天都是如此。
集中营里的人都是必须劳动的,有专长的,可以作面包师、厨师、鞋匠、锅炉工、修理工、洗补衣工、打水员(将井水压入蓄水池)及医护人员等。除年老体弱多病的赫士和戴存仁外,不论男女,不分贵族、官员、专家、学者、富商还是贫民、乞丐都得工作,大家轮流帮厨、洗菜、烧火、做煤球、打扫卫生、清除垃圾等。芝罘学校和成人学校虽可按时上课,但他们分担的工作,课余时间仍然要补上。
集中营里有一座面包房,三座厨房和一个给老弱病残做饭的小灶,每家每室还有一台自砌的小炉灶,自己烧开水、煮咖啡或做供应以外的小吃,冬季还分配取暖的铁炉子并供应少量粉煤,自己做煤球烧。集中营里有洗补衣房、修鞋室、锅炉房及多处淋浴设备,也有医院、手术室、化验室和病房等(这些设施都是教会医院和广文中小学劫后残存的,但是医疗器械残缺不全,尤缺特效药物)。
晚饭后,在押人员可以自由活动,散步、游戏、排练节目、打球比赛,天黑后开晚会、唱诗歌、开舞会、演话剧、游戏比赛、开辩论会、教徒做晚祷等,活动进入高潮,教堂和所有餐厅里都挤满了人,最后,入寝的钟声敲响,必须回各自的房间上床,不准在别处逗留。

星期天除照常点名外不劳动,各教派轮流到教堂做礼拜,早上天主教做弥撒,点名后,圣公会各教派联合做礼拜,晚祷唱圣诗。每逢过年和圣诞节、复活节也是只点名,不劳动。在这些节日里,通常天不亮就开始进行各种庆祝活动,直到晚上。在集中营内,还可以举行婚礼和葬礼,这些礼仪也是按照各国不同教会风俗和习惯举行,日本看守并不干涉,但必须事先报告并在看守到场监视下进行。赫士博士和利迪尔的葬礼就办的极其隆重,由牧师主持仪式,学生组成仪仗队,生前比较谈得来的难民抬棺,乐队一路吹奏哀乐,全营侨民都参加送葬。
难民和看守日夜在一起3年多,难民经常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在旁监视的看守也情不自禁地和难民们一起欢笑叫好,有时看守和难民还进行别开生面的球赛或摔跤。每逢日军长官前来探视,集中营都会要求一群难民孩子列队欢迎,这些训练有素的小学生,腰板挺直,目不斜视,先行注目礼,然后用日语报数:“依几、泥、散、席……”
日本看守对待违反集中营规的侨民,一般不殴打用刑,最重的处罚是关禁闭(如基格神甫用衣物与营外中国百姓换食品便被关过禁闭)。但是日本看守对待中国人却极其凶狠残忍,如一名中国临时工偷带食品入内,便被日本看守打得死去活来,随后失踪。上虞河村13岁女小学生韩贞昌在集中营外捡破烂,被日军看守殴打后扔入河中,她游上岸后又被发现,二次被扔入河中。她再游至对岸,终因伤重力竭而死。一位农民在集中营前面的路上拾碎烟叶,被碉堡卫兵开枪打死。上虞河青年韩祥等人,在墙头电网放上木板绝缘,带食品翻墙而入,与难民交换钱物,后来不幸触电身亡。日本看守故意拖延不收尸,让尸体挂在电网上一整天,借以示众。
集中营的粮食等主要食品都实行配给方式,定量和日军占领区的中国城镇居民一样,少得不足以维持生命的最低标准。初期,配给的面粉还比较多,外国侨民自己烤面包吃尚能半饱,配给的粗粮中除高梁外还有玉米和绿豆等杂粮,偶尔还配给少量花生油或花生。集中营里没有糖和乳制品,但代用咖啡和茶都不缺,茄子等蔬菜敞开供应。供应的老骡肉,热天总是长满蛆,骡肝变成黑色,饥肠辘辘的难民们也只好强咽。这些食品是由日本看守们贩运进来的,价格比黑市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