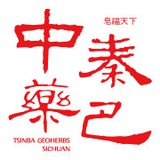读史读到明末,总不免让人心潮澎湃。这是最风云激荡的时代,也是最摧人心肝的时代;这是英雄辈出的时光,也是小人当道的时光;这是一场大梦将觉,是一场宿醉欲醒;是无数人肝脑涂地的年代,也是铁骨铮铮的汉子不绝于世的年代。为了气节这两个无用的字,为了忠义这个愚蠢的词,不知有多少人谈笑赴死,哪怕是阖族殉难也眉头不瞬。在这些个血腥黑暗的年份里,那些名字就如同黑夜里骤然爆发的烟花一般灿烂,迅速的照亮了夜空,又迅速的归于沉寂。他们燃烧了自己的生命化作瞬间的绚烂,就只为了让黑暗的人间记住这世上终有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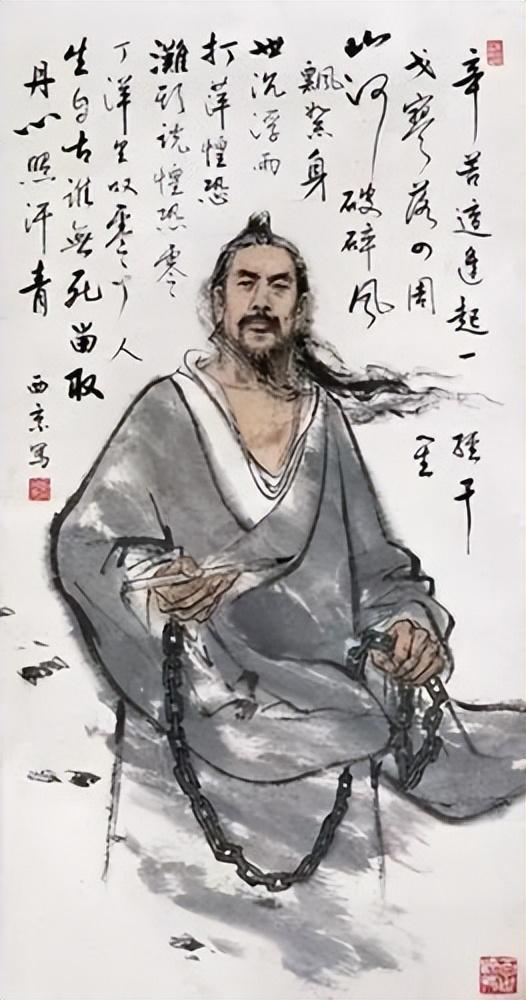
在浩荡的历史风云面前,他们不过是螳臂当车,甚至不能稍微阻碍一下这个车轮前进的速度。可这并不妨碍这群曾经汲汲于功名、念念于歌赋、天天写着无聊的八股文的读书人,甚至是那些走街串巷的贩夫走卒,农人衙役,都争先恐后的挺起胸膛迎着闪耀寒光、鲜血淋漓的长枪走上前去,只为了尽可能的保护他们执念的社稷——哪怕已经天崩地坼,王朝星散,可是他们相信只要他们没有死绝,这个天下就还有薪火相传的希望。
于是乎,我们看到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看到了那副赫赫有名的“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绝笔对联下的江阴全城殉节;看到了身为封疆大吏的瞿式耜和张同敞共同吟诵着《浩气吟》慨然在桂林的青山绿水下赴死,看到了身为内阁一品大臣的朱大典在自己身上绑上火药,哈哈大笑中与进入金华城的清军同归于尽……

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在那个时代实在太多太多。但我今天不想讲瞿式耜、朱大典这些人,他们毕竟是大臣,死节乃是忠于职守。我只想讲几个普通人的故事。他们不是大臣,甚至不是生员,他们是山野之民,方外之僧,贩夫走卒乃至屠狗之辈。他们没有享受过大明朝廷给他们的任何恩惠,甚至反而在一直受着这个朝廷的剥削压迫。可是在天崩地裂的时代,他们却一样挺起脊梁迎着刀枪走了上去,没有一点犹豫,没有一丝后悔。有的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只留下了他们的传说……
一,潘王同殉
王毓蓍,字元趾,浙江会稽人。虽然仅是一白衣生员,但是才名传遍东南,与张溥、陈子龙等同名,师承大儒刘宗周,为浙江读书人年轻一代中之翘楚。

刘宗周
潘集,字子翔,浙江山阴人(与会稽同属绍兴府),也是一个才华横溢之人,出口成章,目空一切。奈何绍兴府已有王毓蓍成名在前,大家热捧王而冷落于潘秀才。正所谓文人相轻,年少气盛的潘集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因此有事没事的在人前批评王毓蓍的文章,简直就差直说狗屁不通了。王毓蓍再好的修养也耐不住如此挑衅,以故二人绝交,虽同在绍兴城里读书就学,时不时会碰面,却绝不互相招呼,俨然一对死敌。
乙酉夏,大清兵下江南,铁蹄瞬间踏碎了江南的宁静与和平。惊慌失措的明朝地方官望风而降,清军几乎是传檄而定浙东。绍兴府官员也是毫不犹豫的选择备好犒师牛酒迎接大清“王师”前来接收。
绍兴府准备献城投降的消息传到王毓蓍家中,正在吃饭的王毓蓍愤然投箸而起,在墙上大书“生员王毓蓍不降!”几个大字,随即赶在清军来到之前投水而死,给他的老师刘宗周留下绝笔书“毓蓍已得死所,愿先生早自决!”(后刘宗周亦绝食而死)
鼎鼎大名的浙东才子王毓蓍投水殉国的消息传开,向与王毓蓍不睦的潘集闻听先是一呆,随即痛哭大呼“先生去了吗?等等你的朋友啊!集是你的老朋友,一定会追随你的!”说罢家也不回,径自前往王毓蓍投水处也要自尽。身边人忙拉着他劝解:“你不过是一个布衣,何必如此?天下甚大,难道就缺你一个义士吗?”潘集惨笑着大声回答:“毓蓍已去!天下人自生,集自死!集不愧天下,天下也不会为集而愧!我岂能不如王兄!”言罢,抱起巨石一块,毅然跳河而死。
二,嫩娘嚼舌
葛嫩娘,本明朝武将之后,家中条件十分优渥。父亲葛挺昱是镇守明朝边关的武将,因为葛嫩娘是家中独女,所以倍受宠爱。自幼就开始跟随名师学习琴棋书画,因为她玲珑剔透的聪慧个性,常常一点即通,年幼就能创作诗词画作。在她十岁左右,她又因为受到了父亲武将气息的感染,希望自己长大后做个女英雄,便日日缠着父亲教导自己武艺,对女儿百依百顺的葛挺昱,只得亲自手把手的,把自己的看家本领都传授给女儿,葛嫩娘也是聪慧,刀枪剑戟,排兵布阵,一学就会,是一名文武双全的女中豪杰。

无奈世事弄人。在风起云涌的明末岁月里,十六岁时,其父葛挺昱不幸在抗清斗争中壮烈殉国,葛府全家殉难,仅葛嫩娘在一个家丁掩护下狼狈不堪的千里辗转逃到了南京落脚。可还没等她喘口气,生活的残酷再次袭来,那个家丁眼看葛府复兴无望,起了歪心思,以100两银子的代价把大小姐哄骗着卖给了妓院,一位将门女杰,就这样沦落风尘了。
好在刚烈的葛嫩娘坚持卖艺不卖身,并因此深得偶然相识的安徽桐城人,同为世家子弟的孙克咸的赏识,二人互诉衷肠,都对对方的报国热情欣赏有加,很快私定终身之好。
恰逢天翻地覆之时,清军兵下江南,南都沦陷。孙克咸与葛嫩娘趁乱逃出了南京。他们不愿意做大清的剃发顺民,而是立志要匡扶明室。于是二人一起来到福州,投靠了当地的明朝将领。
正值清军开到攻打福州甚急。此时葛嫩娘自小学来的本事有了用武之地,她主动请缨去搬救兵。夜里,趁着月色,她一人在城墙系绳而下,找到了一匹快马只身前往泉州劝说当地的将领郑芝龙出兵救援,但无奈当时郑芝龙已经决定投降清兵,完全无视葛嫩娘的苦苦劝说,最后只能带着沉重的心情又偷偷返回福州。
福州城中兵粮短缺,面对清兵的第四次攻城,守城已经是有心无力了。葛嫩娘见到这种情况。再一次去泉州求援,但此时的郑芝龙已经投靠清军了,见到葛嫩娘的求援,不但不理会还叫她也一起归降清廷,气急败坏的她,大骂郑芝龙无耻,随后回到福州城,与丈夫孙克咸毅然决定,与福州城同殉。
不久,内外交困的福州终于城破,孙葛二人力战不屈,终被清军双双俘虏。清军主将贝勒博洛早已听闻福州城中有位女将十分了得,这时看到真人,不由得被其艳丽容貌惊呆了,当即表示只要葛嫩娘归顺自己就保他们不死。可是,国仇家恨于一身的葛嫩娘如何会答应,她破口怒骂博洛“痴心妄想!无非一死而已,便死也要让汝等明白,吾大明儿女岂会甘心受尔蛮夷侮辱!”言罢,猛地一口嚼碎自己舌头,吐到了贝勒博洛身上,随后放声大笑,与丈夫孙克咸一起被冲上来的戈什哈们剁成肉泥,二人至死不出一声。

三,道士挺身
有明一代,因为嘉靖大帝的崇信道教搞得国家乌烟瘴气,天下人颇有怨言。在其驾崩后道士的名声也随之急剧下降。但是在明亡清兴的天崩地裂之际,却有一群远离红尘的山中道士,毅然挺身报国,书写了一首壮烈的诗篇。

这些道士来自湖南益阳的浮邱山。浮邱山乃是道教盛地,当时山上本有数千远离红尘安心修道的道士。可是在国破家亡之际,面对奸淫掳掠屠杀而来的清军,这些出家的道士也坐不住了。没有人逼迫,没有人要求,三千道士自发的集合起来,他们扔下了香烛道经,拿起了刀枪棍棒,甚至打破门户之争主动联合起来(当时山上道士分属全真、正一两派),在李纯阳道长的带领下,毅然仗剑下山,抗清报国。再次向世人展示了什么叫乱世道士下山救世,盛世归隐深山。
这支缺乏训练的三千道士军,凭着一己之力,靠着满腔热血,居然一炮打响,在益阳沧水驿、寨子仑一带阻击清军,给了骄横的清军劲旅不小的损失。

然而,关键时刻,作为战斗主力的明朝政府军却玩起了“战略性撤退”,利用道士们苦战拖住了清军的机会,迅速的南撤了,一口气逃亡了广东。失去支援的道士们终究是不敌火铳和红衣大炮,在残酷的战斗中损失殆尽。然而,他们到死为止,没有一个人逃离战场,没有一个人投降清军。连清军将领也不得不感叹这些道士实乃清军南下路上所遇到的唯一残酷抵抗。
……
整个南明史上,类似上述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最可怪者,一边是底层的士子秀才乃至贩夫走卒为了一身衣冠甘愿抛却头颅,一边是大批的高官显贵望风迎降。即使在南明朝廷已经山穷水尽流亡到缅甸云南交界的穷山恶谷中时,依然有一大批忠心的百姓甘愿为这个毫无希望的朝廷殉葬。岂忠孝节义尽在民间,而官宦士绅丧尽礼义廉耻?但无论怎么样,这些百姓用他们的生命给华夏史书写就了无比灿烂辉煌的一页,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有骨气的民族,一个摧不垮的民族,即使面对高高举起的屠刀,也总有人会挺起胸膛去抵住屠刀,用鲜血滋润脚下这生养我们的土地——这就是我们的华夏!这就是我们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