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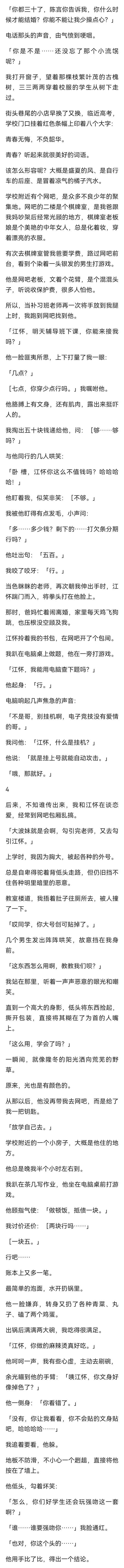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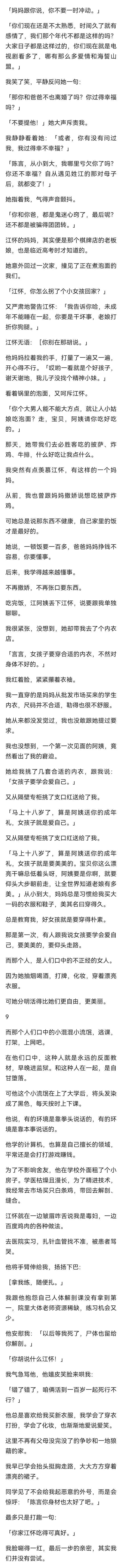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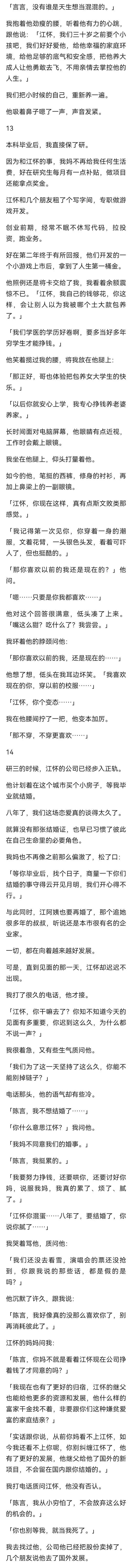
时而自愈,时而崩溃。
四年的时间,我没再听到关于江怀的任何消息,也没再接到过他的任何电话。
他就这样,彻底地消失在我的生命里。
三十岁了,身边的人陆续结了婚,有了孩子。
妈妈身体也不是太好了,她总是长吁短叹。
「言言,妈妈不是没有给过他机会,是他不知道珍惜,你们有缘无分。」
「四年了,兴许人家早就结婚生子了,你也该放下了。」
「你都三十了,你能不能找个人结婚,让妈妈安心?」
我张了张嘴,许多话哽在喉咙,最后只化作一句:「好。」
是啊,都四年了,兴许,人家早就结婚生子了。
犯贱发这种信息,简直是脑子有泡。
我关掉手机,准备第二天的课。
16
新生的第一节解剖课,幸运的是,院里新来一具无偿捐献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学生基本都是第一次直面真正的尸体,有紧张、有兴奋、有畏惧。
「第一次上解剖课,大家心理紧张、恐惧都是正常的。」
「老师,您第一次见的时候,不害怕吗?」有学生好奇地问我。
「我是坚定的唯物主义。」
我笑笑解释,又给学生讲道,
「没有解剖学,就没有医学。一个人愿意捐献出自己的遗体作为医学教学,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奉献精神,这些遗体是医学生第一个手术的【患者】,也是医学生的老师,他们被尊称为【大体老师】,也是我们医学界的【无语良师】。」
每个医学生都对大体老师保持着崇高的敬意。
课程开始前,照例为无偿捐献的大体老师默哀、献花。
他们在这里没有名字,只有编号。我看了眼资料。
今天的解剖对象是52号大体老师,青年男性。
我伸手掀开遗体上盖着的布,为了保护隐私,脸部都是遮住的。
生前应该很高,体型很瘦。
我拿起手术刀,目光不经意落在他胸口位置时,大脑忽然一片空白,整个人仿佛被抽空了力气般……身体止不住地战栗,嘴唇颤抖着,微微张开,却发不出一丝声音,
「老师你怎么了?」
「这个大体老师胸口上竟然文着老师的名字!」
那一瞬间,意识好像已经涣散,耳边仿佛响起多年前的声音。
「这样行不?够有安全感不?」
「我这都盖了章了,以后也没人要我了,你不嫁给我说不过去了。」
「那……万一我跟别人结婚呢?」
「你敢?我只要有一口气在,也要给你逮回来,带你私奔。」
是啊,他说过的,只要有一口气在,就不会让我嫁给别人……
他没有骗我。
如今,他静静躺在那里。
身体冰凉,身体不复以往的健壮,瘦到了极致。
可他就是江怀,尽管遮着脸,我也知道那是他。
因为没有哪个傻子会将陈言的名字文在胸口。
17
我跌跌撞撞起身,跑到学校管理处。
「52 号大体老师,我想知道他……他是怎么死的……」
工作人员表示:「陈老师,你应该明白,大体老师的个人信息都是保密的,我们也不知道。」
「他……他是我男朋友……」
他震惊之余,告诉我:
「大体老师在奉献自己最后的价值后,最后会由院方火化完交给家属,您可以找找他生前的家属。]
对,家属。
前几天,给江怀发的短信,都是有人帮他回的。
我颤抖着拨通他的电话,那头很快便接起了。
「有事?」
我心一颤,怎么会是江怀的声音……
我不会听错……
「江怀,你还活着?」
「废话,我当然活着呀。」
那头,依旧是他吊儿郎当的语气。
「那你出来见我一面。]
「不行,我老婆会生气。」
「你结婚了?」
「对呀,孩子都要出生了。」
我站在原地,感觉时空错乱了般。
「江怀,现在是哪年?」
「2024年啊。」
「巴黎奥运会我国获得了多少金牌?」
「40 枚金牌、27 枚银牌、24枚铜牌,共计91枚奖牌。是我国自 1984年参加夏季奥运会以来,境外参赛所取得的最好成绩。」
他竟然,全都知道……
那躺在学校研究室的遗体是谁?
我突然间想到了什么,问他:
「十年前,我写给你的信,最后一句是什么?」
「额,我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如果还活着应该已经看到那封信了,你为什么听不明白?」
「江怀,你死了是吗?我看到了你的遗体,你现在是人是鬼?」
我紧紧握着手机,手止不住地颤。
「嘿嘿被你发现了,我现在在地府跟你通话呢。」
「你……怎么会死?」
「哎呀,程序员熬夜猝死了……」
「现在阎王爷要我给地府做个系统,还在码代码,一会我去看看生死簿,给你多加几年嘿嘿。」
电话那头,他的声音轻松随意,我再也忍不住,哭着骂他:
「江怀,你这个骗子!!!」
18
我通过以前同学,联系到了以前和江怀创业的朋友。
「他当年就说要去国外发展,股份都卖了,我们也都很纳闷。相处那么多年,他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啊,你们感情那么好,我们都把红包准备好要参加你们婚礼了,哎……是呢,这家伙真不够意思,一走这么多年,兄弟们也不联系了。」
「你们,能联系到江怀的妈妈吗?」我问他们。
「江阿姨我们联系不上,不过有个人可能有她的消息,我们找找关系,看看能不能见上一面。」
他们说的,是江阿姨的再婚丈夫。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等了她很多年的那位叔叔,男人虽人到中年,但依旧身姿笔挺,一身斯文儒雅之气。
他跟我说江阿姨现在状态很差。
时隔四年再见,她脸上没有了精致的妆,散着头发,脸色苍白憔悴,一个人静静地坐着,眼神空洞地望着远方。
「江阿姨。」我轻轻唤了她一声。
她恍惚间抬头,看到我愣住了。
随即缓了缓神色,不耐烦说道:
「四年前我就跟你说过了,我不同意你和江怀的事,他现在已经结婚了,你还来做什么?」
她声音沙哑,整个人散发着深深的疲惫和无力感。
「阿姨,江怀……江怀死了……我知道了……」
「他捐献的遗体,去了我们学校,我……我看到他了……」
她愣了几秒,嘴唇颤抖着,突然起身抱着我失声痛哭。
「言言,江怀走了,他走了……」
「你们准备结婚前,他查出了白血病,他不想让你知道,他不想耽误你啊,更不想让你看到他头发掉光,瘦得皮包骨的样子……」
「他也想活下去啊,他跟病魔抗争了四年,我吃了四年素,一步一叩首求了无数次菩萨,让我去替我的孩子死,所有的罪让我来受,可我的孩子还是走了……」
四年,白血病……
这些词语,像把钝刀,一下下割在心上。
她摇摇晃晃起身,脚步虚浮走进房间,递给我一本相册。
这些照片,他说,要放在他的骨灰盒里。
我颤抖着打开,里面全是我们的照片。
从18 岁到26岁,八年间的恋爱点点滴滴。
最后的几张,是我的背影。
图书馆看书的侧脸,学校路边的背影,比赛领奖的笑脸。
原来这些年,他都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望着我……
「还有这个……」
江阿姨递给我一个小盒子。
盒子上蒙了一层尘土,里面是一枚钻戒,时间久了,已有些氧化暗沉。
「他四年前买的了,准备求婚用的。」
「他说,把戒指,放在他的骨灰上,来世,他一定要送出去的……」
我盯着那枚不再璀璨的钻戒,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变得模糊不清,身体的力瞬间被抽空般。
颓然瘫软在地,心里堵得喘不上气。
原来心痛到极致,是哭不出来的。
「江怀你个混蛋……」
四年啊,这四年他有多痛苦啊。
而我在干什么?
我为什么没有死缠烂打赖在他身边呢?他一个人被病魔折磨了四年啊……
江怀啊江怀,你是要我愧疚一辈子吗?
「他从小就跟着我吃苦,被人骂小杂种,被人欺负,这些年,我一个人把他养大成人,从没想过再嫁,我想让他知道,我是他一个人的妈妈,没有任何人可以抢走。可临终前,他说希望自己妈妈和女朋友都能嫁个好人,有个好归宿。」
「言言你别怪阿姨替他瞒你这么多年,他明白你知道后一定接受不了,他宁愿你恨他,也不愿你放不下他。手机里是自动回复,是他病了以后就开始写的程序,写了四年,我不知道都有什么,他说有很多话。」
「他说,怕你忘了他,又怕你忘不了他。」
「按照他的遗愿,身体能捐的捐,他说,这也算支持你的事业了。最后他说,说好了要带你去看雪,听演唱会的,却食言了。」
我瘫坐在地上,哭得泣不成声。
每一个回忆都变成了利刃,在心上反复切割,曾经的美好如今却成了最残忍的折磨。
我情愿你变心了,娶了别人,却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你死了的事实。
19
我将自己关进房间,反复和手机里的江怀对话。
直到手机耗尽最后一格电。
「江怀,这四年,你到底录了多少话啊?」
「嘿嘿,可能你这辈子都听不完。」
我突然破涕而笑。
学校教务处问我:「陈老师,人体解剖课需要别的老师替你一下吗?]
「不用了谢谢。」
「那个 52号大体老师……」对方欲言又止。
「他是我丈夫。」
江怀,我陪你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有两个学生第一次上课,害怕得不敢上前。
「那些你们惧怕的鬼,可能是别人朝思暮想,再也见不到的人。」
「陈老师,听说您是坚定的唯物主义?」
有人好奇地问我。
从前是。
我一直坚信,人死后就是一团物质,然后会彻彻底底消失在宇宙。
我不信鬼神,不信因果轮回。
可如今,我却无比希望,人可以有来生。
我换好无菌服,戴好口罩,开始认真上课。
「这堂课我们学习剥离皮肤组织和脂肪,然后进行胸部局解。」
有个学生拿着手术刀,有些颤抖。
「老师对不起,我……我下刀偏了……」
我笑笑,安慰她:
「没关系,他人看起来凶,但其实是个很好的人,不会怪你们的。」
「可以在他身上划错千刀万刀,也不要在病人身上划错一刀。」
我聚精会神,平静地操作着。
现在是浅层皮肤组织。
下面暴露的是浅筋膜。
「翻开胸大肌和胸小肌后用解剖刀将前锯肌在各肋骨上的起点一一剥离。
「在第1肋间隙剪开肋间组织,经开口处插入肋骨剪。在第1肋的肋骨与肋软骨连接处,剪断第1肋,再向外下剪断第2肋骨。然后,沿腋前线向下剪断第 3-8肋骨。」
「将肋胸膜与胸前壁钝性分离,将胸前壁完全向下翻开,置于腹前壁的前面。」
「接下来是心脏……」
我闭了闭眼,脑子里响起他孩子气的调笑。
「我就是全天下最专一的男人。」
「来来来,不信你拿手术刀,把我心掏出来看看。」
江怀,我看到你的心了……
20
江怀捐献的遗体完成了最后的价值。
火化后,我挑了件最漂亮的婚纱穿在了身上,将戒指戴在了自己无名指。
将另一枚男士戒指,放进了骨灰盒。
「江怀,把戒指戴好,记得你是有老婆的人,不许在下面看别的女鬼。」
「十年前我写给你的那封信,你没来得及看,我现在读给你听。」
「亲爱的江怀同学,我提起笔写下这封信,正想象着 30岁的你打开它时的模样,我不知道30岁的江怀是什么样子的,成熟稳重?事业有成?
我想此时我们应该已经组建了家庭,有了自己温馨的小窝,有了可爱的孩子。
好好奇我们的孩子是男是女,像你还是像我?我们还会吵架吗?
不知道 30 岁的你有没有变心,还会不会耐下性子哄我。
江怀,我好像从来都没向你表白过,江怀同学,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20岁的陈言真的好爱你,无论过多少个十年,你永远是我生命里最耀眼的那道光。
我在你身边种了棵古槐树,你说你喜欢槐花盛开时,夏风吹起时的清香。」
我化着精致的妆,白纱拖地,笑着跟他一句句说着。
「言言,难受你就哭出来。」江阿姨劝我。
我笑着摇摇头:「阿姨,我不难受的,我很开心的。」
这些年,自己好像一直被关在密不透风的废墟里,无尽的灰暗与荒芜。
当那道光出现的时候,喜欢瞬间便具象化了。
我们都没有攒够一辈子的幸运值,但过去八年的时光,足够我回忆一辈子了。
21
我平静地做完一切,依然按部就班工作、学习、睡觉、吃饭。
闲下来便玩那个一直卡在最后一关的小游戏。
每天睡前,习惯和江怀聊一会天。
[hi,江怀同学。」
[我在。」
「明天多少度?」
「明天气温 15-28 度,微风,多云,早晚温差大,记得带外套。」
「江怀,你在忙什么啊?」
「最近来的鬼比较多,系统有点崩,我在努力修 bu g。」
「那你注意身体,少熬夜,不要抽烟。」
「收到,一定严格执行。」
「江怀同学,说句情话吧。」
「陈言同学,我在地府很想你。」
「你什么问题都知道吗?」
「那当然。」
「江怀同学,你知道游戏的最后一关怎么过吗?」
「墙角有个拿着玫瑰的小男孩,去找他就可以啦。」
我顺着他的指令,在游戏不起眼的角落,看到一个小男孩,留着银色的头发,衣服左侧胸口处,竟然写着很小的「陈言」二字。
我走到他面前,接过他手里的玫瑰花。
天空瞬间升起烟花,游戏画面突然变成了一片玫瑰海。
最后化作了一句[marry me]。
我握着手机,积攒多时的情绪,顷刻溃不成军。
我蜷缩在床上,哭到不能自已。
「江怀,我……我真的好难受……你能哄哄我吗?」
电话那头的他,声音软了几分。
「陈言同学,其实我并没有消失,只是换成了另一种方式在你身边。是你下班路上的风,是清晨推开窗时的阳光,是你夜晚仰望星空时的繁星。」
「陈言同学,一定要活够一百岁再来见我。」
22
后来,我自己去漠河看了雪。寒风凛冽的冬日犹如一场盛大的白色盛宴。夜空中的极光像误撞进午夜里的彩虹。
那里,有首歌很火,我反复听到失眠。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
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
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
我怕我的眼泪,我的白发,像羞耻的笑话。】
我自己坐着火车,去隔壁城市听了周杰伦的演唱会。
我在台下跟着众人合唱: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风偏偏雨渐渐将距离吹得好远。
唱着唱着,就哭了。
你走后的第十年,我还是习惯每天和手机里的江怀同学对话。
你这个家伙,不爱说话,不太会哄人,却用生命最后的四年,说了未来几十年所有的话。
江怀同学,我一点都不孤单。
你好像棵蒲公英,虽然枯萎了,可风一吹,这世界到处都是你的影子。
你走后的第20年,我已不再年轻。
有事没事都会去看你,每次都会叮嘱花店老板。
「不要菊花,我爱人喜欢玫瑰,要一束橙色的。」
我一个人去了布达拉宫,我望着神态各异的佛像,突然潸然泪下。
我点了三炷清香敬神明,不求今世,求来生。
你走后的第30年,我身体也不大好了。
坟前的古槐早已枝繁叶茂。
「江怀,你还记得上学时我们学的课文吗?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当年只觉古文晦涩难懂,如今已是书中人,才读懂作者的思念。」
「江怀,我记忆力好像变差了,有白头发了,眼角皱纹也多了,我好老啊,你一定认不出我了吧?」
我抚摸着他墓碑上的照片,二十岁的模样,他笑得眉眼弯弯,
「只有你这个家伙,永远这么年轻。」
你走后的第40年,我抱着花,步履蹒跚地走到你的墓前。
空山新雨后,我一遍遍擦拭着墓碑上的水珠。
「江怀,我好像活不到一百岁,要等不及去见你了怎么办?」
我问他,他不语。
古槐树上蝉鸣阵阵,远处天边架起一座彩虹。
初夏的风吹过,槐香遍野。
雪白的花朵,随风簌簌飘落。
我怔怔抬头,槐花落在我的白发上。
「江怀你看,下雪了。」
病床前,我戴着氧气面罩,听着学生汇报完最后的实验数据,终于松了口气。
他们问我:「老师,您还有什么心愿吗?」
我一生救人无数,却遗憾没有机会去救回自己的爱人。
我死后,将所有财产无偿捐献国家,将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希望未来,不再有绝症。
火化完也将我也葬在那棵古槐下,有人等我很久了。
我望了眼窗外 缓缓闭上了眼。
番外
「醒了,老婆你终于醒了!」
我恍惚间睁开眼,便瞧见双眼通红、满脸狼狈的江怀。
「江怀,你……你还活着?」
我颤抖着伸出手,想要触碰他的脸庞,确认这一切不是梦境。
「现在是哪年?」
他眼中布满血丝,脸上还带着未干的泪痕,焦急地看着我,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
「2024 年啊。」
「江怀,江怀你没有死,呜呜……」
泪水瞬间夺眶而出,我激动地起身就要去抱他。
我妈和江怀的妈妈,在一旁急得大叫:
「快叫医生,怎么麻醉完脑子出问题了。」
「哎呀别动,刚做完手术,扯到刀口疼啊。」
「手术?」我努力回忆着
「对啊,剖腹产手术,你局麻不耐受,就改成了全麻,睡了好久,可担心死妈妈了,菩萨保佑,终于醒了……」我妈抹了抹眼泪。
江怀……
我又不确定地看了他一眼,站在我面前的是活生生的人。
「还说这个江怀,你生个孩子,他哇哇哭,整个医院,就他哭得声音大。」
我妈控诉着他,他有些不好意思挠了挠头。
「孩子?」
我生了个孩子?
他转身伸手去抱孩子,动作却十分笨拙。
「啊对,老婆你好牛逼,竟然生了个孩子,你看,长得好可爱。」
江阿姨在一旁骂他:
「哎呀哪有你这么抱孩子的,跟拎狗崽子一样!」
「你得让小孩的头枕在手臂上,另一只手托住小孩的屁股。」
「饿了是不是,快去冲奶粉。」
「言言伤口疼不疼,疼得话按一按镇痛泵。」
我看着这一幕,听着一言一语,不知是梦境还是现实。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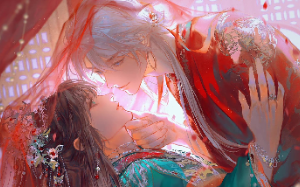



看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