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张学良到了晚年,常常提起过去的事儿,他说:“要说我这一辈子,最不遗憾的就是把蒋介石给抓了。但最让我心里过不去的,就是错杀了杨宇霆。”
前半辈子,他被关了起来,像笼中鸟一样失去了自由。而后半辈子呢,有个阴影一直笼罩着他,让他连想都不敢细想。他常常在想,自己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呢?


【1936年,张学良决定“扣住天子”】
西安那地儿,天还没露出鱼肚白呢,冷得直往骨头缝里钻,跟冰锥子刺似的。在华清池那边,蒋介石披着个睡袍,慌慌张张地翻墙想要逃跑。结果他半个身子愣是卡在了墙里头,脸紧紧贴着那冰凉凉的砖头,别提多狼狈了。
几个守卫猛地冲上前去,一把将人拉了下来,按倒在地上,枪直接顶在了那人的脑门上。张学良就站在门口,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紧绷得跟铁板似的:“把他带去谈判。”
蒋介石坐在火堆旁边,没碰那杯茶,也没发脾气,只是用冰冷的眼神瞅着张学良。

氛围紧张得跟绷紧的弦似的,张直索性直截了当地说:“委员长,要是再不抗日,我可真要采取极端手段,来个‘军事劝谏’了。”
蒋没有明确表态,张学良那边也按兵不动。说起西安事变,这可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精心策划的一盘棋。
东北被日军占了五年,老张亲眼瞧着咱的地盘一点点没了,成千上万的人没了命,可老蒋呢,一门心思就想着打内战。这事儿,老张心里头憋屈太久了,实在是受够了。想想这五年,东北的大好河山,愣是一块块被割了出去。老百姓的命,就像草芥一样,说没就没了。一万个人里头,能活下来的能有几个?可老蒋呢,他对这些好像视而不见,整天就琢磨着怎么跟自家人斗。老张心里头那个急啊,他恨自己没能耐,也恨老蒋的不争气。眼瞅着家园被毁,亲人遭殃,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这内战,不打也罢,咱得先一致对外,把失去的夺回来啊!
当年,张作霖父亲被日本鬼子炸身亡那会儿,他默默地跪在老爹遗体前面,硬是一个字都没吭声。但心里头那股子怨气,足足憋了整整五年,最后全都释放了出来。
他轻轻吐出一句:“我再也不想背负亡国之将的名头了。”这话虽轻,却在南京政府里掀起了轩然大波。蒋介石气得手直哆嗦,但无奈寄人篱下,只能先咽下这口气,签署了停战协议,答应联手抗日。
大家都拍手称赞,同时也满心期待后续发展。当张学良把蒋介石安全护送回南京的时候,其实没几个人知晓,他既没开口要官职,也没请求增兵。他只是悄悄地跟着上了飞机,随后就像人间蒸发一样,没了踪影。

他被软禁了起来,这一关就是大半辈子的时间。要是换做任何其他人,恐怕早就被逼疯了。但他呢,没疯,心里头也从没闪过一丝后悔。
在他还没到西安那会儿,有一件事情让他心里老是放不下,一到夜里就反复琢磨,醒来时满头是汗。他抓蒋介石这事儿,他从没后悔过,但有个人他动了手,却是他这辈子最后悔的——那个人就是杨宇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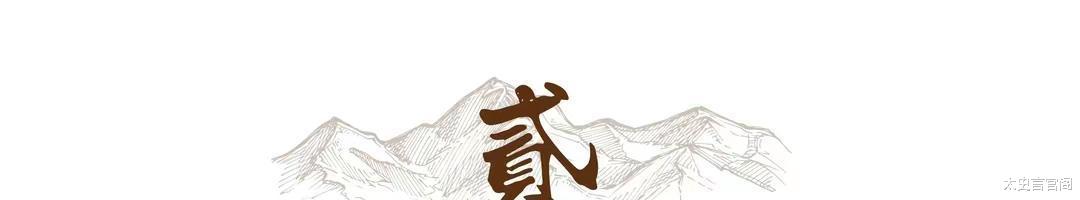
【张学良掷铜板,决定一条命】
1929年冬天,东北那疙瘩的风比西安刮得还要猛,雪花砸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张学良那会儿正坐在他大帅府的书房里,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他听到门外有人走来走去的声音,可他就是憋着没吭声。
桌子上摆着俩铜钱,已经连着抛了三次,每次都是正面朝上,心里头就跟被啥重物压着似的,这回可是来真的了。
当他吐出“杨宇霆,得除掉”这几个字时,心里头已经明白,自己这回是走到头了。

说实话,这次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不是关乎名声大小,而是心里头的那份沉重。我这辈子头一回深刻体会到,要决定结束一个人的生命,真不是像下个军令那样轻松简单的事儿。以前总觉得,那些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们,下个命令就像喝水一样自然,但现在我才明白,那背后的重量,真的压得人喘不过气。决定一个人的生死,需要考虑的太多,不仅仅是命令的执行,更多的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后果的承担。这次,我真的感受到了,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让我意识到,杀人这事儿,真不是随便说说那么简单。它关乎人性,关乎道德,更关乎我们内心的那份良知。所以,我得说,决定杀一个人,真的远比下军令要复杂得多,也沉重得多。
杨宇霆到底是何方神圣?他可不是什么冤家对头,而是张作霖身边的重要助手,东北军里的核心人物。想当年,张作霖还得亲切地喊他一声“杨大哥”。但如今时过境迁,这位曾经的“杨大哥”却成了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说起东北易帜那事儿,南京政府那边想让全国都用一样的国旗,张学良呢,他点头同意了。
小时候,我心里头一股子倔劲儿,琢磨着要走出一条和老爸不一样的道路,不想再重复他那种地方大佬的生活。可杨宇霆这家伙,就是不买账,直接站出来唱反调,明确表示不支持我的想法。
“东北为啥要服软?张作霖费了十年工夫才占下的地方,凭啥说给就给?”杨对蒋不信任,对南京那一套规矩也不买账,他心里头只认兵力和武器。

他是个当过兵的人,说话声音洪亮,性格直爽,而且特别倔强,从不服软。
在张学良眼皮子底下,那人竟敢猛地一拍桌子,好几回开会时,直接就当着大家的面跟人顶撞起来,一点面子都不留。这人可真是够大胆的,丝毫不顾及张学良在场,会上几次三番地跟人较劲,说话那叫一个冲,简直就是往人家脸上招呼,丝毫不留情面。每次那场面,都让人看得瞠目结舌,心想这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在这么多人的场合,如此不给张学良面子。
张学良表面上看还在咬牙硬撑,但心里头已经凉透了。他渐渐悟出一个道理:权力这东西,试探不得,一旦让人看出你软弱,那就等于给自己判了死刑。
到了真正要下决定的那天,他一宿没睡,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灰缸都满了三次。窗外大雪纷飞,积雪都快跟人一样高了。他却迟迟不敢在那个命令上签字,心里头直打鼓,生怕自己将来会变得面目全非,成了那种不忠不义、让人寒心的少帅。
结果那张纸还是写了下来,到了第二天清早,杨宇霆和常荫槐就被喊到了长官府邸。他们连凳子都没来得及沾边,后脑勺就挨了枪子儿。

枪声一炸,整个沈阳城仿佛瞬间静止了那么一下。
没开庭审判,也没给机会去说清楚,罪名倒是写得挺光鲜——说是勾结敌人背叛国家,其实呢,就是私下里争斗,想清除对手。
杨宇霆去世后,并没有被送回老家安葬,而是在当地就进行了埋葬。张学良为了表示对杨宇霆家属的抚慰,给了他们一笔不小的安顿费用。
他没来露面,也没去送行,更没说什么告别的话。但就在那个不幸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口气喝掉了一瓶白兰地。结果,他吐得到处都是,一边哭一边大声喊了一句:“杨哥啊!”
身边的保镖们一个个都小心翼翼,谁也不敢拿出笔记本来记录,更没人敢多嘴多舌。

杨宇霆离世之后,东北那边换旗的事情进行得很顺畅。蒋介石悄悄给张学良发了封电报,里头写着:“少帅那份爱国的情怀,真是让人打心底里佩服。”可张学良呢,一直没给回电。
干掉杨同志,本意是想让抗日这条路能更顺畅,但这一举动,实在是过于严厉了。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能通过这一步,让抗日的事业能够更加稳步前进。然而,回过头来看,这一决定确实下手太重了。我们原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抗击外敌,保卫家园,只是有时候,为了大局,一些牺牲在所难免,但这一刀,确实让人心里不是滋味。毕竟,每一个同志都是宝贵的,他们的离去,都是我们共同的损失。

【两个决定,一生反差】
张学良年纪大了以后,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耳朵不太好使了,说话也变得慢悠悠的。不过,只要有人跟他聊起“西安”,他那双眼睛立马就炯炯有神起来;而要是一提到“杨宇霆”,他的手就会不由自主地颤抖。
他反复说过这样的话:“抓蒋介石这事儿,我一点也不后悔,就算因此被关一辈子,我还是觉得这么做没错。”
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身边的好多人都跟他说,应该把张学良给处理了,说他是“军阀插手政事,坏事儿干尽”。但蒋介石呢,他没听那些人的话,没对张学良下手,只是把他给关了起来。

张学良呢,他也没跑,没喊冤,更没写过啥认错的小纸条。这么多年,他就是不争不闹,一直被关着,直到老去。
但他有一件事情是无法避免的,那就是做梦。
杨宇霆老是在我梦里出现,他穿着一身老旧的军服,就站在沈阳那白茫茫的雪地里,静静地站着,一句话也不吭声。每次梦回,场景都一样,他就那么笔挺地站在那里,仿佛时间在他身边都静止了。沈阳的雪,大片大片地落下,覆盖在他的肩头,可他就像一尊雕像,一动不动。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梦里头的他,总是不说话。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眼神里藏着很多故事,那些关于过去、关于沈阳、关于那段穿旧军装的日子,他可能都深深地记在心里。虽然梦里的他沉默寡言,但那份坚毅和执着,却让我每次醒来都印象深刻。杨宇霆,这个名字,和他的旧军装、沈阳的雪地,一起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久久难以忘怀。
张学良晚年时,跟亲近的朋友聊起往事,他感慨道:“要是那时候我没下那个决定,可能东北军后来的境况会大不一样。”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他是真心这么认为。
杨宇霆离世不久后,东北军的士气就开始下滑了。好多老一辈的将领都觉得心里凉飕飕的,认为老张做法太不近人情,于是纷纷选择退出,不再过问军中事务。
后来,张率带着他的东北军进入关内,打算和中央军一起作战。但没想到,他们一路上连连吃败仗,丢掉了好多地方。打着打着,这支部队就逐渐散了,士兵们各奔东西。

东北军啊,最后并非在战场上倒下,而是被士气给拖垮了。说起来,他们本应是英勇善战的队伍,但到后来,那股子冲劲和斗志却渐渐没了。不是敌人太强大,而是自己心里的火灭了。就像一棵树,根要是没了水分,叶子自然就得枯黄。东北军就是这样,士气一散,整个队伍就没了魂儿。战场上,拼的不光是武器和人数,更重要的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可惜啊,东北军到最后,这股劲儿没了,也就没法再坚持下去了。所以说,他们不是败给了敌人,而是败给了自己,败给了那日渐消沉的士气。
张学良心里跟明镜似的,但他就是憋着不说,变得越来越不爱讲话。好多人来找他聊抗日的事儿,他都挺乐意分享。可只要一提到杨宇霆,他就立马闭口不谈。有一次,人家正拿着录音机录呢,他一摆手,直接给关上了,说了句:“这事儿,我提都不提。”
他老爱提起的,其实是关于西安事变的那段历史。
1936年那会儿,他直接把蒋介石给“请”住了,硬拉着老蒋坐下来谈条件。从早到晚,吃饭睡觉都不让老蒋离开视线,就连上个厕所,都有人在外面候着,真是看得紧紧的。
蒋被惹火了,直接骂他是个“粗鲁的家伙”,但他呢,还是一脸和气,不停地给人递茶倒水。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最后两人还是把统一抗日的事情给商量妥了。

好多人都讲张学良行事冲动,但其实这事他老早就有打算了。他和周总理悄悄见过面,跟杨虎城也一块儿商量过,就连军队的调动,也都是背地里安排妥当的。
这次事情搞定得特别快,总共就三天时间,蒋介石就被抓住了,而且还没人牺牲。这事儿让张学良挺自豪的。
但他对杨宇霆的事儿,没敢直接点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杨宇霆那边的情况,我搞得有点糟。”边上的人一听,心里都明镜似的,觉得这是说他“政治上不够老练”。但张学良自个儿心里有数,那哪是什么“搞得糟”,简直就是“彻底翻脸”了。

说起来这两码事,一件关乎国家大义,另一件呢,关乎当时的局势。一件事,有人敢大声宣扬;另一件,却只能默默藏在心底。捉拿蒋介石,那可是豁出命去的行动;而处决杨虎城,则是割舍了深厚的情谊。
蒋介石到了晚年,在他的日记里头是这样写的:“张汉卿这人吧,虽然有时候会犯错,但他是忠心的;做起事来有时挺倔,可心里头是真诚的。”这短短一句话,就算是给张学良的一个总结性评价了。
张学良听后,只是淡淡地回应道:“那家伙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张学良的结局,藏着太多反转】
张学良这辈子,一开始就是众人瞩目的少帅,可到最后,却成了人们口中的“囚犯”。有人问他,这一辈子走过来,到底值不值当,他倒是挺豁达,笑着回应说:“至少我还活着呢。”他年少时风光无限,身为少帅,手握大权,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然而,世事难料,后来的他经历了许多波折,最终失去了自由。尽管如此,当被问及这一生的得失时,他并没有显得太过在意。在他看来,或许人生的价值并不在于地位的高低,也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而在于自己是否能够坦然面对一切变故,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所以,即使最后成了“囚犯”,他也能够笑着面对,因为在他看来,只要还活着,就还有希望,就还有未来。
到了晚年,他选择在夏威夷安享时光,因为腿脚不便,出行得靠轮椅帮忙。那时候,他周围只有几位老朋友和细心的护士陪伴着。
我平时不怎么读报纸,也不太聊政治话题。有时候,我会拿起书翻一翻,或者动动笔写点东西。但要说最常做的,那就是练写一副对联了:“世间存浩然之气,万物各展其姿。”

有人曾经这样问过他:“要是说你这辈子最自豪的事儿,那是不是就算西安事变了?”
他呆了片刻,回答道:“这不是说我有多得意,而是确实有这个需要。”话说得轻描淡写,但他的眼神却显得异常深沉。
然后我又问:“有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事情呢?”他沉默了一会儿,没有直接回答。
隔了好久,他才缓缓开口:“我以前干掉过一个对我老爸忠心耿耿的家伙。”
大家都知道那晚的事儿,说的是谁心里都有数。他孤零零地坐在那把藤椅上,从夕阳西下一直坐到夜幕深沉。手里的雪茄,才抽了一半,就静静地熄灭了。
后来,护士跟我们讲,他那一整晚都没合眼,眼睛就直勾勾地盯着窗外。外面的风呼呼地吹,把纸窗吹得吱嘎吱嘎直响,可他愣是一点儿也没动。

张学良这辈子走了两步弯路:第一回是轻信了蒋介石,结果把自己给关了一辈子;第二回呢,是没听杨宇霆的话,结果就像是砍掉了自己的得力助手一样。说起来也真是让人感慨,张学良当初要是没那么相信蒋介石,可能就不会落得个被囚禁的下场。而要是他能多听听杨宇霆的意见,或许很多事情都会不一样,他也不会失去那么重要的一个帮手。这两步走错,真的对张学良影响特别大。第一个错误让他失去了自由,后半生都在囚禁中度过;第二个错误则让他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智囊和伙伴,让自己的力量大打折扣。所以啊,有时候,相信谁、不信谁,真的是个大学问,一步走错,可能就满盘皆输了。
人上了年纪后,很多事情都能看淡、放手,但偏偏有两样东西始终难以割舍。岁月流转,人们会慢慢发现,曾经的执着、纷争,到了老年大多都能一笑置之。然而,总有那么两件事,像是心头的一颗朱砂痣,怎么也忘不了。第一件事,或许是对过往美好记忆的眷恋。那些年轻时的欢声笑语、奋斗岁月,即便时过境迁,依旧在心底深处熠熠生辉,让人无法割舍。第二件事,则可能是对家人深深的牵挂。无论儿女是否已成家立业,作为长辈,那份担忧与关爱始终如影随形。毕竟,血浓于水,亲情的力量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所以说,尽管老年人能放下很多身外之物,但对美好回忆的怀念和对家人的深情厚谊,却是他们一生都难以释怀的珍宝。
在聊起自己那些年的往事时,我几乎把什么都说了,打仗、和人商量事儿、暗杀行动、被关起来、被赶到外地……不过,说到杨宇霆,我就简单提了一句:“我让人把他给解决了”,既没说为啥,也没细说当时的情况。

他心里明白,这事儿压根儿就说不清楚。
回首这一生,经历的起起伏伏,就像是面前摆着的两条不同方向的小路,自个儿挑了一条走下去,就再也不能折返回来重新选了。这一路上,有风光也有坎坷,但都是自个儿的选择带来的结果。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想想过去的那些事儿,就像是放电影一样在脑海里过一遍,有的让人心里美滋滋的,有的又让人忍不住叹气。但不管怎样,路都是自己选的,得自己走完。有时候也会想,如果当初选了另一条路,现在会不会有所不同呢?但这也只能是想想罢了,因为人生没有如果,也没有回头路可走。只能坚定地沿着自己选的路,继续往前走,不管前方是荆棘还是坦途,都得咬牙坚持下去。所以说,这一生的荣辱得失,其实都是自个儿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既然已经选择了,就别再后悔,更别抱怨。因为生活就是这样,不会给你第二次选择的机会。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现在,好好地走好接下来的每一步。
他并非战场上最耀眼的将军,也不是政坛上最落魄的政治家。他是张作霖的儿子,那位曾经让蒋介石吃了三天两夜苦头的少帅。就是他,下令处决了自己的把兄弟杨宇霆,让杨宇霆走上了不归路。
他这一辈子,始终被三个不同的角色给紧紧绑着,一直到他离世。这三个身份,就像三道枷锁,一直伴随着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如影随形。他试图挣扎,试图摆脱,但最终还是没能成功。它们不仅定义了他的生活,更影响了他的命运。从年轻时起,他就感受到了这三个身份带来的压力。它们既是他前进的动力,也是他沉重的负担。他不断地在这三个身份之间寻找平衡,试图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然而,无论他如何努力,这三个身份都像是一道无形的墙,将他困在了里面。他无法逃脱,也无法忽视它们的存在。它们成了他生命中无法抹去的一部分,伴随着他度过了漫长的一生。直到他离世,这三个身份依然紧紧缠绕着他。它们就像是他生命的印记,永远地留在了他的身上。虽然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故事,他的经历,以及他那三个无法摆脱的身份,都将被后人铭记。
他离世的时候,既没有举办盛大的国葬,也没有鸣枪致意的军礼,就是平平淡淡、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遗嘱中,老爷子没说到蒋,也没提到杨,就吩咐说想把自己的老军装和一张东北的地图,一起带进坟墓里。他就是想让这两样东西,陪他走完最后一程。没有多余的废话,就是这么简单直接,就像他生前的性格一样,干脆利落。军装代表了他过去的岁月,地图则让他记挂着那片曾经奋斗过的土地。这两样东西,对他而言,意义非凡。

尽管张学良曾走过弯路,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挑起了责任的大梁。他明白,人生路上难免会有些磕磕绊绊,但重要的是要勇于面对,敢于承担。张学良没有因为过去的错误而逃避,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决定用自己的行动去弥补那些过失。他深知,担当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行动。于是,张学良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去努力挽回那些因错误而失去的东西。他一步一个脚印,走得坚定而有力,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让自己和他人看到改变的决心。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有担当的人应有的模样。无论过去如何,他都愿意勇敢地站出来,去面对,去承担,去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这样的张学良,让人敬佩,也让人相信,只要有心,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改变,去成长。
一辈子起起伏伏,他给后人留下的不是光彩照人的荣誉,而是一份深刻的警醒。碰到大事大非时,得有那份勇气和魄力;而对待身边亲近信任的人,更得胸怀宽广、有大气度。真正的豪杰,不光是敢冲敢闯,更难得的是,他们敢于承认错误,勇于悔改。
张学良亲自讲述,经由唐德刚细心整理的内容被汇编成了《张学良亲口说历史》这本书,由中华书局在2009年出版发行。在这本书里,张学良用平实的语言,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他没有用太多华丽的辞藻,而是用最直白的方式,将那些过往的岁月娓娓道来。唐德刚作为整理者,很好地保留了张学良的原话和语气,让读者仿佛能亲身听到张学良的讲述。整本书条理清晰,张学良根据自己的记忆,将历史事件按照时间顺序一一展开。他讲述了自己年轻时的军旅生涯,参与的重要战役,以及与各方势力的交往和谈判。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细节,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亲身经历了那些历史事件。这本书没有添加任何不必要的内容,而是保留了最核心、最关键的历史信息。张学良的讲述既真实又生动,让读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关系。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张学良的一生,以及他对中国历史的独特见解。
#百家说史品书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