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这么一个案子,是一桩简单而又普通的刑事案件,整个案子案情清晰明了,既没有刑讯逼供,也没有栽赃陷害,但这个案子后来不仅轰动了宋朝,在整个中国法律史上,都是一件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件,审判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其影响之大空前绝后。在当时引发了朝野的一场大地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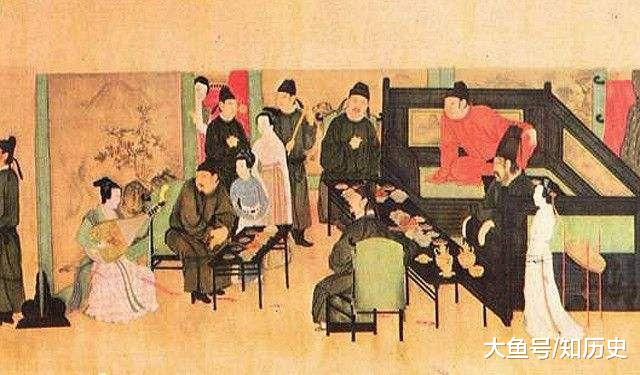
熙宁元年正月,为母亲守孝的13岁登州少女阿云,被叔父以几石粮食的聘礼许配给一位名叫韦大又穷又丑的老光棍为妻。阿云不同意叔父包办的这个婚姻,于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阿云晚上悄悄来到韦大的家里,黑暗中她拿起砍柴刀朝着熟睡的韦大一阵乱砍。被惊醒的韦大慌忙用手阻挡,被砍掉一个手指头。阿云看韦大醒来,又惊又怕,丢掉柴刀,扭头就跑。知县接到报案,通过排查,锁定阿云有重大嫌疑。知县将阿云捉来,少不更事的阿云便将事情的整个由来交代得清清楚楚。此案就此告破。
阿云招供后,知县以谋杀亲夫的罪名判处她死刑。宋朝法律程序严谨,地方死刑案件必须逐级上报,最后由朝廷的最高司法机构——大理寺和审刑院进行复核,经复核没有问题的,才准许地方官对人犯执行死刑。案子报到登州知府那里时,登州知府许遵认为,按照宋朝律法规定,守孝期间的婚约无效,再者阿云是被叔父逼婚,因此这门亲事是不合法的。既然婚约不合法,阿云也就没有谋杀亲夫之罪。以故意杀人来说,韦大并无大碍,阿云罪不至死。于是许遵签上自己的意见,将案子报送到大理寺和审刑院。大理寺和审刑院审查案卷后认为,即便阿云不是韦大的妻子,但是其蓄意谋杀,并且造成了对方人身伤害,按照大宋律法一样要判处死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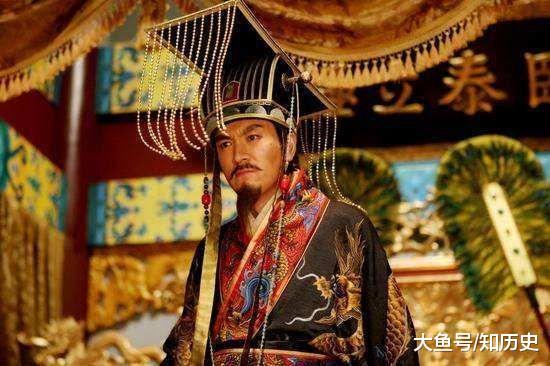
恰在此时,宋神宗下诏说,谋杀已经造成人身伤害,但官员在审讯犯人并对犯人用刑前,犯人如实供认犯罪情节的,以自首对待,并依照谋杀罪行降低两个等级论罪。
这个诏书简直就是为阿云量身定做,按照诏书的规定,阿云最多只会被判有期徒刑。许遵便以皇帝的诏书为依据,向刑部申诉。希望能够救阿云一命。
以大宋律法,皇帝的诏书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刑部不接受许遵的申辩,依然维持死刑判决。
就在看起来阿云确定难逃一死了的时候,事情又发生了戏剧化的转折。许遵被调往大理寺任大理寺卿,掌握了案件复核的主动权,阿云被改判有期徒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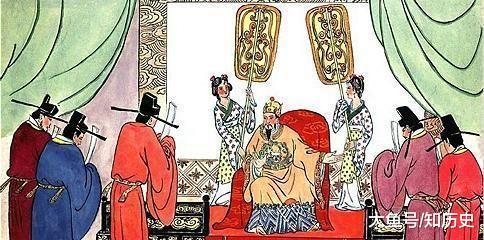
御史台的官员却不愿意了,御史上书皇帝,弹劾许遵,说许遵利用职务之便枉法。神宗皇帝把这个案子发到翰林院,让当时最有名望的两个翰林学士来评判,这两个人便是司马光和王安石。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意见也截然不同,司马光支持刑部的死刑判决,王安石支持许遵的有期徒刑判决,两个翰林学士为此在朝堂上吵的不亦乐乎,谁也无法说服谁。双方争论的焦点,不外乎就是阿云的判决是按大宋律法来,还是按皇帝的诏书来。这实际上就是法律效力大,还是皇帝的诏书效力大的问题,这次争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律敕之争”。
司马光和王安石争论的真正意图不在阿云这个案子本身。当时王安石在朝廷里鼓吹变法,而司马光则是坚决反对变法。如果以皇帝的诏书为准,就证明皇帝的旨意对法律有最终解释权,可以对法律进行修改和变更,而这是王安石推行变法的基础。司马光认为法律是国家最高意志的体现,任何人都不能干预司法,包括皇帝。神宗皇帝看到两人相持不下,又将案子交给其他翰林学士及朝廷官员审议,审议的结果是支持王安石的意见,神宗皇帝御批“可”。

不要以为这样就能结案了,审刑院的官员联名上书皇帝,要求继续与王安石辩论。枢密院、中书省的官员也参与进来,纷纷发表意见。这起普通的谋杀未遂案把大宋的朝堂搅了个天翻地覆,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神宗皇帝便对犯人自首的界定和量刑做出详细解释,命令翰林院按自己的解释拟写诏书,发往中书省,要中书省遵照执行。却被中书省直接驳回,说皇上的诏书违背法律,不能执行。
这下可把皇帝给惹火了,神宗直接下诏,免除阿云的死刑,改判有期徒刑。次年,王安石变法开始。
没过多久,朝廷大赦天下,阿云被释放回家。得以重获自由的阿云嫁人生子。但是她的案子并没有真正结束。

神宗去世,哲宗继位,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司马光当上了宰相,得势的司马光重新审理此案,以谋杀亲夫的罪名将阿云逮捕并斩首示众。时过十七年,司马光终于还是以阿云这条民女的性命来宣告自己的胜利: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哪怕是皇帝!
司马光真实目的并不是非要杀死这个民女来找回十七年前的面子,而是为了让王安石的改革派不再有死灰复燃的机会。
本文来自知历史工作室原创作者/不文
知历史工作室原创作品 未经许可 禁止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