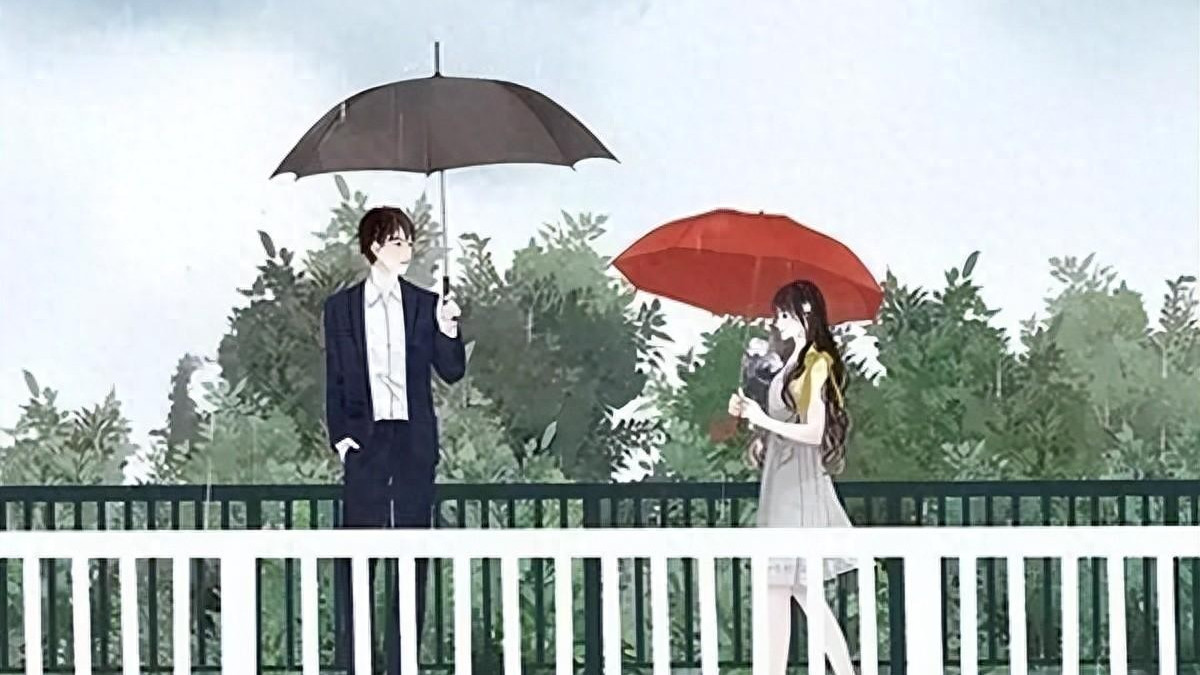简介:
良人啊良人你到底在何方向?
相夫教子是她的理想,奈何滚滚红尘里摸爬滚打,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一生一世一双人,不过是骗人的笑话,原来谁都不是她的良人。良人只是她偶尔行经的风景,美则美矣,却早已停留在她的生命之外。

精选片段: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火红的一千响鞭炮被竹杆高高挑至半空,红红火火地炸响出一地细碎的红屑。只听得窗外一阵锣鼓喧天,出门一看,原来是隔壁的王二今日娶亲。
最前面是迎亲的锣鼓,后面跟着四人抬的花轿摇摇晃晃一路前行。乡里乡亲脸上洋溢着逢年过节才有的喜气。平时傻愣愣的王二今天看上去也格外精神,王叔、王婶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小孩子们无疑是最快乐的,他们奔跑着叫道“看新娘子去喽。”然后一窝蜂的钻进王二家的院子,等着看刚下轿子的新娘子,顺便再讨一些红包、喜糖之类的东西。
农村里最缺少的就是娱乐,所以每当有人婚丧嫁娶,总是全村最热闹的时候。
桑晴以前也是这样的人,但现在这份热闹是别人的与她无关。触景伤情情更伤。面对此情此景她不由想到自己当年嫁到王家时的情景。
她八岁那年父母双亡,独身一人流落到王家村,被好心的王大妈收养,从此便在这里扎下了根。
王硕是王大妈的儿子,是桑晴不太标准的青梅竹马。记得当年是他第一个递给桑晴一个馒头融化了她心中的冰雪,那时在小小的桑晴的眼中他就是安全的代名词,代表着可以信任。
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桑晴爱花,特别是芍药。王硕总会去村外不远的芍药沟采来缤纷的芍药送给她,然后乐呵呵的瞅着她将花朵插在鬓边,一脸的满足。有时他也会亲自为她戴上芍药,但笨手笨脚的他总是把她一头柔顺的长发弄得一团糟,而她也不恼,两人对望着傻傻地笑成一团。
后来她顺理成章地嫁给了他,那年她十四岁,穿着亲手绣制的红绸嫁衣,头盖下是如花的容颜。龙凤花烛红彤彤地照着房间,一盅合卺酒,双臂交叉缓缓饮下,从此他便是她的夫,她便是他的妻。还记得他许下的誓言,“此生只有她一人是他的妻,是他的最爱。”
天不从人愿,新婚当晚,征兵令火速传来,王家村各家各户的青壮年皆应征入伍前往前线保家卫国。
他们依依惜别,她不敢流露出悲伤,因为还有婆婆。婆婆守寡多年,儿子是她仅有的希望,她又怎忍心在她面前期期艾艾?
征人一去千里杳无音讯,不知生死。
桑晴拉下窗帘,隔绝了屋外的喧闹。屋内一盏油灯如豆,昏昏黄黄的灯光映着一个孤寂的身影。她仿佛觉得自己的灵魂在黑暗的灯光中舞蹈,舞出一天一地的孤单和思念。但只有在黑暗中,阳光下的她是晦暗的,因为他的离开。
他去了已有六年。留她一人苦苦撑着一个家。两年前婆婆又由于思念儿子而哭瞎了双眼,自此不事生产。
柔弱双肩怎挑得其如此重担?有时她会怀疑,不知道自己辛苦操持的家他还能不能见到,他还会不会回来。
也许,思念就是最好的养料,支撑着她继续等下去,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只知道要一直等下去,一年、两年,也许是一辈子。
思念就像水草,一旦缠上了就再也无法抽拔出来。等是她的命运,她一直如此相信。
“回来了,回来了!”隔壁的刘大妈兴冲冲的跑进来对着桑晴大喊。
“刘大妈,什么回来了?” 桑晴有些莫名其妙,抬头看了看刘大妈又低头继续做自己的活。今天要帮人浆洗的衣服还没完工,她忙得很。其实她每天都很忙,养活两个人是不容易的事,虽然有乡亲接济,但人生在世靠山山倒,靠人人跑。总得自力更生,才得丰衣足食。
“快别洗了,王家媳妇,你家王硕回来了呀!”刘大妈见她不动,急忙上前去拉她。
“什么?”手中的洗衣棒应声而落。
“别什么、什么的了,快去,快去,都到村门口了。”
“哦,哦。” 桑晴一时六神无主,也不记得和刘大妈道谢就一头冲出门去。
刚走两步就看见前面转角处转出一队人来,个个神情肃穆,一路吹吹打打而来。为首的两个手里各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的什么桑晴却是看不懂。她本是书香门第,但仅仅在八岁前学过些《弟子规》之类浅显的文章,八岁后家破人亡终是不得书香熏染。
她一时愣住,这样的排场,真的是硕哥回来了吗?她不敢问,怕是别家的征人衣锦还乡。
片刻,那队人已离她不远,他们有序地向两边分开让出一条道来。远处隐隐传来马蹄声,只见一骑飞驰而来,扬起漫天尘土。
棕色的骏马在她面前停下,马上的人皮肤黝黑,衬得整个人越发健壮。
是他,就是他,她的硕哥哥!
她张嘴,却说不出一句话。
王硕一路飞驰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一路上他归心似箭,无奈县官乡绅定要为他接风洗尘,只得叫部下先行回去通报。喝过两杯水酒,他迫不及待地上马向祖宅奔去。
两边的草木不断倒退,正是近乡情更怯,他反复地想着不知母亲如何,又不知可好。
近了,近了,家乡的一草一木透露出熟悉的芬芳,祖屋就在前面。一点也没变,一切一如当初的纯朴,变得也许只有饱经风霜的自己。
先行的部下见到他便停下来让路,他不及多想驱马上前。
面前荆钗布衣的女子,呆愣得看着他,晴妹!
勒紧缰绳,他在马上俯视她,她在地上仰视他。仿佛回到初会时,高大的男孩看着瘦小的女孩,便是这个角度,一个仰视,一个俯视。他是她的天,让她一抬头就能看见幸福。
“硕哥哥。”颤抖着声音呼唤他。
王硕翻身下马,紧紧将她搂进怀里,“晴妹!”
六年的等待化为一掬热泪,桑晴在王硕的怀里泣不成声,“你……你终于回来了呀。”
千斤重的一句话片刻间倾吐出来,悲、喜、怨、乐……纵有千言万语也只讲得出这一句。
两人相迎进屋,王硕跪倒在年迈的母亲面前,“娘,孩儿回来了!”
盲眼的母亲摸索着儿子的脸庞,哭瞎了的双眼再次溢出泪水。
看着老泪纵横的母亲,一时间三人哭作一团。
当天王硕带着母亲、妻子住进了安排好的驿站。
没有龙凤花烛,王硕和桑晴在一片喧嚷慌乱中度过了成为夫妻以来的第一夜。
天未亮桑晴便醒了,这是多年来的习惯。她躺在床上,六年来的一幕幕仿佛昨天,而现在身处雕栏玉砌的厢房就像是梦一场。柔软的锦被、精致的帷帐、淡雅的薰香……此生她从未见过。身边的王硕仍在酣睡,他黑了,却未瘦,只显出一种经历风霜后的精壮。
她转向他,此时此刻只有他尚存一份真实感,经过昨夜,他就是她真正的夫。总算是熬出头了,他荣归故里定是有了一番作为。听说他们要搬去京城,他的府第已竣工完毕。她曾听人说起京城的繁华,所以对今后的生活满怀憧憬。
他的背上留着深深浅浅的伤痕,她忍不住伸手去摸。有的已渐渐长平,有的仍狰狞的盘横着。六年来他也受了不少苦,其实她不要他拜相封侯,只要他完好无损的回来,一切就都好了,那怕是一辈子守着贫瘠的土地,她也甘愿。
胡思乱想间她又昏昏沉沉睡了去。
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上路,一路鸣锣开道好不威风。
桑晴同婆婆坐在马车里,时不时好奇地揭开窗帘看看外面的风景。
“晴儿,你过来,我有话要说。”婆婆招招手示意桑晴过去。
“妈,什么事?”
“晴儿啊,我知道这六年委屈了你。”婆婆拉着她的手说,“按名分来说你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是正室,可是……”
桑晴隐隐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她不明就里的看着婆婆。
“可是……可是……”她觉得有些说不出口,过了半晌还是咬咬牙说了下去,“硕儿他受皇上赐婚已娶了丞相之女,所以……只能委屈你了。”
桑晴听了犹如五雷轰顶,一时呆若木鸡,说不出话来。
“晴儿啊,昨天他告诉我的时候我已狠狠骂过他。他自知理亏不敢开口,我只好厚着老脸来跟你讨个饶。晴儿,天命难违,是我们王家对不起你,硕儿答应会好好照顾你,除了名分不同,其他事上你不会受任何委屈。”说罢她掀起车帘子唤进王硕说:“我替你向晴儿讨过饶了,你快发誓会一辈子对她好。”
“晴妹,我……”王硕讷讷的说了几个字,就一径的低着头。
桑晴一时瘫软在坐垫上,婆婆、丈夫的话在耳边乱哄哄的缠作一团。她知道到自己已不是妻,她戴着妻子的头衔苦熬了六年,最终落得一个妾室的位置。
“晴妹,我会好好待你的。我虽然没什么学问但也知道糟糠之妻不可弃。我也是不得已,你……”他殷切的看着桑晴。
“晴儿,晴儿,你倒是说句话呀。”婆婆摸索着想去扶桑晴。
“妈,硕哥,我知道了,我不会怪你们的,你们放心吧。”桑晴强忍着泪水说出这句话。
“妈,你坐车也累了,躺下歇歇吧。”桑晴杏眼含泪看了王硕一眼,便服侍婆婆在车厢一侧的锦榻上躺下。
“晴儿,委屈你了。”
桑晴不语,只是拍了拍婆婆的手,替她掖好被子,然后自己坐到了车厢的角落里。
王硕几次想开口,看这架势生怕自讨没趣,坐了一会儿后就下车去了。
车厢里安静了,桑晴着这令人窒息的安静中蜷缩在车厢的一角。
“晴儿,委屈你了。”六年的煎熬只换来这苍白的六个字。硕哥不再是她一个人的了。她现在刚刚知道,一个男人若不爱你,你连挽回的机会都没有。
丞相的女儿,温婉高贵,不是她这种乡野村妇能比较的。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她能理解,真的能理解。
远赴京城,她背井离乡,无依无靠,不答应又能如何?郎心如铁,自己纵使韧过蒲苇也无济于事。
她的天被撕开了,也许她宁愿等待,至少等待中她还有希望。
赶了几天的路后,王硕一行终于进了京城。
京城的繁华是桑晴不能想象的。她懒得去掀窗帘,却听得到人们喧嚷的嘈杂一片。只有队伍最前头鸣锣开道才让人群向两边散开,风尘仆仆的一队人马从街心不失威风地通过。
就要到了,到了又如何?她真希望这段路程永远不要走完,即使在狭小的马车里过一辈子,她也甘愿。
终是到了,雕栏玉砌的将军府。
门帘被掀开,王硕伸出手想扶她下来。她迟疑着,仍然将手放进他的手里,这是这几天来,他们唯一的一次肌肤相亲。
站在门口,她看着门上的牌匾,龙飞凤舞的几个大字据说是当今圣上亲笔书写,她也看不懂写了什么,或者说写了什么与她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她不过是个妾,只能拘束的站在那里,任来往的仆役向她投来好奇的目光。是的,他们的主子是丞相的千金,她和他们一样为奴为婢。
婆婆也下了车,王硕作着他的孝子,小心翼翼的搀扶着老母。
一个华服高髻的贵妇人从府邸里迎了出来。她很年轻,脸上有着初为人妇的幸福和滋润。她盈盈拜下向王母行礼,又素手纤纤,挽上王硕,动作自然得好像王硕从来就是她的夫。
桑晴看着一群人相携走进大门,多热热闹闹的一家人,她已经被彻彻底底的遗忘了。
她思索着自己要不要离开,只听旁边有人过来招呼她说:“喂,你,说你哪。”
“你是在叫我吗?”桑晴试探着问。到底是京城将军府的丫环,气势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不说你说谁呢!是从老家来的吧,将军安排过了,你跟我来吧。”簪着梅花簪的丫环转身头上的流苏晃荡出倨傲的弧线,虽然桑晴的衣服裁制花色都比她的出色,但在她面前桑晴只有自愧形秽。她低下头跟在丫环身后。
丫环并没有带她进大门,而是沿着外墙走去。
“请问,我们要去哪?”桑晴小心翼翼地问。
“当然是走后门,你还想从正门进去?!”丫环头也不回地说。
“后门”两个字听的桑晴痛彻心肺。
他不是说过糟糠之妻不可弃吗?
他不是发过誓会对自己好吗?
结果,结果她连从正门进去的机会都没有。
是了,是了他曾答应过此生只有她一人是他的妻,是他的最爱。然而呢?男人的誓言从来不可信。原来她还没有学乖。
这也许是府中最偏僻的角落,还好,桌椅床凳还算齐全干净。桑晴打量着她以后的栖身之地,幽幽叹了口气。
“哎,哎,你不要发呆好不好,快点收拾一下,我还有带你去正厅。”丫环不耐烦地看着她,她的主子才是正牌夫人。这种来路不明的乡下狐狸精,浑身上下只有一张脸还能看。
“哦。”桑晴看出她的敌意,不声不响的把包袱里的衣服放进厨里。这些衣服还是路上新添的,没几件,显得柜子里空荡荡的。
“我好了,姑娘请带路吧。”她客气地说。
“不梳头吗?这里好歹是将军府,不要太丢人现眼了。” 蓬头垢面还不自知,整一个乡下土包子。妄想跟主子抢姑爷,她昏了头了!
桑晴拿出随身携带的梳子,自己的确有点妆容不整。坐下来对镜梳妆,随便用木簪绾了个髻,到底是疏忽了,只准备了衣物,忘记她头上与衣物极不相配的发簪。
罢了,女为悦己者容,桑晴已无需装扮。
走进富丽堂皇的正厅,王硕夫妇和王母围坐在八仙桌前,热络的拉着家常。
桑晴有些不知所措的呆立在门口。
王硕注意到她,说:“来,向夫人见礼。”
“不必三拜九叩了,大家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成云歆雍容华贵的笑着。她也是婚后才知道有桑晴这个人的。
一哭二闹三上吊这种撒泼的事她是做不出的。冷了两天脸,爹爹出面调停让他陪了不是,才息事宁人。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嫁都嫁了,又是名正言顺的将军夫人,有些事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否则丢脸的还是自己。堂堂丞相千金岂可与村妇争宠,自降身价?况且桑晴被王硕安排进了最偏僻的角落,如果她乖乖的待着,府里也不差多养一口人。如果她不乖,成云歆眼里闪过一丝寒光,这个将军夫人自己作得也要作,作不得也要作。深宅大院里的事她见多了,让一个人无声无息消失的方法也多得是。
王硕生怕夫人不快,催促着桑晴说:“礼数是不能少的,快向夫人行礼。”
桑晴了然一笑,自己是逃不掉了。她双膝跪地,一叩、再叩、三叩……
每叩一下,她心里就清楚一分,自己是妾!自己是妾!!自己是妾!!!
“妹妹快起来,行此大礼我怎么受得住?”成云歆起身扶起她。这个女人看上去很无害,不过还好是要提防着,小心她扮猪吃老虎。毕竟她长得太漂亮,很少有男人能忽视她的美丽。
男人会英雄相惜,女人不会,太美的女人是全民公敌。
“来,妹妹,我有东西要送给你。你看看那么漂亮的人儿,竟然戴着木簪,相公,你真是疏忽了。”成云歆使了个眼色,身后的陪嫁丫头胭脂双手捧上一个雕花的木盒。成云歆慢悠悠的打开盒子,里面是整套的珍珠首饰。
桑晴明显的感觉到成云歆说话时她身后的佣人们脸上挂着讥讽,她怎么配得上珍珠?她只配戴着木簪终老在她的田间。
成云歆见她不接,说:“妹妹不喜欢吗?”
“不,我喜欢的,喜欢的。谢谢姐姐。”桑晴强颜欢笑。
“试试吧。”成云歆替她戴上手镯、项链,又帮她换了发簪,一边换还一边说:“多配你,天生丽质带什么都好看。相公你说是吧?”
“哦,那是夫人眼光好。”王硕讪笑着。他怎么敢夸她漂亮,要不是不小心被她知道了桑晴的事,他根本不会把她带回来。
桑晴好像是她的娃娃一样任她摆布。
回到房里,桑晴木然的取下身上的首饰。灯光下,圆润的珍珠发出柔和的光芒,她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看的东西,比初升的太阳还好看。但它只带给她屈辱,告诉她自己与他们是如此的格格不入。
又是一个人了。
她躺在床上强迫自己睡觉,不去想明天该怎么过。她是无根的浮萍,随波逐流,明天怎么样,不是她能想象的。
成云歆在宴会散后,闻言之:“你看桑晴怎么样?”
“主子,她不过是脸蛋漂亮了点,一点气质都没有,不过是个刚从乡下来的丫头片子。”胭脂不屑的说。
“你接她进来的时候她说什么了没有?”
“没有,她敢说什么?我给了她个下马威,带她从后门悄悄进来的,让她知道知道自己的身份。”胭脂讲得眉飞色舞,“她呀,包袱里才那么几件衣服,还戴着个木头簪子,笑死人了。也没办法,没见过世面的女人都是这样。我看她是没希望的,就等着老死在那个角落里吧。”
“胭脂!”成云歆喝止住她。
“主子。”胭脂低下头,立刻闭嘴。
“管好你的嘴,不要太看轻她了。她是块璞玉,假以时日说不定就会大放光彩。”成云歆深知任何的松懈都会导致失败,“你给我看好她。每天送饭的任务就交给你了。”这样一来既能名正言顺的监视她,又显得她宽宏大量。
“是,交给我吧,我一定把她看得死死的。”
桑晴每天无所事事。她不出门,因为没地方可去。本来入府的第二天她是想去给婆婆请安的,却被丫环客客气气的请了回去。
丫环是新来的,她没见过。大约是上头关照了,丫环总是送了三餐后就离开从不与她说话。
王硕来过一趟,劝导她不要出门。他说得很有技巧,什么她初来乍到水土不服,府第颇大怕她走失迷路。
桑晴不反驳他,他是铁了心要把自己关在这个角落里的。无妨,心既死,在哪儿里都一样。
她现在的生活像极了大家闺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怕自己会忘了时间,桑晴每天清晨起来总在墙上划一道,日子久了,那些斑驳的划痕倒也生出几分错落有致来。
百无聊赖之际,她突然想起一句戏文——等待良人回来那一刻,眼泪为你唱歌。
她着了魔似的翻来覆去的浅吟低唱着这句不知从何出戏文里听来的句子。她也就会这么一句,反反复复,有时调子高,有时调子低,有时还会唱错。
等待良人回来那一刻,眼泪为你唱歌。
“刻”要发成“阔”,樱唇轻拢似是万般忧愁。她千遍万遍的唱着,任寂寞的声音在空荡的屋子里漂浮。有泪却不落,原来她早已忘记如何哭泣。只有那声音湿湿漉漉。
桑晴其实很容易满足,只是她等得太久。她也曾假想自己在王硕的怀里恸哭,埋怨他的寡情。只要他回来,她就会把等待中受过的种种委屈尽数化作一场梨花春雨,而这点点泪水便可以滋润她近乎干涸的心灵,让她忘记过往的磨难。
然而在她整个将军府的生涯里,他只来过三次,从头至尾只来过三次。
忠心的胭脂每天向成云歆报告桑晴的状况。当说到她有事无事嘴里哼的歌时,胭脂撇撇嘴说:“也不知道她中了什么邪,反反复复唱这一句,不会是疯了吧。”
成云歆长叹一声:“还是不死心啊,她等得便让她等。你嘱咐琉璃一日三餐切莫苛刻了她。”
她深知自己和王硕的婚姻是政治婚姻。对王硕而言丞相的乘龙快婿的比将军自是高出几分,对父亲来说又多了一员得力干将。两全其美之时,她的感受自然不重要。
说到爱不爱王硕,这很难说,不过一定是比不过桑晴吧。她一直就有联姻的觉悟,在爱情方面还算看得开,无非是嫁一个还过得去的,生几个子女在膝下亲近,相夫教子,稳坐正室之位,一生也就这么过去了。爱与不爱是一项奢侈的选择,合得来就好,至少面子上能相敬如宾。
王硕人高马大,虽然未曾饱读诗书,但一身彪悍的气势仍不失为夫婿的好人选,对她也算不错,日日嘘寒问暖,可谓关怀备至。足矣,若能诞下麟儿,已无憾矣。
想到这里她不禁微微有些脸红。一旁的胭脂打趣道:“主子怕是想姑爷了吧!”
她催了她一口,“小蹄子,忙你的去吧,少嚼舌头,小心我随便找个小子把你配了。”
胭脂笑嘻嘻的往外走说:“主子才不舍得呢!”
这一天,来送饭的丫环全身缟素,头上还带着一朵白花。
“请问,府里有白喜吗?”桑晴不安的问,若说到有人过世,莫非是婆婆?
“老夫人故去了。”
“什么?今天是几七了?”桑晴大惊,婆婆没了!?
“头七。”
桑晴听了急急向外跑去。婆婆对自己有多年的养育之恩,她故去了这样的大事竟然没有人来知会自己一声。
“哎,你去哪儿?”丫环拦住她。
“我要去灵堂上香拜祭。”桑晴不顾她的阻拦继续向前走去。
“这怎么行?你不可以出去的。”老爷吩咐过她是不能出去见人的,自己又拦不住,这可怎么办才好?
正在两人僵持不下之际,胭脂闻讯过来问:“怎么回事,琉璃?”
“胭脂姐姐,她一定要去老夫人的灵堂拜祭,可老爷吩咐过,她不可以随意出门的。”琉璃见救星来了,立刻竹筒倒豆子般的诉苦。
“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我会解决的。”胭脂示意她先离开,然后转向桑晴说:“灵堂里姑爷的朋友、同僚络绎不绝,岂容你出去丢人现眼?好好待着吧!”
“我是婆婆的儿媳妇,我要去,一定要去。”桑晴争辩着,现在的她有着难得的强硬。
胭脂白她一眼,“你当自己是她的儿媳,她可不这么认为,少往自己脸上贴金。实话告诉你吧!姑爷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你的存在。你要认清身份,你连二夫人都称不上。”她特意加重语气地说出“二夫人”三个字。
桑晴不管不顾,一把推开她就向外冲。胭脂一时不察被她推了个趔趄,心下大怒,招呼家丁说:“快拦住她,若将军知道她出去了,有你们好受的。”
桑晴跑出几步就被家丁摁住,胭脂气喘吁吁的追过去说:“跑呀你!再跑呀!你们把她押进去,不准让她出来!”
处置好桑晴胭脂急忙跑去灵堂,蹑手蹑脚的走道成云歆身后告诉她刚才发生的事。
成云歆秀美紧锁说:“做得好,我没想到她还是个烈性子,这样,让姑爷处理吧!索性让她断念死心。”
胭脂答应着,瞅空向刚从与同僚的寒暄中脱身的王硕报告情况。
桑晴挣扎着被推进屋子里,听着门外的人落锁的声音,她扑到门上使劲拍打着门叫道:“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没人理她,她直拍到手掌红肿,叫到嗓子沙哑,慢慢一着门滑坐到地上。
王硕啊,王硕,你太过分了,不能接受自己大可不要带自己进京,何必假仁假义?
埋怨好王硕,她又想到婆婆。她苦命的婆婆,操劳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能享福了,这才两个月不到,她怎么就……
胡思乱想着,门开了,她就势向后倒去,身后的人迅速朝旁边让去,她重重的摔倒在地上。只听头顶传来王硕的声音:“开起来,你像什么样子!”原来刚才让开的人是他。
桑晴爬起来看了他一眼:“我要去拜祭婆婆。”
“人来人往的,你怎么去?”
“我怎么不能去?我哪里见不得人?”桑晴气得发抖,毫不留情的质问他。
“你……”王硕有些说不出话来,“我已娶丞相之女,怎么可以在短时期内纳妾?你也替我着想一下。”
“我只要去拜祭婆婆。”谁为她着想?
王硕见拗不过她,只得说:“那你晚上去,不过我警告你,不准给我闹什么乱子出来。接你回来是看在我娘的面子上,你给我记住了。”他凶狠的推搡着她。
桑晴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不再理他。
是夜,桑晴披麻戴孝跪在婆婆的灵堂里为她守夜。婆婆去了,她也是薄命之人,这么早就魂归离恨天。
她望着王钱氏的牌位,不由悲从中来。
婆婆啊,婆婆,你至少还有个善终,还有人为你的丧事大操大办,为你披麻戴孝,为你筑坟修墓。而我就不知道身后会是怎样一个下场了。
她手里折着纸钱,这好后就放进火盆里化掉。火苗跳动着在她脸上投射出光怪陆离的阴影。一边监视她的琉璃不由打了个冷战,她现在脸上的表情着实不像是一个活人该有的。
守夜对琉璃来说是件很恐怖的事,虽然将军府繁华富丽,但在一片白色中仍逃不脱死亡的阴影。她蜷缩在门口不敢离开,生怕桑晴闹出什么事来。
“你去歇着吧,我不会干什么的。”桑晴看出她的恐惧。她是不怕,若真有鬼魂索命那就来好了,反正她孑然一身,了无牵挂。
琉璃不理她,谁知道她会耍什么花招。
“你坐过来点吧,门口冷,坐到火边来取取暖。”桑晴又招呼她,这么个小姑娘,看上去也不过十五六岁,大半夜的坐在门口怪可怜的。
琉璃看了看漆红色的牌位和棺材,又看了看散发着温暖的火盆,终于挪了过去。不管怎么样,总比冻死好。
“你多大了?”桑晴问她,灵堂里只有她们两个人,也难怪她会怕。
她警惕的看了她一眼,怕她又什么诡计。
“你不要怕,我只是想找人说说话,太久没有人跟我说话了。”桑晴叹了口气。
“我十五岁。”
“还是个孩子呀。”
“不小了,家乡像我这样的都该嫁人了。”她撅起嘴,似乎不满意桑晴把他看成个小孩子。
“你也想嫁人?”
“也许,”她歪着头想了想,“我也不知道。”
“嫁人要看嫁什么人,要看看清楚,别像我这样。”她好像一个姐姐在告诫自己的小妹妹。
“你?”琉璃瞪圆了眼睛,她很想知道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啊。”桑晴凄凉的笑笑。
琉璃发现她笑起来不是一般的好看,究竟怎么好看她也说不上来,总之就是很好看。不过她笑起来让人不由自主地悲伤,仿佛在她的笑容里经历了千辛万苦。
桑晴絮絮叨叨的讲着她的故事,手里的动作却不停下。随着纸钱的投入,火盆里的火忽明忽暗。琉璃觉得时间没那么难熬了,而且她还挺亲近的,不像胭脂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