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明世宗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七月,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进士,王阳明心学的得意弟子:行人司司正薛侃向皇帝上奏,建议从宗室之中选一贤王,入京作为守城王。等陛下日后有了太子,再让守城王返回封国。
在薛侃看来,宣宗年代的襄王朱瞻墡、英宗年代的郕王朱祁钰,都在皇帝出征甚至遭逢变故之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么一项好的制度,被当年的“逆瑾”,也就是深受武宗朱厚照崇信的太监刘瑾所破坏,现在应该重新恢复。
祖宗分封宗室,留亲王一人在京司香,俗呼为守城王。有事或为居守,或代行礼,其为国家虑至深远也。列圣相承,莫之或改。正德初逆瑾怀异,遂并出封。—《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八》

世宗朱厚熜剧照
薛侃是不是讽刺世宗朱厚熜生不出儿子,我们暂且不论。但是文官们颠倒黑白的本事,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正德初年还在京师的亲王,是武宗和世宗的叔父:荣王朱祐枢,但他到底是不容于刘瑾,还是被文官们赶走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艰难的就藩之路朱祐枢,生于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十二月十七日,宪宗朱见深第十三子,生母端妃潘氏。潘氏本身并不出挑,只是在宪宗临终之前才被册封为端妃,评价也不过是“气质粹和,性资淑令”而已。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八月,宪宗驾崩,遗诏皇太子朱祐樘继位,即孝宗。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七月,年仅七岁的朱祐枢就行了冠礼,随即在八月被册封为荣王,封国湖广常德府。

紫禁城皇宫
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十三岁的朱祐枢离开皇宫出居诸王府,为就藩做准备。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二月十二日,是荣王成婚的日子,王妃刘氏:东城兵马指挥刘洪之女。然而这个时间点,先是撞上了庶母丽妃章氏的去世,又碰上了朝廷“春祈”祭祀土神的活动,算得上是一波三折。
戊子,礼部以宪庙丽妃章氏发引在初十日,荣王妃行纳徵发册礼在十二日,是二日俱在春祈禁屠宰日内。恐发引办祭、婚礼办宴于屠宰禁例有碍,请赐裁处。上命办祭、办宴日免禁屠宰,余日仍禁之。—《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一》
一般来说,亲王婚后就要准备就藩。我们来看看荣王殿下几位兄长的就藩年龄:兴王朱祐杬(十九岁)、岐王朱祐棆(十八岁)、益王朱祐槟(十七岁)、衡王朱祐楎(二十岁)、雍王朱祐橒(十九岁)、寿王朱祐榰(十八岁)、汝王朱祐梈(十八岁)、泾王朱祐橓(十八岁)。
就藩计划第一回
根据兄长们的就藩年龄推算,到了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的时候,十九岁的朱祐枢也应该收拾行囊,准备前往常德的荣王府就藩。为此孝宗吩咐荣王的一万石岁禄,由常德府给白米五千石,湖广其余各府给粳米五千石,随荣王之国的官军人等则预给俸粮六月。

明代亲王妃与亲王冠服
此前荣王成婚之时碰上庶母去世,准备就藩前更是连逢三丧:姐夫仁和公主驸马齐世美、庶祖母英庙充妃余氏以及弟弟申王朱祐楷。也许是负负得正的缘故,临行之前朱祐枢突然发现了一件喜事:王妃刘氏怀孕了。
对于朱祐枢这样的首封亲王来说,子嗣问题是头等大事。因为已经就藩的岐王朱祐棆,尚未就藩的申王朱祐楷,都因为无嗣而除国。为了确保王妃能够顺利生产,朱祐枢向兄长孝宗提出目前“难于启行”。
朝野上下闻讯之后一片哗然,文官们认为“舟行平流,无异家居”,荣王应该按时就藩,以免劳民伤财。不过孝宗还是站在了弟弟这一边,下旨让荣王明年二月再择日起程。
下礼部议,谓亲之国辎重甚多,一举动间劳费甚大,今已二次起运。自京师至常德府,不下六千里。有司一切供应,与夫朝谓席殿之数,俱为备日久。而舟行平流,无异家居。若欲改择日期,未免前功尽弃,重为劳贵。上允王奏,命待明年二月择日起程。—《明孝宗实录卷二百二》

孝宗朱祐樘剧照
就藩计划第二回
转眼就到了次年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二月,此时朱祐枢的嫡长子朱厚爋也已经出生,荣王也可以放心就藩。然而就在这个月,孝宗和荣王的亲祖母:圣慈仁寿太皇太后周氏病危,就藩计划被迫再度推迟。
三月初一日,太皇太后驾崩。荣王身为唯一的在京亲王,自然不能缺席大行太皇太后的葬礼。在太皇太后梓宫发引的前一日,荣王要陪孝宗“告辞几筵”。发引日当天,梓宫从午门离宫之时,荣王要哭行朝祖礼。四月二十二日太皇太后神主回宫,荣王还要衰服与孝宗皇帝及皇太子,一起在午门内迎接。
荣王跪奉神帛,兴,仍由庙街左门出至舆前,以神帛安奉讫。礼官跪奏请灵驾进发,荣王仍衰服随行。梓宫由承天门、大明门中门出,荣王还。—《明孝宗实录卷二百十》

太皇太后周氏剧照
一套流程结束,孝宗这才松了一口气,将弟弟的就藩时间定在了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六月。换句话说,荣王在京参与完祖母的小祥(去世一周年)祭祀之后,才会启程前往常德府。
就藩计划第三回
然而什么叫好事多磨,我们看一看荣王就知道。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五月初七日,孝宗皇帝驾崩,遗诏皇太子朱厚照继位,即武宗。
到了六月份,官员们小心翼翼地问新天子:荣王殿下是否需要按时就藩?兄长崩逝,不让已经就藩的亲王来奔丧算是惯例。但是把尚在京师的亲王打发去封国,未免有违大明以孝治国的宗旨。所以武宗和兵部观点一致,让荣王再等一年吧。
戊午,荣王当之国,兵部议以梓宫在殡,王哀疚未忍遽离。且缘道灾伤,不堪供亿。上命来年六月议之。—《明武宗实录卷二》

明孝宗泰陵
太皇太后和皇帝的葬礼流程差不多,朱祐枢身为亲王,也要哭送梓宫离宫并行朝祖礼。然而此时荣王殿下内心极为崩溃,一心只想着躺平,当即“以疾奏免”,也就是老子病了,你们爱找谁找谁。大侄子武宗也很无奈,只能表态:“朕自行”。
就藩计划第四回
一年之期很快过去,到了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六月,眼瞅着武宗皇帝活得好好的,宫中的太皇太后、皇太后也一个个身体倍棒,荣王殿下赶紧上奏要求就藩。兵部开会一讨论,认为可以在今年秋天启程。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皇帝陛下本人跳出来,要求叔父再留一年。据内阁首辅刘健从路边社得到的小道消息,皇帝想让荣王代行拜庙之礼,然后自己出去游山玩水。这下子朝野舆论哗然,刘健愤而上疏,结果皇帝却给他来个留中不报,也就是已读不回,主打一个拖字诀。
大学士刘健等言:“王自弘治十七年已奉孝宗皇帝钦命之国,彼因王妃临蓐留待次年。后两遭大丧,延至三年之上。今若无故再留,于情于礼皆有未安。况闻朝廷留王,为欲代行拜庙之礼。夫天子所敬,莫大于祖宗。常遣亲王代拜,尤不可闻之天下。臣等再三筹度,事体非轻。乞敕兵部会多官详议以请而裁决之,庶为允当。”不报。—《明武宗实录卷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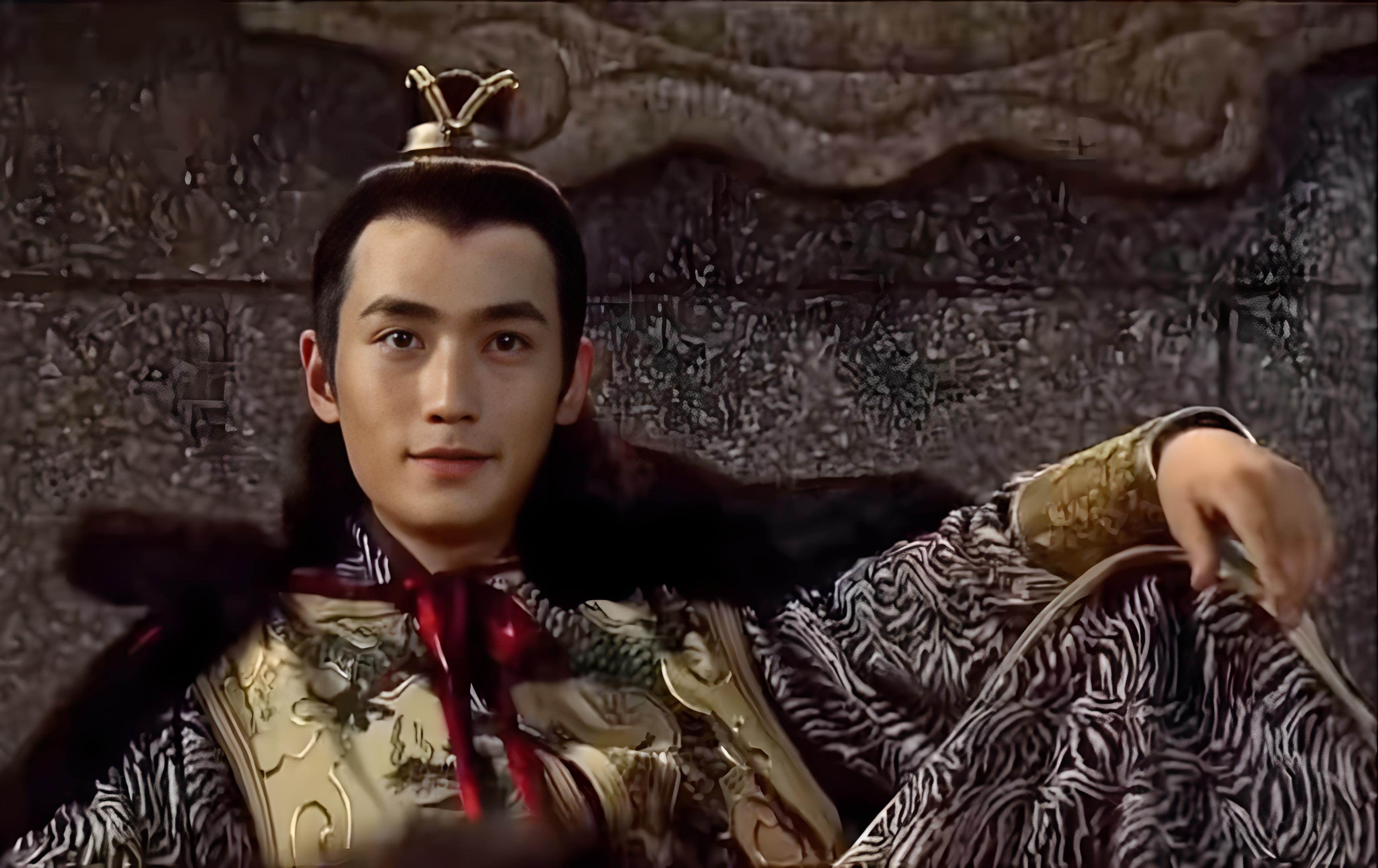
武宗朱厚照剧照
如果说之前王妃临盆之时,荣王殿下确实想待在京师。然而两遭大丧,被迫逗留数年之后,朱祐枢的就藩之心已经极为迫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钱。
荣王在京师的这几年,岁禄标准是三千石,而非就藩以后的一万石。一来二去,已经损失了两万多石。更为肉痛的是,王府的随侍官校,早在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就已经先行赶到常德府准备迎接亲王就藩。这些人的吃住开销,按朱祐枢的说法:“其衣与食皆仰给于臣”,这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在荣王看来,既然大侄子你不想放我走,那是不是多少要有点表示?经过一番极限拉扯,武宗最后同意加禄米一千石,即每年四千石,聊胜于无吧。
就藩计划第五回
人要是倒霉,喝凉水都能塞牙,这话放在荣王身上一点都不过分。

明代亲王府承运殿
到了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四月,湖广守臣奏报:“荣王府第渗漏坍塌”。武宗皇帝差点乐得合不拢嘴,这不是瞌睡有人递枕头么?
当时太监梁文带着人在衡州府(今湖南衡阳)督修雍王府,因为雍王朱祐橒在三个月前突然去世,正不知道接下来该干啥。于是武宗派人通知梁文,别回京师了,即刻去常德府,把荣王府给朕好好修一修。至于荣王殿下,王府没修完之前,您老人家还是待在北京吧。
甲午,湖广荣王府第渗漏坍塌,守臣奏请修葺。时太监梁文,郎中张谧方率人匠在衡州修盖雍王府第。以王薨停工,遂留董其事。—《明武宗实录卷二十五》
就藩计划第六回
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二月,生怕大侄子到期再出幺蛾子,荣王早早地就奏请就藩,这件事连史官也看不下去,在《实录》中记了一笔:“先是荣王屡请之国不果”。
好在这次皇帝终于正常了一回,让钦天监给算了个日子,把时间定在了当年七月。荣王随即上奏,表示自己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岁禄又这么少,府中“用度缺乏”,大侄子你看着办。武宗大笔一挥,赐叔父常德府香炉洲等处庄田六百三十余顷(六万三千余亩)。

奉天门(今故宫太和门)
七月二十二日,荣王殿下在早朝之后,到奉天门陛辞。五年了,终于能去封国就藩,朱祐枢心中也是感慨不已。
戊午,荣王之国。是日,上御奉天门早朝毕,退宝座后。王冕服至御前,行五拜礼。上赐王酒,送至门东阶,王叩头而下。上目送至午门,王叩头阖,上还宫。—《明武宗实录卷四十》
结语:也许是为了发泄多年滞留在京的怒气,荣王一路南下之时“绑缚官吏、需索财物、夹带私盐、沮滞客商”,所过之处鸡飞狗跳,只留下一地鸡毛。武宗也不在意,虽然降敕戒谕,但却把主要责任都归在了随行的王府官员头上。
回到本文开头,文官们说荣王被迫就藩,是刘瑾违反祖制,什么叫睁眼说瞎话,这就是。文人的一支笔,颠倒黑白最拿手,千万不能让话语权落在他们的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