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明代官制体系,于京官系统内,每三年会举行一次考选。在此机制下,各部主事有机会升任御史或给事中,这在官场中被视作晋升之途。然而,值得探究的是,主事官居正六品,御史为正七品,给事中则为从七品。为何官职品级降低,却仍被定义为升官?此现象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官场逻辑与制度设计,引人深思。

【明代吏部选官的规则】
在明清时期,吏部于官员选拔方面秉持着同一重要准则,此准则聚焦于“资格与出身”。据《明史·选举志》所记:
在选拔人才的途径方面,除进士、举人、贡生之外,还涵盖官生、恩生、功生、监生以及儒士等。同时,吏员、承差、知印、书算、篆书、译字、通事等诸多杂流亦在其列。这些选拔途径可大致归为三类:其一为进士途径;其二是举贡途径;其三则是吏员等杂流途径,此即所谓“三途并用”之制。
在明代,朝廷对于科目极为重视,严格施行“非科举者不得选官”之政策。然而,虽有此规,那些未经由科举途径的“杂流”人员,仍可凭借吏部铨选的方式踏入仕途。值得注意的是,在官职授予环节,出身这一要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对个人仕途的发展前景影响深远。
科举之正途,涵盖进士与举贡。进士,于正途之中,归属“甲科”范畴;而举贡,则包括举人以及诸般监生。需明确,举贡之内,仅举人位列正途之“乙科”。
在科举制度下,举人面临着两种主要发展路径。其一为投身于会试,其二则是接受教职任命。然而,教职在官僚体系中地位较为卑微,且晋升空间极为有限。鉴于此,落第举人通常倾向于前者,即积极参与会试。仅当举人多次于乡试中失利后,吏部方会考虑为其安排官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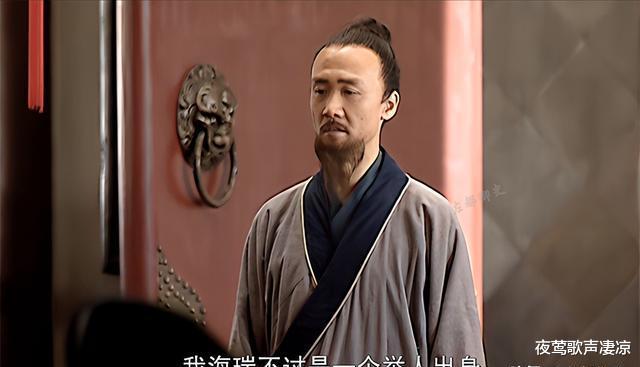
在监生体系里,贡监地位最为尊崇,就出身而论,其与举人相当,故而衍生出“举贡”这一称谓。相较之下,其他诸如贡生、监生及荫生,地位则依次递减,皆在举人之下。
杂途或异途,其构成人员最为繁杂。涵盖京师及各省内外衙署中的全部文职事务经办者与各类技术专业人才。此群体因受限制,无法涉足科举之途,故而难以获取科举功名,仅能出任品级较低的官职,即所谓“吏员”。
关于依据出身选拔官员的标准,《明史·选举志》有着详尽且明确的规定。
在古代官员选拔体系中,于京任职的六部主事、行人、中书、评事、博士,以及在外的知州、推官、知县,其人选多从进士中遴选。而外官中的推官、知县以及学官,主要从举人、贡生里选拔。至于京官中的五府、六部首领官,以及通政司、太常寺、光禄寺、詹事府的相关职位,则由官荫生充任。州县佐贰官员以及都布按三司首领官,通常从监生中择取。此外,外府、外卫、盐运司首领官,乃至中外各类杂职之中入流与未入流的官员,一般是从吏员等群体内选拔。

据此可推断,在初次选拔官员的进程中,出身这一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堪称左右官员仕途发展的关键要素。
对明代职官制度有所研究的学者皆知,在明代官场体系中,仕途前景最为优渥者,首推翰林院官员(如修撰、编修、检讨)、六部主事以及科道官员。紧随其后的,则是各省州县的正印官。究其原因,盖因上述几类官职,在初次授任时,其任职者皆为进士出身。
【明代不同出身官员的升迁路线图】
出身与官员升迁之间存在紧密的因果关联。就翰林官的晋升路径而言,通常伊始由编修、检讨之职,进而擢升至侍讲、侍读,随后进阶至詹事府少詹事,继而升任侍郎、尚书,最终得以入阁,获任大学士之位。

进士出身者的仕途升迁路径主要涵盖三类。其一,于六部担任主事一职,经考满后,擢升至员外郎、郎中,再历经考满,进一步晋升为各寺少卿、卿,后续可升任侍郎、尚书。其二,身为六科给事中和御史,考满之后,会升任佥都御史或左右通政,继而晋升为副都御使、都御史,亦或转任六部侍郎、尚书。其三,从知县起步,先晋升为知州、府同知,直至知府,随后通过“行取”这一机制(即吏部从各省正印官中择选部分官员担任京官),转任科道官,最终逐步升迁至侍郎、尚书。
就晋升途径而言,通过举贡或吏员途径进入仕途者,其升迁轨迹颇为局促,升迁契机相对稀缺。因此,他们于职位上的留滞期往往较长。即便获得升迁,亦鲜能企及侍郎、尚书这般高级别的官职。
与清代不同,明代在政治架构上秉持“内重外轻”之原则。在这一体系下,诸如布政使、按察使这般地方高级官员,其地位亦逊于四五品的京官。至于京师的各类衙门,内部等级分明。其中,翰林官与科道官地位最为尊崇,此两类官职对于任职者的资格要求亦极为严苛。

翰林官之概念,无需赘言。于历史职官体系中,素有“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得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以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可任”之规。此规深刻彰显翰林官选拔之严苛与地位之尊崇。实则,即便以进士身份为基,亦仅有少数精英方获入翰林院之契机,足见翰林门槛之高。
科道官,乃执掌风纪之要职,虽品秩未臻高位,然所司职责至为关键,堪称朝廷行政体系中不可或缺之核心岗位。依定制,当科道官职位出现空缺时,其补任途径多元。其一,可从翰林院庶吉士中改授;其二,于两京以进士身份任职户、礼、兵、刑、工五部之主事,以及中书、行人等职官,经考满后选拔任用;其三,亦可从以进士、举贡身份出任知县者中,通过行取之方式选任。
需明确指出,通过举贡途径获得出身而入选为科道官者,数量极为稀少。据史料记载:“于天下担任地方守令之官员中,进士约占十分之三,举贡约占十分之七;而于科道官群体里,进士所占比例高达十分之九,举贡仅占十分之一。”
在科道官的选拔任用体系中,举贡出身者入选的比例仅占十分之一。更为特殊的是,即便这占比十分之一的举贡出身者得以进入科道官序列,其分布呈现出显著的不均衡态势。具体而言,表现为“有台无省,多南少北”。即这些举贡出身的科道官,大多仅能补任御史之职,而鲜少能获授给事中;在任职地域上,多集中于南京,北京地区则极为罕见。

在明代的职官体系中,翰林院与科道官之职位,对于吏员出身者而言,可谓遥不可及。自洪武初年便明确颁定规制,严禁吏员参与科举考试。此规定犹如一道壁垒,彻底阻断了吏员经由科举获取举人、进士功名的进阶之路。不仅如此,永乐朝伊始,又出台相关政令,明确限制吏员进入科道官序列。自此,职官流品之区分愈发泾渭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