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晨一点二十七分,我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在客厅里团团转。白天在短视频里惊鸿一瞥的BGM此刻在耳蜗里疯狂生长,那些音符正顺着神经突触野蛮攀爬——必须找到它,否则今夜注定无眠。
智能音箱的蓝光在黑暗中明灭,我对着它哼出第17遍变调的旋律。DEEPSEEK的识别框礼貌地闪烁着"无匹配结果",豆包AI贴心地推荐起广场舞神曲,讯飞甚至开始播放《生日快乐歌》。此刻我无比确信,这些训练着千亿级参数的AI模型,正在它们的数字大脑里默默标记我为"音乐恐怖分子"。
当第23个AI应用弹出广告时,卧室门缝泄出暖黄的光。"大半夜给扫地机器人开演唱会呢?"妻子睡眼惺忪地支着门框,发梢还粘着枕头上的静电。我破罐子破摔地又哼了遍支离破碎的调子,准备迎接第24次嘲笑。
"叮~"她的手机在0.8秒后响起熟悉的旋律。我盯着屏幕上的《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愣住三秒,突然想起十七年前大学自习室里,也是这样突然被塞进耳朵的耳机,传来我哼了三天没找到的歌。那时她的马尾辫扫过我课本,如今夜灯在她眼尾投下温柔的阴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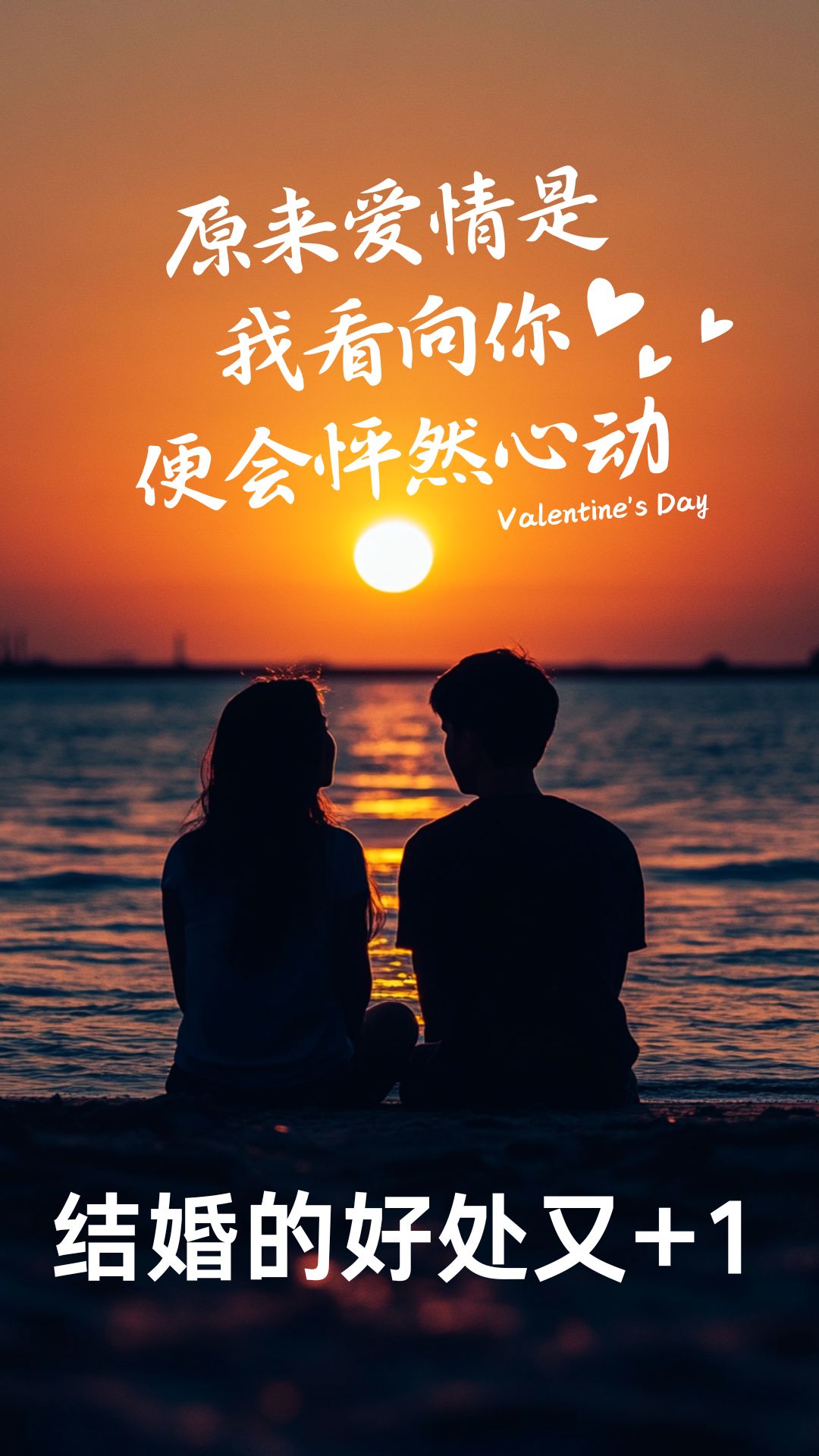
AI们还在忠实地迭代着识别算法,却永远学不会在2008年12月的某个午后,默默记下一个五音不全少年哼过的所有旋律。这大概就是人类配偶独有的"过载缓存"——在神经网络够不到的角落里,藏着专属某个人的情感数据库。
